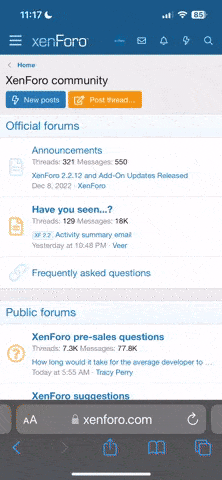韩愈在其《原道》之开篇,提出"博爱之谓仁"。这一以"博爱"释"仁"的意见,在宋代以后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儒家仁学中有代表性的阐释,然而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也对它提出了不少批评。通过考察,本文发现,以"博爱"释"仁"并非韩愈的首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汉唐儒学对"仁"的思考路径,宋代以后对这一说法的接受,则表现出理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使我们看到,韩愈作为中唐儒学革新的代表,其思想既开启了儒学革新的新方向,同时也与汉唐儒学保持着复杂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精神世界的独特面貌和古文创作的独特追求。
韩愈以"博爱"释"仁",在宋代以后曾引起不少批评,有人认为这个说法容易与墨子"兼爱"说相混淆。朱熹的弟子陈埴曾经提到"墨翟以兼爱为仁,孟子力诋之,韩愈作《原道》辟佛老,乃指仁曰博爱之谓仁",他对此甚感不解,遂向其师请教。朱熹为韩愈作了辩解(《木钟集》卷2)。韩愈之说虽有朱熹等人为之辩解,但不可否认,它的确容易使人误解。在汉译佛典中,"博爱"一词十分常见,它经常与"慈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唐宋典籍中,多以"博施"、"博爱"指称佛教之慈悲,如宋人之文章提及某氏乐于佛氏之说,"非取其所谓报施因果,乐其博爱而已"(《河南集》卷5);至于"博爱"与墨子之"兼爱"的区别,韩愈本人非但没有正面剖辨,反而在《读墨子》中将两者相提并论,所谓"孔子之泛爱亲人,不兼爱哉"?这就使问题更见复杂。力排佛老、攘斥异端的韩愈,以"博爱"来定义"仁"的用意是什么呢?
首先,从《原道》的内容来看,韩愈对"仁"、"义"、"道"、"德"的定义,都明显受到汉唐经疏的影响。以"博爱"释"仁"的意见,在汉唐经疏中已有明确的体现,如《周礼•地官•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云:"仁,爱人及物。"这里以"爱人"与"及物"联言,已经接近"博爱"之义,故宋人王与之《周礼订义》于此郑注下注云:"自博爱而兼爱者仁也。"降及唐代,以"博爱"与"仁"并举的言论已经十分常见,孔颖达等人撰著的《五经正义》多次提到"博爱",并将"博爱"与"仁"联系在一起,如《礼记•表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孔疏云:"此经申明同功异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泛施博爱,其事一种是未可知也。"这里以"泛施博爱"论仁,与韩愈之说已十分接近。
《原道》之论"义"、"道"与"德"也明显渊源于汉唐经疏。如"行而宜之之谓义",以"宜"训"义"最早见于《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在汉人经注中,这个训释十分常见,《诗经•大雅•文王》"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恚",毛传:"义,宜也。"郑笺:"义之言宜也。"《周礼》"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郑注:"义,宜也。"唐人《五经正义》多次出现类似训释,如《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正义:"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尚书•高宗肜日》"言天至绝命",孔疏:"义者,宜也,得其事宜。"《尚书•舜典》"徽美至违命",孔疏:"义者,宜也,理也,教之以义,方使得事理之宜,故为义也。"韩愈之说与上述训释一脉相承。《原道》"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郑玄注:"道,犹道路也,出入动作由之,离之恶乎从也。"郑玄以"道路"比喻"道"韩愈之说亦脱化于此。《原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实是以"得"训"德"之说的延续。以"得"训"德"最早见于《礼记•乐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汉人经注与唐人经疏中,类似的意见十分常见,如《诗经•大雅•皇矣》之孔疏引《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服虔注:"在己为德。"《周礼•地官•司徒》"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疏:"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总名。"可见,韩愈对"仁义"、"道德"的解释,明显受到汉唐经疏的影响。韩愈称自己为文乃"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他对六经的学习,显然包括对经疏的掌握。中唐儒学虽然兴起以经驳传之风,但韩愈等人还是对经疏有深入的了解,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在唐代有极大影响,那么韩愈以"博爱"论"仁",是否只是对流行的经疏意见的因袭呢?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以"博爱"释"仁"的意见是如何形成并流行的。
先秦儒家之论"仁",并未直接出现以"博爱"释"仁"的说法。在孔子的言论中,与"博爱"最接近的思想是"博施济众"与"泛爱"。《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中"泛爱"之"泛",宋代邢m即解释为"博"。"博施济众"见于《论语•雍也第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
"泛爱"与"博施济众"是孔子所倡"仁者爱人"的一种体现,但孔子论"仁"的重心并不在此。孔子仁论的出发点是"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在修养方式上主张"能近取譬",主张"仁"的实现是推自爱之心以爱人的过程,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这个理论重心出发,孔子对"泛爱"与"博施济众"都没有大力阐扬,持论不无谨慎。"泛爱"之积极的表现自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更多地是从"恕"道来理解"泛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恕"道则是"夫子之道"的核心之一。至于"博施济众",孔子虽称扬其为盛德大业,但"尧舜其犹病诸"一语则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态度,"博施济众"固然是为仁终美的境界,但其事高远广大,作为内在修养的"仁",还是要从"能近取譬"处入手。关于"博施济众"与"仁"的关系,前代注家有不同意见,而邢m、朱熹等人的意见较有代表性,邢m认为孔子之言是:"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于仁,谓不啻于仁,必也为圣人乎!"朱熹引吕祖谦之说云:"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这些意见揭示出孔子看待"博施济众"的真实想法。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的孔子哲学,不会以"泛爱"与"博施济众"为其"仁"论的核心内容。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但其发展主要是以性善论推原仁心之本,而其仁政理论则直接建立在仁心说的基础上。孟子对孔子"能近取譬"、"己欲立而立人"的思想做了深入的发展,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因此,就其理论的重心来讲,孟子与孔子一样,论仁都立足于内在的修养,虽然他对恩及天下的作为多有描述,但其理论的立足点还在于对人性之善端的培养与发扬。"博爱"之思想在孔孟哲学中未受充分关注,有其内在的理论原因。
最先将"博爱"作为仁论的重要内容而加以讨论的,就今天所见的材料来看,是西汉中叶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其书卷10云:"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同书卷18又提到圣人"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这里的"泛爱"意近"博爱";又卷41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后者脱化于《孝经•三才第七》"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但《孝经》虽云"博爱",还没有像董仲舒这样将之与"仁"教相提并论。
降及汉晋之际,以"博爱"论"仁",乃至直接以"博爱"释"仁"的意见大量出现,如东汉末年徐干所著之《中论》,其文云:"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卷上)汉末大儒郑玄之经注虽没有直接出现博爱为仁的字眼,但有关的注释已经流露出类似的意思,如《周礼•地官•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云:"仁,爱人及物。"这里以"爱人"与"及物"联言,已经接近"博爱"之义,故宋人王与之《周礼订义》于此郑注下注云:"自博爱而兼爱者仁也。"三国时期的韦昭在为《国语•周语》做注时明确提出"博爱于人谓仁";晋袁宏《后汉纪》卷3直接出现"博爱之谓仁"的说法,其文云:"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称焉,德播一乡,一乡举焉,故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立名,未有殊其本也。"这些意见相当集中地出现在汉晋之际,是很可注意的现象。此后,以"博爱"与"仁"并举之论,渐次流行,唐人文献中,类似记载,所在多有,如朱正则《五等论》"盖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爱,本之以仁义"(《旧唐书》卷90);张九龄称赞东汉徐稚"博爱以体仁"(《曲江集》卷20《后汉征君徐君碣铭并序》);常衮称赞杨灵"德行孝悌,温良博爱,故宗族称其仁"(《滑州匡城县令杨君墓志铭》,《全唐文》卷420);柳宗元亦称扬其叔父"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仁著于内焉"(《柳宗元集》卷12《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唐律疏议》卷一有"心则主于博爱之仁"之语。可见,"博爱"与"仁"相联的说法,在唐代已经相当流行。
以"博爱"论"仁",乃至以"博爱"释"仁"的意见,为什么自西汉以来逐渐流行,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从内涵上看,"博爱"一词,融会了《论语》之"博施济众"与"泛爱"两种含义,前者多指向"王者之德",如《孝经•三才章第七》"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汉代以来,"博爱"作为"王者之德"被大量使用,如汉初贾谊《新书》有"德莫高于博爱人";《汉书•刑法志》云:"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卷85)《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何休注,称晋伐鲜虞为"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在"泛爱"这个意义上,"博爱"指向"士君子之德",从今天所见的资料来看,其使用要晚于作为"王者之德"的意义,《后汉书》称赞"(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这个用法在后世相沿不断,上述唐代典籍中张九龄、柳宗元等人的言论也是类似的用法。
作为"王者之德"的"博爱",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以"博爱"论"仁"的核心内容。《春秋繁露》重视以博爱论仁,并非行文之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表达了鲜明的尊君态度,他提出"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卷1);"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卷6);"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民有庆,万民赖之'"(卷11)。这种尊君思想,反映了董仲舒为巩固汉代中央集权专制政局、发挥大一统理论所做的政治思考。对于人君的政治责任与权力,他都做了丰富的阐述,提出人君一方面要以威势成政,一方面要躬行教化,因此他特别强调人君当恩泽远被,而恩泽所施愈广,人君之德行愈完美,其论云"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仁义法》)。在这个理论背景下,作为王者恩泽远被的博爱,就成为"仁"的重要内容而受到强调。
董仲舒的尊君思想,固然受到西汉现实政治环境的激发,但从儒学发展的背景来看,它也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在先秦儒学中,孔孟的政治思想并不强调君尊臣卑,孟子所倡民贵君轻之论,更与尊君之论判然有别。服务于君主集权的尊君之说,在儒家内部,可以上溯至荀子,《荀子•正论》云:"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服从,以化顺之。"其《致士》云:"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
荀子与董仲舒的尊君之论,既回应了现实的需要,也有儒学理论上的基础。荀子生当战国晚期,与孟子将儒家伦理向心性上发展的方向不同的是,他的理论以礼为核心,强调隆礼重法,追求现实之事功。他提出儒者修身之要务,在于尽心家国政治,于现实中推行礼义,其《儒效篇》指出,儒者可以"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荀子对君主之推尊,是其隆礼重法思想的现实体现。礼义隆于天下,实赖君主以完成,故君主必握权柄以治下,其《性恶篇》云:"君者善群者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若去君主之势,则"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忘,不待顷矣"。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君道与儒效是相通的,儒者"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效》)。荀子将儒家伦理建立在礼的现实推行与实践之上,因此圣人与人君隆礼义于天下的巨大作用,就代表了礼之推行的最高成就,因而也就成为伦理之典范。如果说"博施济众"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因其事高远而被悬而不论的话,那么,在荀子之学中,它就成为极受关注的内容,在《儒效篇》之开篇,荀子就大力标举周公的"大儒之效",称赞他"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 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按照这样的思路,恩泽广被的"王者之德",自然成为"仁"最重要的体现。
董仲舒之尊君思想,回应了西汉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在理论基础上,他直接承袭了荀子哲学的精神,同时做了进一步的推进。荀子论"仁",体现了以"礼"释"仁"的倾向,其辞云:"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这反映了其整体的思想倾向。董仲舒对"仁"做了更丰富的阐释,在阐发孔子"仁者爱人"之义时,他提出了"仁以治人"的意见:"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而容众……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这个意见,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孔子爱人之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其实质则是淡化了孔孟仁学中以"仁"为个体内在之精神修养的因素,突出了仁为外治的精神,强调"仁"对于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作用,所谓"推恩广施"、"宽制容众",这种理论倾向,与荀学颇多共性。董仲舒对"仁"的阐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郑玄经注释"仁",云:"相人偶谓之仁。"其中的"相人偶",就是强调从人与人的关系中理解"仁",这同样是"仁以治人"、"仁为外治"思想的发挥。清代阮元总结了这种看法,"今综论《论语》论仁诸章,而分证其说于后。仅先为之发其凡曰:'元窃谓诠解'仁'不必繁称远引,但举《曾子制言篇》'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譬如相人偶之人'。数语族以明之矣。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称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然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研经室一集•论语论仁篇》)。"仁为外治"的思想,上承荀子论"仁"之理论视角,它与孟子的仁心说反映了荀孟二家发展孔子思想的不同取向,在其后的历史中,董仲舒这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人文献中类似的意见也十分常见,如魏徵之《理狱听讼谏》云:"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全唐文》卷140)这与董仲舒的理论显然有渊源之迹。董仲舒以"博爱"论"仁",正渊源于他所阐述的"仁以治人","仁为外治"之思想,作为"王者之德"的"博爱",是"仁以治人"的最重要的体现。
作为"士君子之德"的"博爱"在儒家仁论中地位的上升,也与荀子哲学对儒效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哲学中以保守的态度论及的"泛爱",在荀子哲学中就成为仁的重要内容。以"博爱"论"仁"之思想与荀子哲学的关系,还可以找到不少具体的佐证,如前所举徐干之《中论》直接出现"仁以博爱"的说法,而《中论》对荀子有极高的评价,其辞云:"荀卿生乎战国之际而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审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哲学影响下产生的"博爱为仁"的意见,与墨子之"兼爱"判然有别。荀子以礼释仁,因此"博爱"是以尊重礼的原则为前提。关于这一点,前人的有关解释,已经有相当清晰的阐发,如《古文孝经孔氏传》于"是故先之以博爱"下注云:"博爱,泛爱众也,先垂博爱之教以示亲亲也,故民化之而无有遗忘其亲者也。"《孝经•天子章第二》"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唐玄宗注云:"博爱也。"宋代邢?疏云:"此依据魏注也。博,大也,言君爱亲又施德教于人使人皆爱其亲,不敢有恶其父母者,是博爱也。"这些意见皆以亲亲为"博爱"之基础,体现了"以礼化民"的精神,其与墨子兼爱之义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董仲舒以"博爱"论"仁",并未辨析其与墨子兼爱之差异,原因在于其"仁为外治"之思想,贯注着以"礼"释"仁"的精神,"博爱"乃君王以礼教化天下之成就,故博爱之有别于兼爱,毋庸赘言。
韩愈以"博爱"释"仁",继承了汉唐儒学仁为外治、崇尚礼教的精神,其渊源于荀学的痕迹,极可注意。以荀学观之,博爱之基础实在于礼,故虽博爱而不废亲亲尊贤,仁民爱物之次第,这一精神乃不言而喻,故韩愈在《读墨子》中直接以孔墨并论而不担心有淆乱之危险,所谓"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如此坦然之论,正反映出荀学在汉唐儒学中的广泛影响。然而宋人在理解其博爱为仁之说时,多忽略其中的荀学渊源,故与墨子兼爱混淆不明之讥,遂由此起。
宋明理学对"博爱为仁"之说的理解,多着重从"仁"与"爱"的关系来分析,其中渗透了新的理论视角,程颢认为韩愈此说不妥,因为"爱"是"情","仁"是"性":这里体现了北宋道学对性情问题的关注。明代王阳明对此说的批评,则是从其致良知之理论出发:"爱之本体固可谓之仁,但亦有爱得是与不是者,须爱得是方是爱之本体,方可谓之仁。若只知博爱而不论是与不是,亦便有差处,吾尝谓博字不如公字为尽。"(《王阳明集》卷五)王阳明认为,"仁"的本质即是"心之本体",即"良知",而"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卷2),所谓"廓然大公",即是"无私欲之蔽"(卷1);因此,"爱"只有"无私欲之蔽",才能复其本体为"仁"。这些讨论,无一不体现出新的理论兴趣,而这对于韩愈本人来讲,应当是他始料未及的。
由此可见,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代表,他虽然开启了不少儒学革新的新方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与汉唐儒学保持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对"仁"的理解,无疑是其儒学思考的核心,而其以"博爱"论"仁",并非是对汉唐儒学之成说的简单因袭,而是包含了对汉唐儒学之理论旨趣的深入继承,这一点可以从《原道》一文,从他整体的思想倾向中得到清晰的印证。《原道》篇对"仁"之内涵的阐释,清晰地表现出崇尚礼教、追求外治的精神,这与孟子心性哲学的关注点不无异趣。《原道》以"仁义"定名"道德",而其对"仁"之内涵的具体阐释,则是紧紧围绕"先王之教"所体现出来的一整套礼教施设,所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 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原道》还同时表现出对圣人与君主的充分推重与肯定,认为"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韩愈排击佛老之理论基础正在于指出佛老否定圣人,无父无君,而其根源在于空谈心性,无视礼教之作用,所谓"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以其夷狄之法而坏先王之教。从《原道》的论证结构上看,其"定名"、"虚位"说,也是对儒家正名思想的发挥,而正名思想的核心是礼教精神,孔子倡之于前,而由"隆礼义"之荀子发扬于后,《荀子》一书即有《正名》一篇。可见,韩愈对仁的理解,贯穿着仁为外治的入世有为精神,与崇尚礼教的伦理追求。宋人认为汉人将"仁"说成"恩惠",而韩愈受了汉人的影响(《北溪字义》),虽语焉未详,但也看到了韩愈仁论与汉唐儒学之间的关系。向心性论转向的宋代儒学,对于韩愈将"仁"说成"恩惠"不无微辞。
韩愈思想与汉唐儒学的联系,对于我们认识其思想的独特面貌极有帮助。韩愈推尊孟子,提出"内仁而外义"、"仁义存乎内",其《原性》从性情之辨中讨论仁义,这些都受到宋儒的充分关注,但其仁论最大量的表现,则是希望有为于当世的强烈愿望,是为自己与其他布衣之士不得其位的呐喊;是希望乾纲独断,排击藩镇与宦官,重建君臣父子之伦常的政治诉求。这些都流露出汉唐儒学的理论旨趣。
韩愈对仁的外治之功效有强烈的追求,渴望有为于当世。其《原道》虽然引用了《礼记•大学》之正心诚意之论,但其用心在于对天下国家的关注,以此来批评佛老之徒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张籍曾经劝韩愈著书立说以排击佛老,韩愈委婉地拒绝了,他说:"然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也。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者亦有矣,闻而疑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韩愈一生都在为儒家精神的当世之效奋斗不已,其精神中鲜明的实践品格,极为引人注目。
对有道之士不得其位的不平与焦虑,是韩愈诗文的重要主题,其理论基础正是"博爱为仁",只有予仁者以高位,才能使其"博爱远施",而只有"博爱远施",才能充分地实践"仁",其《太学生何蕃传》感慨何蕃位卑而不能"有所立",其辞云:"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于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为泽,不为川乎!川者高,泽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义,充诸心,行诸太学,积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将雨,水气上,无择于川泽涧溪之高下,然则泽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于彼者欤?故凡贫贱之士,必有待然后能有所立,独何蕃欤!"这样,韩愈就为寒士的不平之鸣赋予了充分的道德内涵。宋人对韩愈的干进之心多有批评,北宋儒学革新之代表,对韩愈深怀景仰之心的欧阳修,对韩愈《感二鸟赋》中所流露的钦羡名位富贵之念感到不满(《读李翱文》)。南宋时朱熹则批评韩愈只是要官做(《朱子语类》卷137)。这些意见都忽视了韩愈仕进之念与其求仁之心的密切联系。宋儒将仁论的基础转向心性,韩愈仕进之心的伦理内涵自然容易被忽视。葛晓音师曾在分析韩愈对儒道革新的贡献时,精辟地指出,韩愈大力肯定有道之士的仕进追求,"使出身贫贱的道德之士要求跻身卿相之列的政治愿望,罩上了'道'的圣光"(《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汉唐文学的嬗变》)。韩愈的这一贡献,与其对汉唐儒学理论旨趣的继承发扬有密切的关系。
独特的仁学思想,使韩愈的政治理想与态度也呈现出高亢的姿态。渊源于汉唐儒学的"博爱为仁",以崇尚礼教为其核心,因此韩愈所渴望的不是一时一政的裨补,而是在现实中重新建立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一整套"先王之教"。他对于王权的推重,打击藩镇与宦官势力的思想,都不是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着眼于"先王之教"在社会中的全面重建。完整而丰富的理想蓝图使其政治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韩愈对理想的服行不怠,无疑会使其在世人眼中变得狷介倔强。从政治态度上看,韩愈的仕进之心,并不止于得一位,荣一身,而是希望得大位成博爱广敬之效。荀子以推行礼义之成就的大小来判断儒者成就的高下,而大儒之效必以重权高位为基础。我们不难注意到,韩愈所抒发的不平之鸣,亦流露出对大位的向往。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盛唐文人高谈王霸,渴望高位,不屑吏职的传统,其不平之鸣中的郁勃之气,正与巨大的政治渴望相伴随。但是,其追求的核心乃在仁义,其抗俗自立,发乎伦理追求的道德气魄,与盛唐文人高谈王霸的"露才扬己"相比,又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这正是中唐古文之寒士精神,与盛唐精神的联系与区别所在。
宋儒不仅以向心性的转向,改变了韩愈以仕进为求仁之方的理论取向,同时也以更理性务实的态度,改变了韩愈政治理想与态度的高亢姿态,欧阳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欧阳修早年与范仲淹等人赞助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官峡州夷陵参军。《宋史》本传记载:"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错乖直,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见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也正是从夷陵开始,他开始对政治的复杂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思想上高言空论的成分逐渐被排斥,将忧念天下之心,与不辞卑官的脚踏实地联系起来。其后王安石及第之后,主动求为地方官,希望由此了解民生,积累政治经验。这些宋代精英士大夫的政治姿态,与韩愈有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宋儒与韩愈的差异,使我们看到,韩愈虽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他身上有很多地方表现出与传统时代的联系,荀子哲学以及深受荀子之学影响的汉唐儒学的理论旨趣,在韩愈的仁论中有深刻的反映。韩愈推尊孟子,但他对孟子仁论的心性内涵并没有做更多的阐发,这个工作是留待宋儒加以深化,他认为荀子"大醇小疵",但其仁论又多著荀学色彩。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推知,荀学之于韩愈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汉唐儒学的中介而产生的。韩愈汲取其崇尚礼教、追求外治之精神,而改变了其单纯倡言性恶等理论旨趣。
由"博爱之谓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韩愈思想的复杂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内涵,学界已经有了许多深入的探讨,而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来看,这样的探讨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http://www.studa.net/wenhuayanjiu/080819/155427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