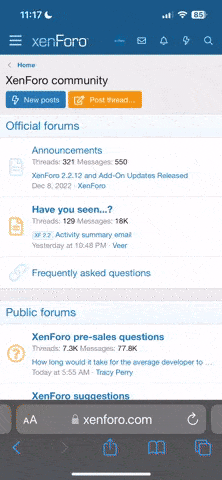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哪里――谈ZG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1人在浏览)
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哪里――谈ZG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ZG十八大的中心话题是改革,有学者称是“重启改革”。自从ZG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出“改革开放”旗号,已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会等方面积累的问题也日渐增多,许多矛盾已近临界点,执政党自身腐败冗散等问题严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坦陈“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改革必须继续,不改革没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内定新总理李克强声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媒体概括李总理讲话的核心,若用两个字那就是“改革”;用四个字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铁还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时代最强音,也是当代政治关键词。但是,“维稳”一词在近几年似乎盖过了改革,成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20多年前,邓小平就呼吁“稳定压倒一切!”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将无从谈起。为求稳定,邓小平说了不少狠话,也出强力干了一些狠事,声言“发展是硬道理!”要稳定20年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坚决拒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核心”,都是谨慎地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前进,经济上破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许多麻烦问题都是用强力捂着拖着,民众不满,上访者不绝于路,群体性抗议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万次,到如今,“维稳”形势已日见危艰,代价越来越高而局面益显严峻。可以说问题相当严重。
“维稳”思维使执政党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动作,或者说其路线图就是先经济,后政治,先脱贫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有人甚至说经济上去了一切都好办,这不仅使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而且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权钱交易寻租腐败,出现既得利益特权阶层阴奉阳违以“维稳”为借口,暗中阻碍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情状。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对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理顺公平效率各种关系。改革是十分繁杂的事,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掌权者自己,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谁,却长期模糊不清,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能撼动,自称党虽也会犯错但能自我匡正,党政体制本身没有问题,不允许怀疑,改革只是政策调整,是执政党领导民众改造社会。那里有问题需要改革,就在那个领域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本已很强的党政机制,而很少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于是乎改革进程中动不动就高喊“加强党的领导”!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说:“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强调人大立法“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并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现动u,“国家可能陷入嚷疑钤ā薄A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也要“加强党的领导”,人大立法实际上变成了党立法。
其实,强化体制加强党的领导早已达到极限,已是强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松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转换体制机制,给民众更多自治的空间,这或许可称之为“开放”吧!党的领导自ZG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就强得很,毛泽东主政时已是强得不能再强,现在还要再加强,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其实就是不肯转换体制机制,等于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都清楚,我国经济大发展就在于抛弃了苏式集权计划模式,在于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行政管制,在经济领域转换了体制机制。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也能放松放松,更加开放一些。执政党如果对自身问题动一动刀子,对自身体制、政治行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于改革呢?
胡、温十年执政不可谓不勤勉,但在关键问题上想改改不动,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最后两年推出的两项所谓“大”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敢对准自己,不敢在关节眼上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措乖张,进退失据。
2011年2月19日,ZG中央党校隆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见地出席,政治局委员也统统到场,由习近平主持,胡锦涛发表讲话。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其基调还是加强党的领导,以强化社会管制来“维稳”。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橹醒肷缁峁芾碜酆现卫砦T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担任主任,对社会民众的管控又进一步加强了。
10月18日,为时4天的ZG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全会没有对自身腐败等问题提出议题,而是空穴来风地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知道,思想文化的繁荣靠的是百家争鸣,应减少思想箝制,保障创作自由,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春秋战国和五四时期,就是因为权力不进入该领域。而ZG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却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S后发表题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主动权”的讲话,并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要“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一切还都是老路数,“加强党的领导”,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半点松绑的意思。
这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其实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维稳”之实,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请问,加强党的领导,就能繁荣文化吗?这与其说是文化改革,不如说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当局就加强了对网络空间的监管,要推行网络实名制,关闭了一些敢提异议的网站,以加强“社会管理”,其实质乃是“维稳”防民。在我国,军队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维稳经费超过军费。据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2012年春“两会”《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开支是6293亿元,比国防费高出200亿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预算达7017亿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费,全都是用在维稳防民上。梁启超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改革对象的确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是挥向别人,还是对准自己?是改别人,还是改自己?这个问题,30年来其实一直是摇摆不定,改革的手术刀大多是挥向了社会各色人等,却很少挥向执政者自己。上述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即是典型,无论是“社会管理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不敢对自身严重问题动真刀,办法都是“加强党的领导”老一套。人们于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变,执政党别自以为是,解剖别人之前请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闭幕的11月15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我们听到了总书记的响亮发声:“打铁还要自身硬”!对此各界有很多解读,联系到近一个多月来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强调反腐败,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看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明确表示: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呢?
同样的话今年广东省领导人也多次讲起,如政治局委员汪洋就坦言:“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并说: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省长朱小丹也明确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并说:“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领导人说,邓小平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后来朱F基总理也讲改革要闯雷区。但是,真要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党政干部自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谈何容易!
为什么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呢?是因为执政的党政干部自身问题很大且非常严重,有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也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棘手的利益格局等问题。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说明执政党不对自身开刀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化改革,敢于对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温家宝总理十八大前在广东所呼吁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并不先进,百年痼疾至今难以祛除
执政党自身问题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看一看ZG中央组织体系。
十八届一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另有中央侯补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等,其数总计约6百多人。这些机构即是现今中国最高权力实际之所在,这6百多人无疑也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员都是省部大军区级以上干部,他们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首脑、书记等;候补中央委员171人居其次,皆为副省级以上大官,他们大权在握,而又级别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以及政府各部与事业单位领辖的司局、处、科各级网状党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层系统。政府机构实行科层制并不希奇,这在世界各国都行用。但中国的权力体系却是以党为中心,党也科层官僚化了,且党政不分,这一套完全是移植于苏联,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乃至学校、医院等“单位”,都有党委党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书记挂帅当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都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形成集权一元化领导体制。
一整套的党政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乃至政治行为方式,都完全是外来的,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没有半点“中国特色”。如总书记、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国侯补委员等,连名词都来自苏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过是监察委员会的翻版,改了几个字,意思则完全是一样的。纪检监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前苏联也是一致的。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宁首创,其特征就是层层集权,使党领袖的命令能贯彻到基层党组织每一个人,实行分科分层的军事化管理。这个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列宁初提出来时就遭到党内反对,并引发党分裂。但列宁是在“地下党”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国家党无法公开合法活动的情势下,才强调严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以对付沙皇警察统治,这在当时还是有效果的。一战中沙皇统治崩溃,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能在乱中夺权,就证明了党的力量。按集权原则组织起来有严密纪律的党,被称为“列宁党”,起先是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或称革命党。然而,掌权执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国,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单位都实行集权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也要听党的,最后是政经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手里,这又被称为“斯大林体制”。列宁党和斯大林政体,就是所谓“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党政体制,无论是列宁党还是斯大林政体,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广泛质疑和批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孟什维克批评列宁党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与沙皇的专制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宁党是官僚组织。列宁虽作了种种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辩解,并骂考茨基为“叛徒”,但苏联建政后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现官僚制负面效应,使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官僚主义”问题严重。
托洛茨基则尖锐地指责党的“官僚化”,反对选举流于形式、层层任命、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批评“党内书记特权阶层”,“扼杀党的独立自由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而中央是官僚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行政命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对苏维埃政权很快被“党化”的政治现象提出批评。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政之初其实就很落后,与其吹嘘的“先进性”实相差万里。干部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贪污腐败,早在1921年列宁就提出贪污受贿是三大敌人之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要和腐败作斗争。
看来,ZG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诉说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并非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而是GCD国家的百年痼疾。百年来“苏联模式”的国家对此作过种种修正改革,但都失败了,苏联本身也已垮台。中国要走出新路,必须摒弃“苏联模式”,作出体制性的根本改变。
“苏联模式”不仅落后,而且虚伪、血醒!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肃反机关“契卡”,实行“红色恐怖”,自后直到灭亡也没有放松对人民的特务监控,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和实在的好处。列宁临死前也曾怀疑其体制,并试图加强监督,但他死后资历较浅资质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机关”当总书记,靠做琐屑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而掌握了苏联官僚体制机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层层集权,而拥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不久,即将不屑坐机关而愿演说钻研理论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党员,或驱逐或枪毙,进而扩大强化了党政官僚体制。中国GCD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上世纪30年代,就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南斯拉夫GCD政治局常委德热拉斯(MilovanDjilas)到苏联访问时,发现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事事处处讲“级别”,级别越高待遇越高,后来写了《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书,系统批判苏联体制的官僚“特权阶级”,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一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具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
GCD人德热拉斯后来遭到整肃,但毛泽东实际上是同意他的论述的。毛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肃“党内资产阶级”,并说“走资派还在走”,革命对象“就在GCD内”。毛用极左造反方式摧毁党政干部官僚体系,搞绝对平均,连工人“八级工资制”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应取缔。但他本人也不能严于解剖自己,在取缔所有人拿稿费的权利后,却保留了自己拿巨额稿费的特权,并“开后门”送自己亲属和“小女友”到北大历史系上学。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此前由其领导的“四清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农村多拿多占的“四不清”小干部官僚,是向GCD自己开刀。刘少奇将手术刀挥向小官,毛泽东将手术刀挥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则”,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寄希望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祈望“精神原子弹”能够发威,实际上是愚弄民众,搞个人崇拜耍权术,以“路线斗争”掩盖其权力争斗,对人不对体制,等级森严的干部官僚体制机制病害本身,并没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变本加厉,搞“一元化”领导。
百年历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热拉斯、毛泽东等,虽然身份、立场多有不同,但应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左右不同方面,都向GCD本身的官僚体制开炮开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泽东最为激烈。虽然毛发动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但毛后改革开放中,官僚主义、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的确是越演越烈,现在是已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习近平总书记诉说“全党必须警醒”的那些问题,绝非一时一地个别的现象,而是体制机制本质问题,是GCD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将苏联体制概括为“国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苏联模式的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苏联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苏联建立并没有开辟历史新纪元,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党政干部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马克思总结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要求全民普选,人人平等,没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重申了这些原则,建政之初说了不少空话大话。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东欧卫星国及中国,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原则落到实处,也无法落实。为了维护虚假的“人民政权”,苏联在建政之初就推行严厉的书报检查,1920年列宁将俄200多位顶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自后党的宣传部严密控制舆论,箝制思想。若开放报禁允许批评揭露,虚假的苏联政权就站不住。
苏联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个欺骗性制度。列宁最初提出的是“集权制”,并明确说党组织要象战斗“部队”,根本没有“民主”二字。只是因为党内马尔托夫等人的质疑,列宁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语,不过是修饰一下。强调军事化“服从-纪律”的“民主集权制”,在“地下党”时代行用情有可原,但执政后推向全国就产生了“国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权,自相矛盾本身就说不通,但却被吹嘘为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实际上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行集权专制之实。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实行过民主的,苏联垮台后在苏联东欧都重新推行议会民主。然我国执政党不但至今仍死抱苏联“地下党”时代的组织原则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和宪法,而且入党仍保留“地下党”时代的誓词:“严守党的机密!”都执政60多年了,几千万党员对十几亿非党群众,还能有什么“机密”可守?“地下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成了“人大”、“政协”这样公开的民意机关的组织原则,而且8个假党--所谓的“民主党派”,也如此照搬,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国却见怪不怪。其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层层服从,是把整个国家建成等级森严听从命令的大部队,体现的是典型的“国家官僚制”,是一个早已过时了的僵化落后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对象。
三、党政干部特权凝固化和“花钱买改革”
国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学者估计,我国官员之数是国民党统治时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为了掩盖官僚制统治,官僚称呼被改为“干部”,但无论是党的干部还是国家干部,都是按“级别”拿工资的,由国家财政供养,实际上是由人民供养。“级别”越高收入越高,且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也越多,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也拉得越大。按照GCD革命理论,劳动者打倒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当家作主再也不受剥削了。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农民都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工人虽比农民好,却难以和干部阶层攀比,工农权益实际上一直被剥夺。
苏联体制说穿了乃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党来收租税,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新阶级,劳动者是被统治被剥夺者的地位,并无实际改观,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因革命而扭转。早在列宁时期,苏联党政干部特权就已十分严重,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苏维埃高干“普遍地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的家属长期住疗养院,化国家的钱,图自己的享受;干部“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甚至有官员“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等等。这种寄生虫生活,与刚被他们打倒的地主资本家相比,又能有什么区别?到勃烈日阜蛲持问逼冢高干特权更是公开化普遍化。体制机制的全面僵化和党政干部特权的凝固化,使苏联病入膏肓,勃氏死后虽几经改革也不见起色,最后是亡党亡国。
苏联不行了,中国怎么办?“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而一路走来的中国GCD,该怎么办呢?应该说毛泽东、邓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须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文革极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马列口号喊得震天响,实质上是把专制老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请了回来。毛不加掩饰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搞赤裸裸的极权专制,党政军合一的“革命委员会”,较之苏联体制还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没饭吃,却封阿尔巴尼亚为“社会主义明灯”,而不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紧裤带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类”。可怜兮兮在专制禁锢下的亿万民众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干子弟簿希来、习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辈簿一波、习仲勋被关押。十年折腾,虽一片肃杀,但体制机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没有任何突破。
邓小平改革所谓“拨乱返正”,并不是将毛泽东极左“法家路线”复传统“秦政”的船头,拨回正统的苏联路线,而是拨向“右”,驶向西方!这一点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别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向西方学习”就被官方重新公开提倡,虽然向西方学习当时主要指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但在文革时谁敢说一句学美日英法?不管学什么,谁说谁准被打成反革命。
为什么要转而学西方呢?是因为其时东西方“和平竞赛”已初见分晓,中美日破冰后,邓小平等大员首次出国就被所见震惊,有S员说在日本看到的是“车水马龙”,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车“象蝗虫一样”,这就是现代化,连最保守的军头王震在英国也感叹,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他们象毛泽东一样,早已看不起落后的“老大哥”苏联,对僵化的苏联体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极左革命高潮时,就连台湾等“四小龙”都发达了,邓清醒地看到,中国已走进死胡同,故多次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之初把船头拨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邓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经济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学西方搞市场经济,成就极为巨大。政治上邓持重以维稳为要,但也说过50年后中国可以搞“普选”,改革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总体上是要与国际接轨,最终抛弃苏联模式。
但改革一开始就遇到强大阻力,以后阻力越来越大。阻力在哪?就在于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权阶层,即依照苏联模式在建国之初就遍布于党政军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干部“新阶级”。这些人在文革中虽吃尽了苦,刚提改革时他们并不反对,但一触及体制机制,就本能地抵制。这些人或亲身经历苏式红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义灌输自信是红色接班人,对苏联模式感情深厚,一听说取消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浑头火起,更不用说政治改革。邓小平要搞“棹头西”的改革,其实是很艰难的。据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这段话说得非常实在,也寓意深刻。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还原改革之初的内幕盘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启动之艰难。
我们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出现全民经商,干部下海,军队走私的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办的药厂“三九胃泰”,竟公开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做广告。对越南作战回国的部队,公然在马路上倒卖军用品做起了生意,时为营职干部现任上将的刘亚洲看见后,即给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信谏止。又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回忆,他当年任青岛市委书记,严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烟台、威海军队走私汽车他却管不了。江泽民被问及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时,爽快地回答说是禁止军队走私,给军队“吃皇粮”。朱F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先前我们难以理解“官倒”及军队走私,这种很难想象也难以启齿明显地危害国家的怪事,竟敢光天化日下公开干!通过纪坡民的点破,使我们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开放启动是多么多么的艰难!“新阶级”打不破绕不开,连邓小平也不敢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采取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给党政军官僚好处,“拉下水,一块搞”,让他们搞“官倒”当“富家翁”,才冲破阻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花钱买改革”。
怎样评价邓小平这一招呢?象历史上正面评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我们也应正面评价邓小平的作为。面对体制机制难题,邓敢作敢当,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绕过凝固化的官僚特权利益,成功启动了改革。改革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成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坚强后盾,就连林彪嫡系老部下原“四野”四纵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张万年,也高呼:“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严重,宋朝出现的“三冗”在中国现今也出现,所谓冗官、冗兵、冗费,邓小平虽对军队“消肿”,让军转干部到地方照样当官吃粮,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赘外,冗官冗费顽症始终革除不了。这其实也是“国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开放“花钱买改革”的形势下,干部官僚冗散腐败更是泛滥成灾。
花钱买改革,干部特权不敢碰,反而要着力维护,于是乎有了“顾问委员会”、“老干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谓“特供”,高干病房更遍地开花。《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301医院高干病房一个老干部的医疗费用,可以超过一个乡一个镇几万人所费,对已近植物人的高干的护理,可以不计成本。怵目惊心的数据说明,党政机构那是在为人民服务,全是在为干部官僚们自己服务。最近披露国家地震局经费仅千分之一用于预报业务,其余绝大部分用于养人盖楼房补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费”。各级政府有不少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安插冗员吃皇粮,如平原地区没有林木的县有林业局,从无地震的县也设地震局,且广设副职,有的干脆不上班“吃空饷”,当寄生虫,享受特权吃冤枉的干部无可计数。据ZG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4千多万,“吃皇粮”的达7千多万人,18个老百姓要供养一个官员。改革中有几千万工人下岗,但干部却几经“精简机构”也不见下岗者,无岗也得养着护着。中国的国家财政一半以上是用于养官,行政开支“超英赶美”,“三公消费”是天文数字。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说:“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公车私用也耗费了无数国脂民膏,其情形与王朝时代当官做老爷,出行要人抬轿,没有什么两样,反映的是体制性腐败。
出生延安的“高干子弟”陆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会上,痛心疾首地发言:“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陆德是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他出生时瘦弱难养,在艰苦环境下,是朱德总司令将自己那份牛奶省给他吃,才活了下来,为感谢朱老总其父给他取名陆德。这样的“官二代”,发言竟如此尖锐,是忧党忧国忧民!陆德把腐败性“三公消费”归结为“严重的封建残余”,是当年他的父辈奋力革命要铲除的东西,现在竟“愈演愈烈”,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陆德把官僚特权腐败归结到子虚乌有的“封建残余”头上,仍是在为体制开脱。我前面说过,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自建立伊始就没有“先进性”可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国家官僚制”病症,后来愈演愈烈是本身体制问题。“旧社会残余说”则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发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进的苏联不是官僚体制,诸多官场恶习乃旧社会遗留,其表现为官僚主义而非体制,以后会加以克服并越来越好;多数GCD人本质也是好的,个别党员腐败是受资产阶级侵蚀,经教育可以恢复“纯洁性”。据此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弹说”,重复布哈林的论调,说GCD人是“特殊材料织成的人”,个别人腐败是被阶级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所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吃懒做等都是旧社会的遗留,属于剥削阶级。这类自欺其人的说教现今是不值一驳,既然是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那么建国都60多年了,S着时间的推移,“遗留”本当越来越少,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了呢?可见绝非什么“遗留”。习近平说得好,“物必腐之,而后虫生”。问题的根本不在别人,而在于执政党本身,是自身腐烂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别人,改革的手术刀应该挥向自己。
四、不挥重刀革除“苏联模式”病体,中国就不会有出路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委实也不容易,但攻坚战还在后头。有人说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敢不敢改自己,必须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刮骨疗毒,除蛆祛病,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疴的“苏联模式”党政官僚病体不可小[,在中国,蚁附于体制吃饭的人太多,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干部特权利益凝固化,因而积重难返,自我改革的难度极大。就拿8200万GCD员来说,其数早已起过英、法全国总人口,而与德国总人口相当,不出几年可能达到1亿党员,成为世界奇观。这样庞大臃肿的党,又如何能称之为“先锋队”?上下都“与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个性只有党性,内部没有派别,只能是虚假现象,一致都听从中央领导,简直是装聋卖傻,荒唐可笑。入党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蝇营狗苟之徒,是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营私,以求晋身享受特权呢!8千多万党员中,有一半以上与权力沾边,是各级各类干部,他们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中国的事都会好办得多。可惜“先进性”、“纯洁性”这些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无法落到实处,再宣传教育也无用。
庞大的党政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表面上做一套,骨子里是另一套,他们最怕打破现状丧失特权,竭力“维稳”维护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设法阻碍实质性改革。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就出在党员干部身上,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是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国喊了20多年,就是难以推行。为什么呢?所谓技术上有难题是借口,老试点不推行是有意拖延。据说尉健行、吴官正任中纪委书记时还真抓了一下,官员们向中纪委报的身家几乎个个是百万千万,虽不贪污不受贿,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与马克思所谓干部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的标准差距太大,于是乎不敢公示了。因为一公示,马上就“坐实”了德热拉斯所谓普遍享有特权的“新阶级”的存在,是“走资派还在走”,党长期欺骗灌输的阶级“先进性”、“纯洁性”、“公仆说”等,都会马上露馅,对GCD的意识形态是颠覆性的,其势等于自杀!为此,ZG高层也很伤脑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终难以见公婆(人民),其执政合法性由此受到严词拷问和严酷挑战!连台湾马英九、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国领袖都公示家产,为何唯独ZG不敢公示呢,自称“先进性”的ZG党政官员,又有什么脸面面对治下的百姓?
然而,问题的根子其实还不在ZG,“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各苏式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敢于公示干部财产的。因为苏联体制的本质就是对大众的管制和欺骗,庞大的党员干部阶层是党国统治的基础,若不好好供着养着给点特权,金字塔型的庞大等级官僚体制马上就会轰然而垮。苏联垮台后,新生的俄罗斯马上就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得以和奥巴马一样,从容地公示自己的财产,而唯独中国不能。为什么中国不能,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上仍然坚守苏联模式,官员财产公开等于自找死路。不但官员个人财产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门行政开支、三公消费等,也不敢透明公开。在当今中国连改革也要花钱来买,入党当官多是为了捞好处,在广大农村有众多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并没有什么国家干部编制,但每月也是要领钱的,国家转移支付给农村的扶贫款,也大多转入了员外干部的腰包。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具其所吹嘘的“先进性”,甚至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如现今法学界与民众广泛诟病的“劳教”制度,也是移植于苏联。党政官僚腐败是体制性的,其所有问题在前苏联东欧都早就频频发生,且根治不了。因而,并非揭发审判百十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体制机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苏联模式。
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全民党说法,制度上取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总书记任期现在确定为两届,掌政仅10年,老干部虽养尊处优,但确立了其放权离休退休制度。能做到这些,也确实不容易。ZG十八大对干部腐败等问题,也提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习近平表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将改革的手术刀对准党自身,“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11月19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要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官僚主义风气,强调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ZG新领导层一上任就着力部署反腐工作,号召讲真话干实事,不搞官场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不讲空话套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表现出重启改革的新锐之气,一时备受各界关注。但我认为,要做的事还多,重任重压挑战考验还在后头。
改革不能只限于反腐做表面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当今中国的改革实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国家官僚制”已积重难返,已经成为当今改革的主要对象。党政不分金字塔型的党国体制浑身长满了毒瘤,贪污腐败是毒瘤,高额“三公消费”是毒瘤,高干病房是毒瘤,干部特供是毒瘤,老干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挥刀将其割除之。另外,苏联模式的政治行为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政治局、书记处等一套集权方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要逐渐革除变换,代之以民主宪政。执政党要在宪法框架下执政,允许人民监督,允许反对者说话,政务公开,阳光执政,改革体制机制,彻底剔除腐朽苏联那一套。
但我国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大框架上仍然坚持苏联政治模式,其中一条即是坚持列宁主义,对已自取灭亡的苏联模式不敢彻底否定,依赖既定路径,仍坚守封闭落后的苏式党政官僚体制机制,甚至不服输摆出反帝反资姿态,变换花样搞意识形态斗争。前文提到的红二代陆德忧党忧国心肺俱焚,他在提到解决危局的办法时,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集中制乃地下党时的组织原则,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欺骗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靠强化组织纪律,强化旧体制机制,根本就不会有出路。
本来,苏联垮台自己也已彻底否定了自己,哪为什么我国还在坚守呢?答曰:怕体制崩溃会乱,所以要“维稳”,要竭力维护既有利益格局。于是有人公开说:不要把老干部逼到墙角!老干部局千万要把离退休老人照顾好,高干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学者提出所谓“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说,在路径锁定不触犯权贵“存量”利益的基础上,只对“增量”蛋糕进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党政干部官僚集团,连邓小平都动弹不得,谁还能动?只有在承认和优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国推行改革。如此这样的“增量民主”,实际上是花钱买民主。还有人提出花钱买宪政的“党主宪政”说,试图在承认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乞求党能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执政党能在宪法框架下行使权力。又有人提出:“对一些高层贪污官员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他们对官员财产公示制的支持,“以减轻那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减轻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对此,学界还有过一番讨论,仍然是“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的思路。
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花钱买民主、花钱买宪政、花钱买官员财产公示等,乍听起来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并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用赎买来减少改革阻力,以妥协换取既得利益者让步,若真能推动改革,也是可圈可点。天价维稳也确实买到了几年稳定,当然,花费的天价都是纳税人老百姓埋单。中国百姓乃是最坚忍最驯服的百姓,为此广大民众忍气吞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执政当局似乎并不买账服软,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就曾盛气凌人地“郑重”宣告所谓“五不搞”,其执拗与清末新政改革关键时刻朝廷宣布“五不议”,有得一比,对松动体制放权让利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对宪政民主没有半点妥协的空间,仍然坚持列宁党斯大林政体不动摇。明知苏联垮台其制其路错了,为保特权也要坚守列宁斯大林创立的政治行为方式,仍然是枪杆子笔杆子“二杆子”干革命,一手拿枪维稳镇压,一手握笔欺瞒蒙骗,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苏式“二杆子”革命政权其实相当脆弱,苏联70年主要是靠强力镇压和谎言维持,对思想管制更尤为坚决,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书报检查,在列宁那里根本就不加理睬,其建政之初就严厉推行党禁报禁。这一点在中国也贯彻得相当彻底,至今也未见松动迹象,为掩饰遮羞花钱养了8个假党,“肝胆相照”充当花瓶,“多党合作”尤如演戏,虽演技极其拙劣,却至今仍在假戏真做;中宣部对报刊媒体的强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党管舆论”,为什么要管制舆论呢?就是因为自身太虚假,生怕有人揭穿影响其“维稳”大业。苏联政体的欺骗本质,苏联人自己也有很好的总结,苏联垮台前夕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总理雷日科夫总结得最明白清楚:“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方面为彼此佩戴勋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一个政体,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若马克思在世未必会认同,“中国特色”也很难说就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以俄为师”搞“二杆子”革命,移植苏联模式,可以说是吃了大亏上了大当,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辙而死不回头,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而要将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政治统治或管理体制形成以后,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形成现存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们吃体制饭,力求巩固既有制度,阻碍一切改变现状的变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种改革,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变换手法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权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苏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命60年红色江山,从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几千万人,他们死也不肯承认苏联垮台红色革命破产的铁的事实,对苏联体制情有独钟,死抱意识形态“唱红”企盼“革命高潮”的到来,实际上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顾自己特权不失。当今改革最大阻力就是特权凝固化的干部“新阶级”,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横亘在改革之路上要买路钱,谁也得罪他们不起,中国要改革必须正视他们,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同意。干部官僚“新阶级”是百年苏式革命的产物和获利者,是共产政治的百年难题,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嫡传弟子考茨基、卢森堡就对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中国改革的“老大难”。
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必须改变现存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苏联模式旧体制,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体制动手术!在经济上抛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也要抛弃苏联那一套,否则,就难有作为。如今改革是不进则退,前程充满荆棘,成败难以预料,搞得好,可以走向民主宪政均富的光明大道,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动乱,轮回到毛式不断革命的陷阱,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可能万劫不复。这就要求改革者能放下身段,不再固步自封,多倾听人民的声音,少计较自身得失,首先是要在思想上冲破一切禁区,敢于反思自身革命历史,盘算新的出路。ZG十八大召开后,人们对新任总书记及其执政团队寄予了无限希望,希望改革有新的思维,能开创新的局面。旧式高压和天价维稳难以持久,花钱摆平各种复杂矛盾实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今的改革,必须向体制开刀,解决集权专制而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问题,实行民主宪政。所谓宪政,就是限政,宪法是限定政府的权力,界定人民的权利,对此GCD表面上并不反对,实际上却不遵循。凡事总是高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而要加强领导,必然是强化旧体制旧机制,用的是效用递减的老把式,不但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可能走向反面。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又必然要扩大强化组织,要增加费用,这又为寻租腐败陡然增加了空间,冗官冗费于是恶性循环。
党的领导还有没有限度,党一定就要凌驾于国会宪法之上吗,加强党的领导到底还能强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方式,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放松放松党的领导呢?对此,海峡对岸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老同学蒋经国,在台湾政改转型关键时刻的两句话,很有启发意义。其第一句话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其第二句话是:“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侯不去用它”。经国先生也是高干子弟“官二代”,也移植苏联模式列宁党“民主集权制”,搞过高压统治,但在宪政转型紧要关头,却能以大无畏的勇气,告别苏式一党专政。他下这个决心一定也很难,也要顾及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宪干部既得利益集团,然一旦冲破了思想禁区,想清楚了下了决心,就义无返顾地与旧体制告别,踏上了宪政新坦途,而天也并没有塌下来。其上述两句话,也成了政治名言,成为中华民族政改的经典。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推行宪政,就会马上天下大乱,但我看是不会的,相反,不改革长期高压天价维稳,反而有崩解的危险。
当然,政改牵涉面多很复杂,并非易事,还是要有序进行。首先,是要转变观念,要下大决心,敢于冲破思想牢笼。这就要求执政党要有新思维、新的政治观念,要继续解放思想,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己的前途,探索新的出路,不再依赖既定路径,死抱已经灭亡的苏联模式不放,不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新领导层要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敢于放松控制,告别旧体制旧机制,探索新体制新机制,大刀阔斧地割除自身毒瘤,破除改革阻力。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S即“南巡”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发话说:“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下一步改革,表示了很大决心。ZG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也让大家读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体制内党员干部亦可谓是意味深长。改革将决定中国命运,改良和革命从来就是世界各国政治变革的两个关口,未来5年至10年对中国十分关键,不会再有更多的时间任由当政者以高压和天价维稳了!稳与不稳在于改革,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改革者须抓紧时机,勇闯禁忌,主动告别政治垄断,化被动为主动。在新一轮改革中,直面亿万民众,多一些让步妥协,开诚心,布公道,公开性,讲真话,干实事,勇开拓,彻底放弃令人作呕的苏联欺骗性政体和政治行为方式,切切实实地推进宪政民主,避免革命动荡,力争改革的最好前景。
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二元的经济结构和二元户藉制度不改变,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就不会改变,社会乱象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为此,当前调结构是关键,是激发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基础。
如果不满足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要求,领导人就不可能无限期执政下去。与GDP增速相比,中国中产阶级更关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清廉的政府和安全的食品。
在经历了30年的非凡经济扩张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失去动力,如果中国经济急剧放缓,ZG就将失去其最具说服力的合法性来源。如果中国采取主动,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或许会像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台湾与韩国一样,朝着更加多元和民主的体制和平转型。
许多党内和党外人士担心,如果还用老一套的压制工具来压制民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新领导层总有一天会如梦方醒地发现,民众全都走上了街头。沈志华说:“新本届领导班子为中国实施(向更自由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最后的机会,这一转型来自党内和体制内。如果不实施这些改革,社会肯定会爆发动乱。”
三十年来,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了社会人格道德的分裂;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导致了民族人文精神的断裂。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有许多砖家叫兽已沦落为既得利益者豢养的鹰犬,已堕落为既得利益阶层看家护院的家丁,看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个社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精神麻木,心灵污染,心理扭曲,精华无存,糟粕遍地,垃圾充斥,太需要呐喊式的强音了。
QUOTE(yake @ 2013年10月13日 Sunday, 01:58 PM)
三十年来,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了社会人格道德的分裂;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导致了民族人文精神的断裂。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有许多砖家叫兽已沦落为既得利益者豢养的鹰犬,已堕落为既得利益阶层看家护院的家丁,看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个社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精神麻木,心灵污染,心理扭曲,精华无存,糟粕遍地,垃圾充斥,太需要呐喊式的强音了。
[snapback]3589456[/snapback]
利益集团要的是利益,是促进自身利益的改革,不是要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
深化改革,无疑与虎谋皮,损害利益的事,既得利益者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