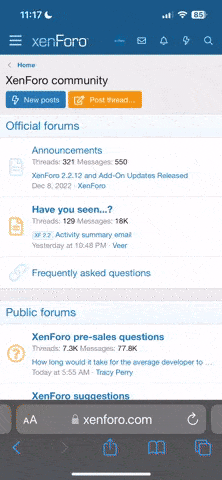http://view.news.qq.com/a/20080524/000002.htm
双面地震
“把那个底色调成灰的”、“花上面加一片绿叶?嗯,很好”――我在和页面设计人员商讨着,这是一个祭奠地震遇难孩子的页面,“要从中看到希望”,我一开始就这样定调,但是我看到第一版设计的时候,不禁皱眉――“这毕竟是一场悲剧,打个比方,我要看到绿色,但那也应该是冬天里的松柏,你不能直接就搞成花繁叶茂的春天”,我想要一个绝望中带有希望,但欣慰中又不能忘掉悲情本色的感觉。
就如同眼前这第一版页面,最近我只是看到了太多的希望,这些希望被施以浓墨重彩,描写的具体详细,而悲情呢?不是没有,只是大开大阖,非常抽象,特别到这几天救生收尾,看那电视,已经不是“悲情中的希望”,而是有向喜剧转化的征兆了。
在我上第一堂新闻培训课时,讲师就反复强调“温暖”,我记下了,并且循此发现了一些很好的报道,最近一次留有深刻印象的是06年一篇采访克拉玛依大火时一位在场领导的,当年及以后的十几年,不管是媒体还是人们的感官都被“让领导先走”占据,却没人知道不是所有领导都先走了,也有领导指挥疏散,落下严重残疾,还遭遇牢狱之灾。这篇报道就让我感觉“温暖”――人性没有灭绝,黑暗中也有光辉。
回到这次地震,我看了无数报道――影像的、文字的,老感觉缺点什么,后来恍然大悟,感情记者们都忙着寻找“温暖”去了,至于悲剧,只知道“很惨”,缺乏具体的、有感染力的描述。
这里我要说,随着经验增长,我慢慢发现那堂“温暖”课有问题,新闻的本质,其实不是发现“温暖”,而是发现“不一样”――在坏事中寻美,在好事中揭丑。所谓发现“温暖”,大抵是因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一般是假丑恶,所以要从中发掘出真善美,更能吸引读者。
大灾难即是大悲剧,但人的眼睛需要看到不一样,于是人们努力发现悲情中的温暖、绝望中的希望、无力中的有力、黑暗中的光辉,这是正常的。但这不意味着另一个极端:将记录变为抽象的悲剧+具体的感动,悲剧也应该是具体的,不能用宏观的寥寥几笔带过,就步入“好的方面”。
本来,媒体会自觉地去做这件事,记录感动的多了,自然就会有人去挖掘丑陋,寻找“你所不知”的“另一面”,所以最终我们就从“双面”的平衡中去接近真实。但是,有了“舆论导向”后,这样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连我这个干这行的都“中毒”了。
黄思雨,一个初中女孩,媒体给她以“坚强”、“勇敢”的面貌,我当时看了也暗赞――“这个孩子真勇敢”,没过两天,又在《南都》上看到描写一个孩子的,说“她躺在成都华西医院,病房谢绝打扰。‘余震、风雨,还有闪光灯,都会让她烦躁’,负责看护她的志愿者、重庆姑娘但文静挡在门口,拒绝采访的态度,像保护奥运火炬一样坚决。心理干预试图进行,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医生成功接近过黄思雨。她总是说,‘走开’”。
“黄思雨”,这不就是那个勇敢的孩子吗,可现在很显然:她的心理有了大问题。我拍一下脑门:一个小女孩,父母下落不明,很可能会成为孤儿,失去了一条腿……。什么“坚强勇敢”,在残酷事实面前这些说辞虚弱不堪,我甚至想到了灾难之神对人类这点嘴上的不服软发出耻笑。当然,我不反对你用任何美好的词语去安慰伤者,但千万别搞成这样――请看《截肢少年马聪》。而对于我们这些没受灾的人,就少点精神按摩吧,让我们体味个体的真实命运更好。
遗憾的是,我目力所及,竟然只看到《截肢少年马聪》这样一篇详细描写个体命运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记者们还停留在记录灾难的阶段,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灾难中个体的生离死别。救生工作结束后,灾民的个体描述就少了,只看到哪里复课了,哪里的安置点添了风扇,然后听了很多“重建家园”的声音,但这声音里没有灾民的看法。仅有的一点描写,其中多半篇幅用在了孩子身上,你想看孤老的、中年人的,很难找,找到了也基本是按部就班:灾难中的坚强+对未来有希望,也就是说把个体命运融入到“汶川挺住、四川雄起、中国加油”的国家、民族叙事里,或者说把国家意志强加到了个体命运中。
很显然,我们对灾民聚焦不够,而对没受灾的人又安慰过多。当我们说“守望相助”时,其实是没受灾的群体在“守望相助”,灾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当我们说“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时,你的表现让我觉得你还是你,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怒吼着质问“为什么没有预测(当然科学的讲地震还无法预测)”、“豆腐渣工程害死我儿!”,而不会说“让我们先放下批评”;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抱怨“为什么五天都没人送吃的来”,而不是“很周到、很满意”;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催促救援的人“快点,为什么这么慢”,而不是称赞“神兵天降”,“有序有效”。
当然,这不怪你,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悲剧的具体细节,没有接近真实的报道,又如何能与灾民“同呼吸”?如今,与灾民“心连心”更不可能了,因为从电视上看,仿佛他们的苦难也随救生工作的结束一起打住。而人们喊着“中国加油”,迅速的走向振奋民族精神的新起点。
坏事中可以挖掘一些亮点,坏事可以推动一些进步,但灾难的苦痛,最终还得由具体的个体承担,那些亮点和进步掩盖不了他们的实在痛苦,我们局外人能分担的也微不足道。一出无奈的悲剧,才是本质。
那么那些感动呢?我要说,除了像“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下来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这样明显编造的,记者们写的感动故事也未必可信,但我可以肯定:真实的感动一定无处不在,一定数不胜数,是的,少了才怪呢。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人性的善良被召唤出来有什么奇怪的,连一些平时鱼肉乡里的地方官员,那面目也可亲可敬呢,但这毕竟是“扭曲”的状态,“扭曲”很快会复原,大灾难对人性的洗礼会维持多久、改变几何,未可知呢。即便是在人性向善的大基调下,“世间百态、人性百态”的本质也未改变,那些趁火打劫、借机揩油的还少吗?
“叔叔,你先救他们吧”,这样的新闻大家一定看过,好像还有“叔叔,我将来要考军校”,这都被当作孩子的礼让和坚强加以赞美,但在另外的版本里,也有相反的情形:两个男孩被压在川北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男孩消极的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当然,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恶劣。
在死亡威胁面前,有礼让,也有如抢物资、抢逃生路,这都有报道。
至于奇迹,本来是最悲的一节。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当然是后者。但如果你的眼里只有那几个生还者,那感受就相反了,你甚至会把这当成喜剧和胜利,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
奇迹意味着死神对极个别手下留情,而对绝大多数照单全收,这几个“意外”让我们得意忘形,甚至以为夺取了死神的主导权,说出了“胜利”的昏话。而实际因为救援难度,因为经验和能力的不足,因为救援不能及时展开,尽管有90小时、10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奇迹,但整个局面还是没有脱离常态:第一天,这里呼救声此起彼伏;第三天,一切都归于寂静……
电视画面里不断播放奇迹,但要认真回想一下,好像播来播去也就那么几个镜头。但每当一个被压的人从废墟中被托出,看着几十双手做出伸向他的动作(我甚至阴暗的想,抬一个人需要那么多手吗),看着白大褂一拥而上,输氧的输氧,吊瓶的吊瓶,我还是觉得我们很好很强大,直到看了“陈坚之死”。这是四川台的节目,那位小伙被实实的压在预制板下,记者在有条不紊的采访他(看着他被压的情形,我真想跳进电视里揍那个记者,但看他神志清楚,说话正常,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我觉得这人不幸中万幸,捡回一条命。但接下来急转直下,他最终被救了出来,嘴里不停的哼哼,但他身边没有白大褂,没有吊瓶,不一会,还是去了。后来我看专家说被压得久了不能突然把重物移开,我不知道救援人员知不知道这点,可即便知道,他们身边没有医护人员,也是白搭。这段节目让我知道了其实我们不好不强大,事后有报道显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救出后没人管,最终还是走了。
有幸的是,我想看到的报道并未绝迹,但比例远远不够,以至于不是我这样的媒体人,可能脑海里永远不会有奇迹旁边万骨枯的景象。
双面地震
“把那个底色调成灰的”、“花上面加一片绿叶?嗯,很好”――我在和页面设计人员商讨着,这是一个祭奠地震遇难孩子的页面,“要从中看到希望”,我一开始就这样定调,但是我看到第一版设计的时候,不禁皱眉――“这毕竟是一场悲剧,打个比方,我要看到绿色,但那也应该是冬天里的松柏,你不能直接就搞成花繁叶茂的春天”,我想要一个绝望中带有希望,但欣慰中又不能忘掉悲情本色的感觉。
就如同眼前这第一版页面,最近我只是看到了太多的希望,这些希望被施以浓墨重彩,描写的具体详细,而悲情呢?不是没有,只是大开大阖,非常抽象,特别到这几天救生收尾,看那电视,已经不是“悲情中的希望”,而是有向喜剧转化的征兆了。
在我上第一堂新闻培训课时,讲师就反复强调“温暖”,我记下了,并且循此发现了一些很好的报道,最近一次留有深刻印象的是06年一篇采访克拉玛依大火时一位在场领导的,当年及以后的十几年,不管是媒体还是人们的感官都被“让领导先走”占据,却没人知道不是所有领导都先走了,也有领导指挥疏散,落下严重残疾,还遭遇牢狱之灾。这篇报道就让我感觉“温暖”――人性没有灭绝,黑暗中也有光辉。
回到这次地震,我看了无数报道――影像的、文字的,老感觉缺点什么,后来恍然大悟,感情记者们都忙着寻找“温暖”去了,至于悲剧,只知道“很惨”,缺乏具体的、有感染力的描述。
这里我要说,随着经验增长,我慢慢发现那堂“温暖”课有问题,新闻的本质,其实不是发现“温暖”,而是发现“不一样”――在坏事中寻美,在好事中揭丑。所谓发现“温暖”,大抵是因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一般是假丑恶,所以要从中发掘出真善美,更能吸引读者。
大灾难即是大悲剧,但人的眼睛需要看到不一样,于是人们努力发现悲情中的温暖、绝望中的希望、无力中的有力、黑暗中的光辉,这是正常的。但这不意味着另一个极端:将记录变为抽象的悲剧+具体的感动,悲剧也应该是具体的,不能用宏观的寥寥几笔带过,就步入“好的方面”。
本来,媒体会自觉地去做这件事,记录感动的多了,自然就会有人去挖掘丑陋,寻找“你所不知”的“另一面”,所以最终我们就从“双面”的平衡中去接近真实。但是,有了“舆论导向”后,这样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连我这个干这行的都“中毒”了。
黄思雨,一个初中女孩,媒体给她以“坚强”、“勇敢”的面貌,我当时看了也暗赞――“这个孩子真勇敢”,没过两天,又在《南都》上看到描写一个孩子的,说“她躺在成都华西医院,病房谢绝打扰。‘余震、风雨,还有闪光灯,都会让她烦躁’,负责看护她的志愿者、重庆姑娘但文静挡在门口,拒绝采访的态度,像保护奥运火炬一样坚决。心理干预试图进行,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医生成功接近过黄思雨。她总是说,‘走开’”。
“黄思雨”,这不就是那个勇敢的孩子吗,可现在很显然:她的心理有了大问题。我拍一下脑门:一个小女孩,父母下落不明,很可能会成为孤儿,失去了一条腿……。什么“坚强勇敢”,在残酷事实面前这些说辞虚弱不堪,我甚至想到了灾难之神对人类这点嘴上的不服软发出耻笑。当然,我不反对你用任何美好的词语去安慰伤者,但千万别搞成这样――请看《截肢少年马聪》。而对于我们这些没受灾的人,就少点精神按摩吧,让我们体味个体的真实命运更好。
遗憾的是,我目力所及,竟然只看到《截肢少年马聪》这样一篇详细描写个体命运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记者们还停留在记录灾难的阶段,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灾难中个体的生离死别。救生工作结束后,灾民的个体描述就少了,只看到哪里复课了,哪里的安置点添了风扇,然后听了很多“重建家园”的声音,但这声音里没有灾民的看法。仅有的一点描写,其中多半篇幅用在了孩子身上,你想看孤老的、中年人的,很难找,找到了也基本是按部就班:灾难中的坚强+对未来有希望,也就是说把个体命运融入到“汶川挺住、四川雄起、中国加油”的国家、民族叙事里,或者说把国家意志强加到了个体命运中。
很显然,我们对灾民聚焦不够,而对没受灾的人又安慰过多。当我们说“守望相助”时,其实是没受灾的群体在“守望相助”,灾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当我们说“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时,你的表现让我觉得你还是你,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怒吼着质问“为什么没有预测(当然科学的讲地震还无法预测)”、“豆腐渣工程害死我儿!”,而不会说“让我们先放下批评”;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抱怨“为什么五天都没人送吃的来”,而不是“很周到、很满意”;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催促救援的人“快点,为什么这么慢”,而不是称赞“神兵天降”,“有序有效”。
当然,这不怪你,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悲剧的具体细节,没有接近真实的报道,又如何能与灾民“同呼吸”?如今,与灾民“心连心”更不可能了,因为从电视上看,仿佛他们的苦难也随救生工作的结束一起打住。而人们喊着“中国加油”,迅速的走向振奋民族精神的新起点。
坏事中可以挖掘一些亮点,坏事可以推动一些进步,但灾难的苦痛,最终还得由具体的个体承担,那些亮点和进步掩盖不了他们的实在痛苦,我们局外人能分担的也微不足道。一出无奈的悲剧,才是本质。
那么那些感动呢?我要说,除了像“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下来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这样明显编造的,记者们写的感动故事也未必可信,但我可以肯定:真实的感动一定无处不在,一定数不胜数,是的,少了才怪呢。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人性的善良被召唤出来有什么奇怪的,连一些平时鱼肉乡里的地方官员,那面目也可亲可敬呢,但这毕竟是“扭曲”的状态,“扭曲”很快会复原,大灾难对人性的洗礼会维持多久、改变几何,未可知呢。即便是在人性向善的大基调下,“世间百态、人性百态”的本质也未改变,那些趁火打劫、借机揩油的还少吗?
“叔叔,你先救他们吧”,这样的新闻大家一定看过,好像还有“叔叔,我将来要考军校”,这都被当作孩子的礼让和坚强加以赞美,但在另外的版本里,也有相反的情形:两个男孩被压在川北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男孩消极的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当然,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恶劣。
在死亡威胁面前,有礼让,也有如抢物资、抢逃生路,这都有报道。
至于奇迹,本来是最悲的一节。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当然是后者。但如果你的眼里只有那几个生还者,那感受就相反了,你甚至会把这当成喜剧和胜利,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
奇迹意味着死神对极个别手下留情,而对绝大多数照单全收,这几个“意外”让我们得意忘形,甚至以为夺取了死神的主导权,说出了“胜利”的昏话。而实际因为救援难度,因为经验和能力的不足,因为救援不能及时展开,尽管有90小时、10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奇迹,但整个局面还是没有脱离常态:第一天,这里呼救声此起彼伏;第三天,一切都归于寂静……
电视画面里不断播放奇迹,但要认真回想一下,好像播来播去也就那么几个镜头。但每当一个被压的人从废墟中被托出,看着几十双手做出伸向他的动作(我甚至阴暗的想,抬一个人需要那么多手吗),看着白大褂一拥而上,输氧的输氧,吊瓶的吊瓶,我还是觉得我们很好很强大,直到看了“陈坚之死”。这是四川台的节目,那位小伙被实实的压在预制板下,记者在有条不紊的采访他(看着他被压的情形,我真想跳进电视里揍那个记者,但看他神志清楚,说话正常,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我觉得这人不幸中万幸,捡回一条命。但接下来急转直下,他最终被救了出来,嘴里不停的哼哼,但他身边没有白大褂,没有吊瓶,不一会,还是去了。后来我看专家说被压得久了不能突然把重物移开,我不知道救援人员知不知道这点,可即便知道,他们身边没有医护人员,也是白搭。这段节目让我知道了其实我们不好不强大,事后有报道显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救出后没人管,最终还是走了。
有幸的是,我想看到的报道并未绝迹,但比例远远不够,以至于不是我这样的媒体人,可能脑海里永远不会有奇迹旁边万骨枯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