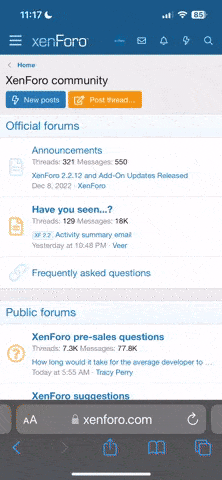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往 事 不 堪 回 首 忆 -----记苦命人吕英 (1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tianya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06-09-25
- 帖子
- 25,094
- 反馈评分
- 766
- 点数
- 191
往 事 不 堪 回 首 忆
---记 苦 命 人 吕 英
陈贞/文
广东茂名县浮山岭的山下乡村出过历史名人:羽衣蹁跹的道士、名医潘茂名,在民国政军舞台呼风唤雨的 巾帼英雄莫秀英、吉林省省长梁华盛、国军军长莫福如。这些名人各自留下了被后世传颂的故事,更多的是小人物像秋风刮下的一片片枯叶消失在泥土里,无声无息,有的小人物却因经历催人泪落而引起后世的关注,同情。
浮山岭的北麓是茂名县分界茅坡村,1957年,吕英,一个的17岁姑娘由根子嫁到了这里,她和年纪相差两岁的丈夫都生于地主家庭。对多数人来说,生命本来应是一条长长的弯曲山路,路边蝶落初尘花盛妍 ,果实累累,该好好观赏才是,但吕英仿佛注定这一生凄风苦雨。不到一年,吕英的丈夫病逝。婆家四壁空空,生活难以为继,时年18岁的她饥肠辘辘,出门觅食,顺着远方的坡园翻红薯泥,喝沟水,饿一餐、饱一餐,夜宿草舍,终于在距离故乡60公里远的东南面电白马踏公社的一条村庄找到了归宿地,她自嫁的富农成分的杨家长子,这对年轻人同病相怜。插秧、割稻、打禾、养猪、养家禽、挑大粪、挖河泥……她干过任何粗重的农活。夫妇俩芭蕉开花――一条心,犹如春天的蜜蜂闲不住,每天为生计而劳作。 虽然生活清贫,但他(她)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重新获得爱的18岁女人,有了男人的滋润,有了一间可以遮雨挡光栖身的茅屋,随着两个男孩子的相继出生,家庭有欢声笑语,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心情舒畅的吕英 逐渐丰腴起来了,犹若六月荷花------众人共赏。
1968年7月底,革总司首领吴XX等人从水东码头乘坐汽艇窜到电白县电城镇开黑会,出席人员是县内各地司派小头目,吴在会上胡言,核狗(对核派组织的蔑称)与乡村的地主富农相勾结,妄图复辟变天,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一个核狗或地富分子等于开荒三亩地......吴要求各公社(公社今改为镇)捕杀这类人员。电白马踏公社司派头目许栖、杨蹈j 秉承吴XX的黑旨意,迅速在境内掀起一股杀害无辜者的恶浪,指使下面大队领导率领民兵分赴各个自然村消灭阶级敌人---黑五类 。
仅相距两三天,吕英的丈夫、家公、家婆、2个小叔子、2个儿子与马踏公社各条村庄的数百黑五类先后被杀。吕英的丈夫被多位凶手用稻插叉捅伤,诸处伤口血流如注, 疼得打滚,哀求用枪打.....。吕英是年28岁,她在这桩几乎是满门抄斩的血案中活了下来。几天后,一个大队干部登门,这位不速之客对吕英说:“你获得党的宽大处理,完全是我的功劳。你再留在这里既穷又衰,如果再来一次清理阶级队伍,你就插翅难飞 。”在毛泽东时代,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迁徙,外出要凭路条,吕英等同毛驴拉磨,走不出这个圈,随时有血光之灾 ,但胆小,泪痕斑斑的吕英沉默以对。 大队干部见状,便安慰开导她:“我妻子的哥哥张某是马踏公社邻村的人,从来没结过婚,虽然今年只有48岁,但身体很好,而且家庭成分是贫农,我是他的亲戚,我是贫农成份的GCD干部,谁人都不敢欺负我的内兄。如果你肯嫁给他,那么你的生活有依靠,而且生的子女可随父亲的贫农成份。”贴上贫农标签的人能平平安安,而出身所谓剥削阶级的人自然是命如蝼蚁,不久前,至亲和其他地主、富农尸横野外的情景,让刚回过神来的吕英依旧感觉很恐怖,这名干部其实也是这个杀人组织的骨干,树上的乌鸦,圈里的肥猪---一色货 ,但他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话还是让吕英心有触动 !吕英又看见大杀阶级敌人的现象暂停了,可偶尔有五类分子的子孙被捉去斗争时而被打死的消息传来,为了求生,明知是茅坑里放玫瑰花,明知此人大自己20岁,双方出身社会背景不同,教养有别,不可能建立感情,今后还要与此人繁殖后代,恶心到想吐啊,可她经受不起对方的连哄带吓,终于违心地嫁给了张某。
婚前,吕英并不了解张某的人品。
1952年,电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张某32岁,力大,粗野庸俗,心肠歹毒, 群众见过他对地主、富农张牙舞爪的样子,他吊打这些农民的“吸血鬼”很卖力,他倚仗土改工作组的权势,强迫过几个风韵犹存的地主婆与之上床,以换取对他们夫妇手下留情;同村的王家少女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在淫棍张某的眼里:春茶尖儿---又鲜又嫩。机会来了,因王家评了地主成份,张某以此胁迫她上床.....老虎来了盖被单―― 挡不住, 这位满嘴臭气的老男活像一头发情的畜牲一样扑过去,片刻这名少女成了剥皮的青藤――一丝不挂,在她身上拱起来,摸起来,又似老鸭下水嘴上前啄食,口水滴到这个少女的脸蛋、嘴唇......。次年,王姓父母饿死,便嫁给一个休妻的小学罗老师。罗比王女大10岁。行房之夜,罗老师发现妻子不是处女,追问之下,妻子道出实情。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个正义感的乡官,乃撤了张某村官的职。张某臭名昭著,加上好逸恶劳,所以48岁仍无妻室。罗老师对妻子冷若冰霜,且打骂不断,王女多次跪求丈夫不要计较前嫌,但罗始终不为所动......1955年春,18岁的小王净身出门,只携带几斤生番薯,步行200多公里到雷州半岛海康县天竺庵出家,主持接纳了这位可怜的少妇。从此,这名少妇在他乡削发为尼,与青灯做伴,朝夕念经,她希望慢慢老去,终于有一天能像一朵花儿零落成泥碾做尘,做异域的孤魂。
等到看穿张某的真面目后,生米已煮熟饭。那个时代,吕英无智慧、无勇气、无力量挣脱人家为她戴上的命运枷锁。
1969年---1971年,吕英为衣冠禽兽的张姓丈夫连生两子,但二子的性情酷似乃父,游手好闲,全是破风筝---抖不起来。他们确是可以跟随父亲的成份。吕英看见后夫比不上前夫,后夫的二子更是样样比不上前夫的二子,乃经常伤心,“情如花逝空遗恨,泪过素颜留红痕 ”,吕英眼眸中闪出的那一抹悲伤,是对前夫残留在她心底的爱。
1998年7月某日,既是前夫60周岁的阴诞日,又是前夫含冤去世30周年的忌日,58岁的吕英备了少许祭品去附近的庙里为亡夫敬香,不意此事为后夫发觉。吕英回到家里,后夫横眉瞪目,恨其旧情不散,多少年来抱着妻子这尊菩萨亲嘴――都是一头热乎,乃不顾已78岁高龄的病弱身躯,举粗棒对妻子一顿狠打,吕英头部被打得血流如注、伤及内脏,卷缩地上呻吟不已,当夜即死,而他因对妻子偷祭杨姓前夫一事气恨交加,对妻子往死里打时用力太猛,所以不久也被阎罗王召去。
吕英当年在那位“好心人”的力保下,幸免于死 ,多活了30年,但最终还是惨死在这个恶夫的暴力下。吕英三嫁,真像“ 中药店里的揩布,揩来揩去都是苦” ,佛教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按马列主义无神论,她永远没机会回“岸”了,因为生命没有轮回。而王姓地主妹出家11年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号召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海康县红卫兵砸毁她所在的尼姑庵,其本人被轮暴,乃抱一只观音菩萨悲愤地投水自杀。
有一个人提起了当年的惨事,说他所在的(马踏公社)那条村庄“ 也是重灾区。当晚8、9时左右,(大队)民兵(奉命)押地主老少出村到刑场。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小孩子跟随大人走到村头,突然对大人说:‘爷爷,我把木屐放在路边,等回来时再穿。”其爷爷长叹一声,神色惨然,“孩子,回不来了!’村人闻言,心如刀绞。”其实,这种凄惨的,风号雨泣的场景遍布当时的马踏乡村。
2013年12月,我去到北海市,电约陈焯到北部湾广场得兴酒楼喝茶。吕英的生母陈崇颐是陈焯的四姑母。陈崇颐娘家是书香门第,高州根子的望族,兄弟姐妹都是知书识礼的人,胞兄陈崇斌系民国时期中山大学毕业生,曾担任吴川县中学校长。陈焯对我说:"吕英是我的表姐。我只见过她一面,她12岁那年到我家来想要点吃的东西,可我家也实在拿不出来,她失望地走了,她才12岁啊,我母亲为此一直很愧疚,觉得很对不起她!我现在一想起这事,都无法平静,难过!”
我知道,陈焯家在62年前也被划为地主成份,陈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看到了他说起小吕英上舅妈家讨吃那一幕情景时眼里噙着泪水......
“深知身在情长在,前尘不共彩云飞”,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 ----吕英带着对杨氏丈夫的深情怀念离开人间16 年了。
在听别人讲述这类真实的故事时,我一边用心去记,一边流下对他(她)们同情的眼泪;我在整理这篇故事的素材时,我又一次难过得哭了,我不但为她哭,也为许多像她家有类似悲惨遭遇的人们而哭。
---记 苦 命 人 吕 英
陈贞/文
广东茂名县浮山岭的山下乡村出过历史名人:羽衣蹁跹的道士、名医潘茂名,在民国政军舞台呼风唤雨的 巾帼英雄莫秀英、吉林省省长梁华盛、国军军长莫福如。这些名人各自留下了被后世传颂的故事,更多的是小人物像秋风刮下的一片片枯叶消失在泥土里,无声无息,有的小人物却因经历催人泪落而引起后世的关注,同情。
浮山岭的北麓是茂名县分界茅坡村,1957年,吕英,一个的17岁姑娘由根子嫁到了这里,她和年纪相差两岁的丈夫都生于地主家庭。对多数人来说,生命本来应是一条长长的弯曲山路,路边蝶落初尘花盛妍 ,果实累累,该好好观赏才是,但吕英仿佛注定这一生凄风苦雨。不到一年,吕英的丈夫病逝。婆家四壁空空,生活难以为继,时年18岁的她饥肠辘辘,出门觅食,顺着远方的坡园翻红薯泥,喝沟水,饿一餐、饱一餐,夜宿草舍,终于在距离故乡60公里远的东南面电白马踏公社的一条村庄找到了归宿地,她自嫁的富农成分的杨家长子,这对年轻人同病相怜。插秧、割稻、打禾、养猪、养家禽、挑大粪、挖河泥……她干过任何粗重的农活。夫妇俩芭蕉开花――一条心,犹如春天的蜜蜂闲不住,每天为生计而劳作。 虽然生活清贫,但他(她)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重新获得爱的18岁女人,有了男人的滋润,有了一间可以遮雨挡光栖身的茅屋,随着两个男孩子的相继出生,家庭有欢声笑语,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心情舒畅的吕英 逐渐丰腴起来了,犹若六月荷花------众人共赏。
1968年7月底,革总司首领吴XX等人从水东码头乘坐汽艇窜到电白县电城镇开黑会,出席人员是县内各地司派小头目,吴在会上胡言,核狗(对核派组织的蔑称)与乡村的地主富农相勾结,妄图复辟变天,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一个核狗或地富分子等于开荒三亩地......吴要求各公社(公社今改为镇)捕杀这类人员。电白马踏公社司派头目许栖、杨蹈j 秉承吴XX的黑旨意,迅速在境内掀起一股杀害无辜者的恶浪,指使下面大队领导率领民兵分赴各个自然村消灭阶级敌人---黑五类 。
仅相距两三天,吕英的丈夫、家公、家婆、2个小叔子、2个儿子与马踏公社各条村庄的数百黑五类先后被杀。吕英的丈夫被多位凶手用稻插叉捅伤,诸处伤口血流如注, 疼得打滚,哀求用枪打.....。吕英是年28岁,她在这桩几乎是满门抄斩的血案中活了下来。几天后,一个大队干部登门,这位不速之客对吕英说:“你获得党的宽大处理,完全是我的功劳。你再留在这里既穷又衰,如果再来一次清理阶级队伍,你就插翅难飞 。”在毛泽东时代,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迁徙,外出要凭路条,吕英等同毛驴拉磨,走不出这个圈,随时有血光之灾 ,但胆小,泪痕斑斑的吕英沉默以对。 大队干部见状,便安慰开导她:“我妻子的哥哥张某是马踏公社邻村的人,从来没结过婚,虽然今年只有48岁,但身体很好,而且家庭成分是贫农,我是他的亲戚,我是贫农成份的GCD干部,谁人都不敢欺负我的内兄。如果你肯嫁给他,那么你的生活有依靠,而且生的子女可随父亲的贫农成份。”贴上贫农标签的人能平平安安,而出身所谓剥削阶级的人自然是命如蝼蚁,不久前,至亲和其他地主、富农尸横野外的情景,让刚回过神来的吕英依旧感觉很恐怖,这名干部其实也是这个杀人组织的骨干,树上的乌鸦,圈里的肥猪---一色货 ,但他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话还是让吕英心有触动 !吕英又看见大杀阶级敌人的现象暂停了,可偶尔有五类分子的子孙被捉去斗争时而被打死的消息传来,为了求生,明知是茅坑里放玫瑰花,明知此人大自己20岁,双方出身社会背景不同,教养有别,不可能建立感情,今后还要与此人繁殖后代,恶心到想吐啊,可她经受不起对方的连哄带吓,终于违心地嫁给了张某。
婚前,吕英并不了解张某的人品。
1952年,电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张某32岁,力大,粗野庸俗,心肠歹毒, 群众见过他对地主、富农张牙舞爪的样子,他吊打这些农民的“吸血鬼”很卖力,他倚仗土改工作组的权势,强迫过几个风韵犹存的地主婆与之上床,以换取对他们夫妇手下留情;同村的王家少女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在淫棍张某的眼里:春茶尖儿---又鲜又嫩。机会来了,因王家评了地主成份,张某以此胁迫她上床.....老虎来了盖被单―― 挡不住, 这位满嘴臭气的老男活像一头发情的畜牲一样扑过去,片刻这名少女成了剥皮的青藤――一丝不挂,在她身上拱起来,摸起来,又似老鸭下水嘴上前啄食,口水滴到这个少女的脸蛋、嘴唇......。次年,王姓父母饿死,便嫁给一个休妻的小学罗老师。罗比王女大10岁。行房之夜,罗老师发现妻子不是处女,追问之下,妻子道出实情。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个正义感的乡官,乃撤了张某村官的职。张某臭名昭著,加上好逸恶劳,所以48岁仍无妻室。罗老师对妻子冷若冰霜,且打骂不断,王女多次跪求丈夫不要计较前嫌,但罗始终不为所动......1955年春,18岁的小王净身出门,只携带几斤生番薯,步行200多公里到雷州半岛海康县天竺庵出家,主持接纳了这位可怜的少妇。从此,这名少妇在他乡削发为尼,与青灯做伴,朝夕念经,她希望慢慢老去,终于有一天能像一朵花儿零落成泥碾做尘,做异域的孤魂。
等到看穿张某的真面目后,生米已煮熟饭。那个时代,吕英无智慧、无勇气、无力量挣脱人家为她戴上的命运枷锁。
1969年---1971年,吕英为衣冠禽兽的张姓丈夫连生两子,但二子的性情酷似乃父,游手好闲,全是破风筝---抖不起来。他们确是可以跟随父亲的成份。吕英看见后夫比不上前夫,后夫的二子更是样样比不上前夫的二子,乃经常伤心,“情如花逝空遗恨,泪过素颜留红痕 ”,吕英眼眸中闪出的那一抹悲伤,是对前夫残留在她心底的爱。
1998年7月某日,既是前夫60周岁的阴诞日,又是前夫含冤去世30周年的忌日,58岁的吕英备了少许祭品去附近的庙里为亡夫敬香,不意此事为后夫发觉。吕英回到家里,后夫横眉瞪目,恨其旧情不散,多少年来抱着妻子这尊菩萨亲嘴――都是一头热乎,乃不顾已78岁高龄的病弱身躯,举粗棒对妻子一顿狠打,吕英头部被打得血流如注、伤及内脏,卷缩地上呻吟不已,当夜即死,而他因对妻子偷祭杨姓前夫一事气恨交加,对妻子往死里打时用力太猛,所以不久也被阎罗王召去。
吕英当年在那位“好心人”的力保下,幸免于死 ,多活了30年,但最终还是惨死在这个恶夫的暴力下。吕英三嫁,真像“ 中药店里的揩布,揩来揩去都是苦” ,佛教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按马列主义无神论,她永远没机会回“岸”了,因为生命没有轮回。而王姓地主妹出家11年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号召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海康县红卫兵砸毁她所在的尼姑庵,其本人被轮暴,乃抱一只观音菩萨悲愤地投水自杀。
有一个人提起了当年的惨事,说他所在的(马踏公社)那条村庄“ 也是重灾区。当晚8、9时左右,(大队)民兵(奉命)押地主老少出村到刑场。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小孩子跟随大人走到村头,突然对大人说:‘爷爷,我把木屐放在路边,等回来时再穿。”其爷爷长叹一声,神色惨然,“孩子,回不来了!’村人闻言,心如刀绞。”其实,这种凄惨的,风号雨泣的场景遍布当时的马踏乡村。
2013年12月,我去到北海市,电约陈焯到北部湾广场得兴酒楼喝茶。吕英的生母陈崇颐是陈焯的四姑母。陈崇颐娘家是书香门第,高州根子的望族,兄弟姐妹都是知书识礼的人,胞兄陈崇斌系民国时期中山大学毕业生,曾担任吴川县中学校长。陈焯对我说:"吕英是我的表姐。我只见过她一面,她12岁那年到我家来想要点吃的东西,可我家也实在拿不出来,她失望地走了,她才12岁啊,我母亲为此一直很愧疚,觉得很对不起她!我现在一想起这事,都无法平静,难过!”
我知道,陈焯家在62年前也被划为地主成份,陈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看到了他说起小吕英上舅妈家讨吃那一幕情景时眼里噙着泪水......
“深知身在情长在,前尘不共彩云飞”,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 ----吕英带着对杨氏丈夫的深情怀念离开人间16 年了。
在听别人讲述这类真实的故事时,我一边用心去记,一边流下对他(她)们同情的眼泪;我在整理这篇故事的素材时,我又一次难过得哭了,我不但为她哭,也为许多像她家有类似悲惨遭遇的人们而哭。
- 注册
- 2005-04-23
- 帖子
- 6,195
- 反馈评分
- 407
- 点数
- 191
- 性别
- 男
QUOTE(想伸张正义 @ 2014年12月16日 Tuesday, 07:22 PM)
现在的人心一样凶残,如果再有类似的运动,死的人更会多。
----------------------------------------------------------------------------------------------
我想,社会不会再回到上世纪70年代前的状态了。我觉得,中国一直在进步----允许人们发牢骚,以前,你为地主、富农说一句公道话都是犯禁的!
现在的人心一样凶残,如果再有类似的运动,死的人更会多。
[snapback]3722760[/snapback]
----------------------------------------------------------------------------------------------
我想,社会不会再回到上世纪70年代前的状态了。我觉得,中国一直在进步----允许人们发牢骚,以前,你为地主、富农说一句公道话都是犯禁的!
- 注册
- 2005-04-23
- 帖子
- 6,195
- 反馈评分
- 407
- 点数
- 191
- 性别
- 男
QUOTE(东澳夕照 @ 2014年12月17日 Wednesday, 12:28 AM)
中国人对自己同胞下手比日本人更狠,我们常对外族人屠杀同胞义愤填膺,同胞间的屠杀,哪怕死的人多几倍,从不反省,反而会隐瞒历史。何等之悲哀啊!
----------------------------------------------------------------------------------------
她生存的环境险恶-----遇到了乱世为非作歹的人。
中国人对自己同胞下手比日本人更狠,我们常对外族人屠杀同胞义愤填膺,同胞间的屠杀,哪怕死的人多几倍,从不反省,反而会隐瞒历史。何等之悲哀啊!
[snapback]3722846[/snapback]
----------------------------------------------------------------------------------------
她生存的环境险恶-----遇到了乱世为非作歹的人。
QUOTE(杀虎使者 @ 2014年12月16日 Tuesday, 11:15 PM)
能用这个词去表达吗?没文化。
QUOTE(tianya @ 2014年12月17日 Wednesday, 06:33 PM)
不是去赶考,表达有点不准确无所谓啦。其实,蛙子读过高中,读书是不少的。
QUOTE(东澳夕照 @ 2014年12月17日 Wednesday, 10:34 PM)
说的没错,蛙子起码读过一个学期的高中,在乡下,不能说没文化了。
准确的说是中专读了一个学期。20岁前读书比绝大多人都多。名著基本没看过,黄书和小说占的比例最大。6个字的回帖我看不出哪个词表达的不正确。
能用这个词去表达吗?没文化。
[snapback]3722842[/snapback]
QUOTE(tianya @ 2014年12月17日 Wednesday, 06:33 PM)
不是去赶考,表达有点不准确无所谓啦。其实,蛙子读过高中,读书是不少的。
[snapback]3723003[/snapback]
QUOTE(东澳夕照 @ 2014年12月17日 Wednesday, 10:34 PM)
说的没错,蛙子起码读过一个学期的高中,在乡下,不能说没文化了。
[snapback]3723096[/snapback]
准确的说是中专读了一个学期。20岁前读书比绝大多人都多。名著基本没看过,黄书和小说占的比例最大。6个字的回帖我看不出哪个词表达的不正确。
- 注册
- 2005-04-23
- 帖子
- 6,195
- 反馈评分
- 407
- 点数
- 191
- 性别
- 男
QUOTE(农夫 @ 2014年12月18日 Thursday, 10:17 AM)
马踏真发生过这样的事?
-----------------------------------------------------------------------------------------------
这个故事是吕英的表姐陈X和(离休干部)及其胞弟陈焯讲述
的。1968年8月初,马踏公社滥杀无辜,此事上世纪80年代由杨华主编的官
方电白县志有概述,透露共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孙243人,民间盛传共杀
520多-----1984年,我到马踏出差,是当地人亲口对我讲的。一位龙湾插队
知青邓XX亲眼看到1968年8月5日夜晚八点左右,一共有32名石窟大队的地
主、富农及其子女在马踏供销社门前被验明正身押往圩头岭枪杀!杀手:厚
皮成、大肚贵。听说,这两名凶手已去世多年。
邓XX那晚也被五花大绑,绑在现场,罪名“投毒”下井杀害贫下中农。
杀害无辜的现象被坚决制止后 电白还属于湛江地区管辖时,ZG电白县
委曾成立调查工作组前往马踏公社清查这类血案。
传说,后来石窟大队书记因这桩怵目惊心的血案被判刑
马踏真发生过这样的事?
[snapback]3723130[/snapback]
-----------------------------------------------------------------------------------------------
这个故事是吕英的表姐陈X和(离休干部)及其胞弟陈焯讲述
的。1968年8月初,马踏公社滥杀无辜,此事上世纪80年代由杨华主编的官
方电白县志有概述,透露共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孙243人,民间盛传共杀
520多-----1984年,我到马踏出差,是当地人亲口对我讲的。一位龙湾插队
知青邓XX亲眼看到1968年8月5日夜晚八点左右,一共有32名石窟大队的地
主、富农及其子女在马踏供销社门前被验明正身押往圩头岭枪杀!杀手:厚
皮成、大肚贵。听说,这两名凶手已去世多年。
邓XX那晚也被五花大绑,绑在现场,罪名“投毒”下井杀害贫下中农。
杀害无辜的现象被坚决制止后 电白还属于湛江地区管辖时,ZG电白县
委曾成立调查工作组前往马踏公社清查这类血案。
传说,后来石窟大队书记因这桩怵目惊心的血案被判刑
QUOTE(tianya @ 2014年12月18日 Thursday, 11:17 AM)
-----------------------------------------------------------------------------------------------
这个故事是吕英的表姐陈X和(离休干部)及其胞弟陈焯讲述
的。1968年8月初,马踏公社滥杀无辜,此事上世纪80年代由杨华主编的官
方电白县志有概述,透露共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孙243人,民间盛传共杀
520多-----1984年,我到马踏出差,是当地人亲口对我讲的。一位龙湾插队
知青邓XX亲眼看到1968年8月5日八点左右,一共有32名石窟大队的地主、
富农及其子女在马踏供销社门前被验明正身押往圩头岭枪杀!杀手:厚皮
成、大肚贵。听说,这两名凶手已去世多年。
传说,后来石窟大队书记因这桩怵目惊心的血案被判刑
令人发指!丧尽天良。
-----------------------------------------------------------------------------------------------
这个故事是吕英的表姐陈X和(离休干部)及其胞弟陈焯讲述
的。1968年8月初,马踏公社滥杀无辜,此事上世纪80年代由杨华主编的官
方电白县志有概述,透露共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孙243人,民间盛传共杀
520多-----1984年,我到马踏出差,是当地人亲口对我讲的。一位龙湾插队
知青邓XX亲眼看到1968年8月5日八点左右,一共有32名石窟大队的地主、
富农及其子女在马踏供销社门前被验明正身押往圩头岭枪杀!杀手:厚皮
成、大肚贵。听说,这两名凶手已去世多年。
传说,后来石窟大队书记因这桩怵目惊心的血案被判刑
[snapback]3723163[/snapback]
令人发指!丧尽天良。
QUOTE(tianya @ 2014年12月18日 Thursday, 11:17 AM)
-----------------------------------------------------------------------------------------------
这个故事是吕英的表姐陈X和(离休干部)及其胞弟陈焯讲述
的。1968年8月初,马踏公社滥杀无辜,此事上世纪80年代由杨华主编的官
方电白县志有概述,透露共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孙243人,民间盛传共杀
520多-----1984年,我到马踏出差,是当地人亲口对我讲的。一位龙湾插队
知青邓XX亲眼看到1968年8月5日夜晚八点左右,一共有32名石窟大队的地
主、富农及其子女在马踏供销社门前被验明正身押往圩头岭枪杀!杀手:厚
皮成、大肚贵。听说,这两名凶手已去世多年。
邓XX那晚也被五花大绑,绑在现场,罪名“投毒”下井杀害贫下中农。
传说,后来石窟大队书记因这桩怵目惊心的血案被判刑
是文革武斗还是之前的阶级斗争?
-----------------------------------------------------------------------------------------------
这个故事是吕英的表姐陈X和(离休干部)及其胞弟陈焯讲述
的。1968年8月初,马踏公社滥杀无辜,此事上世纪80年代由杨华主编的官
方电白县志有概述,透露共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孙243人,民间盛传共杀
520多-----1984年,我到马踏出差,是当地人亲口对我讲的。一位龙湾插队
知青邓XX亲眼看到1968年8月5日夜晚八点左右,一共有32名石窟大队的地
主、富农及其子女在马踏供销社门前被验明正身押往圩头岭枪杀!杀手:厚
皮成、大肚贵。听说,这两名凶手已去世多年。
邓XX那晚也被五花大绑,绑在现场,罪名“投毒”下井杀害贫下中农。
传说,后来石窟大队书记因这桩怵目惊心的血案被判刑
[snapback]3723163[/snapback]
是文革武斗还是之前的阶级斗争?
- 注册
- 2005-04-23
- 帖子
- 6,195
- 反馈评分
- 407
- 点数
- 191
- 性别
- 男
QUOTE(校董大人 @ 2014年12月18日 Thursday, 12:37 PM)
是文革武斗还是之前的阶级斗争?
-------------------------------------------------------------------------------------------------
文革期间啊,校董大人。真正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6年---1968年,共三年时间,是三年浩劫,有人说10年浩劫乃系无稽之谈。1969年,军人接管电白地方政权,严令派性组织上缴武器!紧接着,军管会抓人,大批武斗分子被关押.....临时监狱就在电白县粮食局谷仓。
自1969年以后,电白进入治安稳定时期,生产全面走上正轨,政府对被杀的无辜地主富农每人各赔偿120元。
[attachmentid=335825]
图为电白粮食局围墙,围墙内原来2座大型谷仓,1969年,司派、核派武斗干将都被关在里面接受审查。
是文革武斗还是之前的阶级斗争?
[snapback]3723165[/snapback]
-------------------------------------------------------------------------------------------------
文革期间啊,校董大人。真正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6年---1968年,共三年时间,是三年浩劫,有人说10年浩劫乃系无稽之谈。1969年,军人接管电白地方政权,严令派性组织上缴武器!紧接着,军管会抓人,大批武斗分子被关押.....临时监狱就在电白县粮食局谷仓。
自1969年以后,电白进入治安稳定时期,生产全面走上正轨,政府对被杀的无辜地主富农每人各赔偿120元。
[attachmentid=335825]
图为电白粮食局围墙,围墙内原来2座大型谷仓,1969年,司派、核派武斗干将都被关在里面接受审查。
QUOTE(tianya @ 2014年12月18日 Thursday, 12:09 PM)
-------------------------------------------------------------------------------------------------
文革期间啊,校董大人。真正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6年---1968年,共三年时间,是三年浩劫,有人说10年浩劫乃系无稽之谈。1969年,军人接管电白地方政权,严令派性组织上缴武器!紧接着,军管会抓人,大批武斗分子被关押.....临时监狱就在电白县粮食局谷仓。
自1969年以后,电白进入治安稳定时期,生产全面走上正轨,政府对被杀的无辜地主富农每人各赔偿120元。
[attachmentid=335825]
图为电白粮食局围墙,围墙内原来2座大型谷仓,1969年,司派、核派武斗干将都被关在里面接受审查。
文革的派性斗争,为什么要杀地主呢?马踏那些凶手是司派?
-------------------------------------------------------------------------------------------------
文革期间啊,校董大人。真正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6年---1968年,共三年时间,是三年浩劫,有人说10年浩劫乃系无稽之谈。1969年,军人接管电白地方政权,严令派性组织上缴武器!紧接着,军管会抓人,大批武斗分子被关押.....临时监狱就在电白县粮食局谷仓。
自1969年以后,电白进入治安稳定时期,生产全面走上正轨,政府对被杀的无辜地主富农每人各赔偿120元。
[attachmentid=335825]
图为电白粮食局围墙,围墙内原来2座大型谷仓,1969年,司派、核派武斗干将都被关在里面接受审查。
[snapback]3723175[/snapback]
文革的派性斗争,为什么要杀地主呢?马踏那些凶手是司派?
- 注册
- 2005-04-23
- 帖子
- 6,195
- 反馈评分
- 407
- 点数
- 191
- 性别
- 男
QUOTE(七九工 @ 2014年12月18日 Thursday, 01:16 PM)
文革的派性斗争,为什么要杀地主呢?马踏那些凶手是司派?
------------------------------------------------------------------------------------------------
马踏公社是司派掌权!插队马踏农村的知青基本是核派观点,但实际上大部分知青后期并不参加武斗,初期,这些知青打出的旗号叫“支农红联”,汇集旗下的人马近200。
在电白对地主富农举起屠刀的全是司派阵营的人员,这类人来全自农村,农村人在阶级斗争意识的长期灌输下,对地主富农非常仇恨。
文革的派性斗争,为什么要杀地主呢?马踏那些凶手是司派?
[snapback]3723176[/snapback]
------------------------------------------------------------------------------------------------
马踏公社是司派掌权!插队马踏农村的知青基本是核派观点,但实际上大部分知青后期并不参加武斗,初期,这些知青打出的旗号叫“支农红联”,汇集旗下的人马近200。
在电白对地主富农举起屠刀的全是司派阵营的人员,这类人来全自农村,农村人在阶级斗争意识的长期灌输下,对地主富农非常仇恨。
相似主题
正在浏览此帖子的用户
当前在线: 2 (会员: 0, 游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