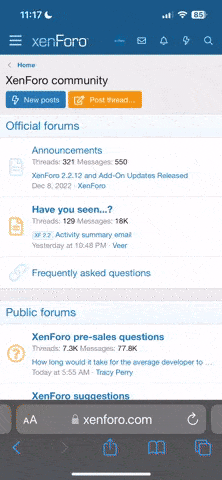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吊“灯” (2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梅韵
- 开始时间
QUOTE(飘落的黄叶 @ 2014年05月14日 Wednesday, 07:47 AM)
我也七零后,印象中确实是初中课文。鲁迅的文章,特别是小说类文章,是比较艰涩的,如故事情节较生动的《伤逝》,要读出故事背后的话语,也是较难的吧我想,而且一万个人可能不止一万种解读。读鲁迅杂文,是我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后的事情,边读边对照身边的人和事,感觉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如梅韵写的吊灯,许多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当然为了尊严而离异,或为了随俗而放弃尊严(工作)的情况,就我所知,在传统观念相当强的客家人地区也是较少的了,这只能说明电白的传统意识根深蒂固。
祥林嫂式的悲剧,是几千年中国女性悲剧的一个宿影了吧。中国的监狱多,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从来就没有个人的位置,所以从文化上就促成了监狱多的法理基础。也因为没有个人的位置,思想上更促成了监狱多的法理基础。祥林嫂和陈家女人,都是思想监狱的牺牲品。要突破这些监狱,不能靠单纯的革命,说教。只能靠人们的不断觉醒吧我想。
 分析得真好!佩服!
分析得真好!佩服!
我也七零后,印象中确实是初中课文。鲁迅的文章,特别是小说类文章,是比较艰涩的,如故事情节较生动的《伤逝》,要读出故事背后的话语,也是较难的吧我想,而且一万个人可能不止一万种解读。读鲁迅杂文,是我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后的事情,边读边对照身边的人和事,感觉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如梅韵写的吊灯,许多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当然为了尊严而离异,或为了随俗而放弃尊严(工作)的情况,就我所知,在传统观念相当强的客家人地区也是较少的了,这只能说明电白的传统意识根深蒂固。
祥林嫂式的悲剧,是几千年中国女性悲剧的一个宿影了吧。中国的监狱多,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从来就没有个人的位置,所以从文化上就促成了监狱多的法理基础。也因为没有个人的位置,思想上更促成了监狱多的法理基础。祥林嫂和陈家女人,都是思想监狱的牺牲品。要突破这些监狱,不能靠单纯的革命,说教。只能靠人们的不断觉醒吧我想。
[snapback]3640971[/snapback]
QUOTE(汪洋大海 @ 2014年05月15日 Thursday, 08:01 AM)
此文确实好,文彩飞扬,我认真阅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同事来自晏镜,他说也有如此习俗,他村摆灯酒的那天他花的利是钱达2千元,有10人请他喝灯酒。不过,这种习俗应被抛弃,妇女成为了牺牲品,重男轻女的思想与计生政策相违背。尊敬的楼主,你是位女教师吧,钦佩!
前些日子里有不少的人与我说,在目前的中国“教育与教师”都是个敏感的话题,易招来骂声。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许多人还是明理的。
嗯,我确是一位女教师。
此文确实好,文彩飞扬,我认真阅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同事来自晏镜,他说也有如此习俗,他村摆灯酒的那天他花的利是钱达2千元,有10人请他喝灯酒。不过,这种习俗应被抛弃,妇女成为了牺牲品,重男轻女的思想与计生政策相违背。尊敬的楼主,你是位女教师吧,钦佩!
[snapback]3641322[/snapback]
前些日子里有不少的人与我说,在目前的中国“教育与教师”都是个敏感的话题,易招来骂声。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许多人还是明理的。
嗯,我确是一位女教师。
QUOTE(梅韵 @ 2014年05月21日 Wednesday, 12:01 PM)
 分析得真好!佩服!
分析得真好!佩服!
是你写得好,我顶多插科打诨娱乐下大众,文章是做不出的哈。
我读鲁迅等人的文章,结合自己的观察,觉得中国社会本来就是监狱多如牛毛的社会,有形的监狱多,无形的心狱更多,有形的监狱易破,无形的心狱难解。从古代以明文方式记入典籍的五刑,到没有文明记载却在实际中对疑犯施行迫供的花式繁多的刑具,到朱明皇朝的剥皮揎草登峰造极。在这种严刑峻法的拷问下能免于屈打成招的人,必定是内心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坚贞之士,这种人一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人来。这样高压的现实社会,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保持行为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的,这个是制度上的硬性约束。
宋以后的程朱理学,则从思想上对个体进一步奴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大旗被掌握权力的手高高举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奴役的程度。有个典故是很值得回味的,就是理学大师朱熹、严蕊、唐仲友的历史公案。这段公案表明,敢于坚持理学者,大概都有酷吏的性格倾向,内心缺少仁爱包容而显得贫瘠,对外却一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样子。理学的严苛和峻法的冷酷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中国几千年多如牛毛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始作俑者就这两样东西。要打破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除此别无他法可想,一点个人看法哈。
义妓严蕊在得脱牢笼后的自提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虽有人怀疑是唐仲友党伪作,却无疑反映出某种历史心声,向往和追求自由之心是古今中外人性之需,禁锢人心从开始就不受待见的。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宋•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终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记忆有误,应该是卜算子哈,编辑更正之,抱歉了。
[snapback]3643929[/snapback]
是你写得好,我顶多插科打诨娱乐下大众,文章是做不出的哈。
我读鲁迅等人的文章,结合自己的观察,觉得中国社会本来就是监狱多如牛毛的社会,有形的监狱多,无形的心狱更多,有形的监狱易破,无形的心狱难解。从古代以明文方式记入典籍的五刑,到没有文明记载却在实际中对疑犯施行迫供的花式繁多的刑具,到朱明皇朝的剥皮揎草登峰造极。在这种严刑峻法的拷问下能免于屈打成招的人,必定是内心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坚贞之士,这种人一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人来。这样高压的现实社会,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保持行为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的,这个是制度上的硬性约束。
宋以后的程朱理学,则从思想上对个体进一步奴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大旗被掌握权力的手高高举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奴役的程度。有个典故是很值得回味的,就是理学大师朱熹、严蕊、唐仲友的历史公案。这段公案表明,敢于坚持理学者,大概都有酷吏的性格倾向,内心缺少仁爱包容而显得贫瘠,对外却一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样子。理学的严苛和峻法的冷酷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中国几千年多如牛毛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始作俑者就这两样东西。要打破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除此别无他法可想,一点个人看法哈。
义妓严蕊在得脱牢笼后的自提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虽有人怀疑是唐仲友党伪作,却无疑反映出某种历史心声,向往和追求自由之心是古今中外人性之需,禁锢人心从开始就不受待见的。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宋•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终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记忆有误,应该是卜算子哈,编辑更正之,抱歉了。
QUOTE(飘落的黄叶 @ 2014年05月21日 Wednesday, 06:40 PM)
是你写得好,我顶多插科打诨娱乐下大众,文章是做不出的哈。
我读鲁迅等人的文章,结合自己的观察,觉得中国社会本来就是监狱多如牛毛的社会,有形的监狱多,无形的心狱更多,有形的监狱易破,无形的心狱难解。从古代以明文方式记入典籍的五刑,到没有文明记载却在实际中对疑犯施行迫供的花式繁多的刑具,到朱明皇朝的剥皮揎草登峰造极。在这种严刑峻法的拷问下能免于屈打成招的人,必定是内心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坚贞之士,这种人一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人来。这样高压的现实社会,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保持行为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的,这个是制度上的硬性约束。
宋以后的程朱理学,则从思想上对个体进一步奴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大旗被掌握权力的手高高举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奴役的程度。有个典故是很值得回味的,就是理学大师朱熹、严蕊、唐仲友的历史公案。这段公案表明,敢于坚持理学者,大概都有酷吏的性格倾向,内心缺少仁爱包容而显得贫瘠,对外却一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样子。理学的严苛和峻法的冷酷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中国几千年多如牛毛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始作俑者就这两样东西。要打破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除此别无他法可想,一点个人看法哈。
义妓严蕊在得脱牢笼后的自提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虽有人怀疑是唐仲友党伪作,却无疑反映出某种历史心声,向往和追求自由之心是古今中外人性之需,禁锢人心从开始就不受待见的。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宋•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终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记忆有误,应该是卜算子哈,编辑更正之,抱歉了。
 学习了!
学习了!
是你写得好,我顶多插科打诨娱乐下大众,文章是做不出的哈。
我读鲁迅等人的文章,结合自己的观察,觉得中国社会本来就是监狱多如牛毛的社会,有形的监狱多,无形的心狱更多,有形的监狱易破,无形的心狱难解。从古代以明文方式记入典籍的五刑,到没有文明记载却在实际中对疑犯施行迫供的花式繁多的刑具,到朱明皇朝的剥皮揎草登峰造极。在这种严刑峻法的拷问下能免于屈打成招的人,必定是内心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坚贞之士,这种人一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人来。这样高压的现实社会,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保持行为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的,这个是制度上的硬性约束。
宋以后的程朱理学,则从思想上对个体进一步奴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大旗被掌握权力的手高高举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奴役的程度。有个典故是很值得回味的,就是理学大师朱熹、严蕊、唐仲友的历史公案。这段公案表明,敢于坚持理学者,大概都有酷吏的性格倾向,内心缺少仁爱包容而显得贫瘠,对外却一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样子。理学的严苛和峻法的冷酷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中国几千年多如牛毛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始作俑者就这两样东西。要打破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心狱,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除此别无他法可想,一点个人看法哈。
义妓严蕊在得脱牢笼后的自提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虽有人怀疑是唐仲友党伪作,却无疑反映出某种历史心声,向往和追求自由之心是古今中外人性之需,禁锢人心从开始就不受待见的。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宋•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终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记忆有误,应该是卜算子哈,编辑更正之,抱歉了。
[snapback]3644051[/snapback]
风在夜里哭泣(一)吊灯
风在夜里哭泣(二) 流失的美丽
时间是个最好的疗伤师,这类似的道理曾被无数的人明证过,而现在也被我证实着。
日子悄悄的流逝着,转眼间离年初那个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吊灯摆灯酒的热闹日子已有两个多月,由当时的那一点感触所引发的伤感早已经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人本来就是种健忘的动物,更何况不是发生在自家身上的痛苦事儿呢。我是个自私的家伙,所以我比任何人忘记得更快,我又恢复了我那无心无肺的快乐而忙碌日子。
我每天工作,上班下班,在家庭与工作中来往奔跑着。
一天,夜里十点多钟,下晚自修回来的我一进房门,就一边解除身上工作的武装,一边摁开了电脑的电源开关,然后在等待电脑启动的同时,找衣服,收拾衣物――忙了一天,挺累的,我准备一边听音乐一边洗澡,让自己好好放松放松。电脑打开了,习惯性挂上Q。
当我洗漱完毕坐在了电脑前,发现Q像在不停的闪烁, 点开后发现来信的原来是旧同事婷婷,她发给我一个大哭的的小头像。
“怎么了?我的小乖乖。“我一边递上纸巾一边戏谑着问她。这个婷呀,很是个性情中人,常常一会哭一会笑,常常是旁边的人还在为她的哭而担忧时,她那边又乐得哈哈大笑了。因此饱受她折磨的我便也慢慢的练得刀枪不入了。
”淑她……她出事了。”电脑那边传过来断断续续的一句话,让我的心一阵抽紧。
我没吭声,只是发了一个“?”过去。
“淑昨天又去流了,但在手术台上没有下来。听说是‘血崩山’――那血呀,怎么也止不住,流了一地……“不会吧,我在心里问着,但想起淑这么久来的情况,又觉得实在不像是婷的咋呼――再说,她也不可能拿这事来咋呼呀――看着屏幕上的字,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模糊。
婷与淑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们三人同舍而居每人一间独立的小房间,我们是同一年毕业又是一起进入那间镇中学成为同事的。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也都气盛,经常一起讨论工作,讨论生活,也一起到学校周围的田野里散步,采集野菜野花编织着属于我们青春女孩们的梦想。在三个人中淑长得最美,身材高挑,五官端正,性格娴淑;她虽语言不多,却每每一语中的。而我与婷却都是咋咋呼呼一个争强一个斗胜的家伙,因此当仨人在一起时,总是我与婷俩人的嘴巴子斗得你死我活,烽火四起了,婷呢则在一边微笑着看热闹。而最让我与婷羡慕忌妒恨的是不管我们闹得如何不可开交,她呢总能一语中的,轻轻的把我们的死结打开。那一份气定神闲真是羡煞旁人,因此我们曾经戏谑她说:”如果我们是男人非取你为妻不可。”
就因为这些,当我与婷还在各自母亲的唠唠叨叨中躲避着过日子时,淑就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成为了小镇里某知名人家的媳妇,她的丈夫我们见过几次,是另一学校里的老师,人长得挺帅的,浪漫而多情,许多人都说他们俩是金童玉女般的绝配。
淑结婚后,就与翁婆们住到了一块,但她还是常常到我们宿舍里来与我们聊天,有时还给我们带一些小点心蔬菜瓜果等食物――据说是她婆婆做了让她带过来的。吃着她带来的这些食物,看着淑洋溢了一脸的幸福,我们打心眼里厦羡慕着。是的,红润的脸色,甜蜜的笑容无一不昭示着她的生活是幸福的。于是,茶余饭后的人们不管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小湖边的柳荫下,聊天时总喜欢拿她来说事。许多饭堂里的阿姨在给我们这些年轻女孩介绍对象时更是啧着嘴打着包票说”你放心好了,这户人家呀,就像淑家一样,嫁进去,绝对是享福的份。“
然而,淑结婚两年后,事情好像在发生着慢慢的变化,有时我们会发现她眉心间流露出点点的忧戚。记得1998那年,暑假来临的最后一天。学校开学期总结大会,会议结束时,人们在会议室前那棵荔枝树下说着告别的话。将近两个月的假期到来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与婷相约到BJ去旅游,淑沉闷地从会议室出来,我兴奋地迎上去揣了她一拳问:”BJ,你去不去?“
”什么?“也许我问得太突然了,淑有点茫然。
“假期去BJ玩玩,你去不去?”我重复了一遍。
“我……我家里有些事,不能去……祝你们玩得开心啦!”淑说完这句话后就转身离去了。婷看着淑的背影一脸沉思状的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劲呀……淑怎么了?”
经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异样。然而暑假的来临带给我们巨大的欢乐,刚刚的那一闪念很快就被我们完全忘记,在假期里我们不仅去BJ游了故宫,登长城做了一回“好汉”,还去了长江三峡……
八月尾新学年会议那天,学校教职员工们结束了多彩的假期生活,又从各地聚拢回来了。离开会还有几分钟,三三两两的人站在了校道两边的荔枝龙眼树下。快大开时淑才到来,她的脸色没有了先前的红润,也许是赶路过于匆忙吧,脸有点苍白。我担心的问她是不是病了,她随口应着说是有点感冒。后来会议结束后,我们把淑拉到宿舍里――这么久不见,心里有着许多的话要说。到了宿舍,婷缠着淑非要让她说说假期是怎么过的不可,是不是与老公去那里HAPPY了。在婷的一再纠缠下,淑沉吟了很久才说这个假期她根本就没出过门,一直都是在家里呆着。原来在放假时,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为了保险,都没计划出门远行。然而在假期临末了时才发现BB是女婴,结果做了人流“手术做完还不足一个星期。”淑平静地说。
是的,我们知道,淑的丈夫是独子,生个男孙是淑做为儿媳的必然使命。但是,计生法规定,禁止人为选择性的终止妊娠。难怪刚才淑在会议室门前一直推辞说是身体感冒,如果刚才说出来给别有用心的人听去了,那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可以让淑马上丢掉工作,就连给她检查胎儿性别,替她做手术的人都会受到连累。
“别担心,下次吧,下一次你一定能怀上男儿的。”我安慰她说。
“哎,听我妈说凤冈岭的送子观音很是灵验的,要不你去求求吧。”婷出主意说。
……
那之后,我不知道淑有没有去求过送子观音,但是在后来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淑进行了四次的人工流产,其中有一年做了三次流产手术,每一次手术都让淑好像大病一场那样。就这样,淑也由原来那个有名的大美人逐渐逐渐的变形――不仅脸上的红润完全消失,原来一直挂在上面的娴静的笑容也不见了,原先那丰满的体态也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高挑的身材一旦消瘦,便显出佝偻之态――美在淑的身上快速的流失着。
然而我与婷也都相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里――我们都结婚了,虽然我们曾经怀揣过梦想,但结婚了的女人不得不面对着横亘在我们女人面前的那一个沉重而无奈的话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上对于已经结婚的女子,虽然政府一再提倡男女平等,一再宣传”生男生女一个样“,但生个男孩是绝大多数男人心照不宣的愿望,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只能生一胎女公职人员来说便必须一箭中的,因此在人们的言语间便有了许多关于生男孩的秘诀,在性别相同的人群聚集的地方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永恒的话题。
然而不久,我就离开了那个小镇。与她们分别的前两天,我们有个小小的聚会,那是几个知心好友之间的聚会,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另两个已经结婚的女同事――都是年经人,只是她们遂心如意的生养到了儿子,那天,这两个生到男儿的同事告诉了我们一些生儿子的秘诀。
我不知道,淑与婷有没有按照秘诀那样去生育儿女,反正我没有――至于为什么没有,那是后话。
离开小镇后,我就没有再见过淑,只是常在QQ里与婷聊一些八卦事儿,有时也会说起淑,在这些零零碎碎的话语里,我知道淑一直都不怎么好――虽然老公,翁婆一如既往的待她好,但是她也一如既往的没生到男孩。还听说由于多次流产,淑闹上了盆腔炎等一些妇科疾病,常常往医院跑。当时听说她这么苦,在叹惜之余我总会在心里默默的祝福她,祝她早生贵子,脱离苦海。
然而我没想到最后听到的关于淑的竟是噩耗――死于宫外孕引发的大出血,我知道有些妇科疾病会引起宫外孕,也知道宫外孕的危险性。但我没想到淑竟然在身体没痊愈时会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受孕,我没想到这么美好的一段婚姻竟然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变成了淑的坟墓。我突然想,这一家子里的人真的懂得爱吗?她们,他们真的爱淑吗?
为何呀?为何我又听到了那呜呜咽咽的夜风的哭泣呢? 它们是在痛哭那流失了的美丽吗?
(注:这个为速写,为应蛤蟆挑战,未经怎么修改。抱歉。)
风在夜里哭泣(二) 流失的美丽
时间是个最好的疗伤师,这类似的道理曾被无数的人明证过,而现在也被我证实着。
日子悄悄的流逝着,转眼间离年初那个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吊灯摆灯酒的热闹日子已有两个多月,由当时的那一点感触所引发的伤感早已经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人本来就是种健忘的动物,更何况不是发生在自家身上的痛苦事儿呢。我是个自私的家伙,所以我比任何人忘记得更快,我又恢复了我那无心无肺的快乐而忙碌日子。
我每天工作,上班下班,在家庭与工作中来往奔跑着。
一天,夜里十点多钟,下晚自修回来的我一进房门,就一边解除身上工作的武装,一边摁开了电脑的电源开关,然后在等待电脑启动的同时,找衣服,收拾衣物――忙了一天,挺累的,我准备一边听音乐一边洗澡,让自己好好放松放松。电脑打开了,习惯性挂上Q。
当我洗漱完毕坐在了电脑前,发现Q像在不停的闪烁, 点开后发现来信的原来是旧同事婷婷,她发给我一个大哭的的小头像。
“怎么了?我的小乖乖。“我一边递上纸巾一边戏谑着问她。这个婷呀,很是个性情中人,常常一会哭一会笑,常常是旁边的人还在为她的哭而担忧时,她那边又乐得哈哈大笑了。因此饱受她折磨的我便也慢慢的练得刀枪不入了。
”淑她……她出事了。”电脑那边传过来断断续续的一句话,让我的心一阵抽紧。
我没吭声,只是发了一个“?”过去。
“淑昨天又去流了,但在手术台上没有下来。听说是‘血崩山’――那血呀,怎么也止不住,流了一地……“不会吧,我在心里问着,但想起淑这么久来的情况,又觉得实在不像是婷的咋呼――再说,她也不可能拿这事来咋呼呀――看着屏幕上的字,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模糊。
婷与淑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们三人同舍而居每人一间独立的小房间,我们是同一年毕业又是一起进入那间镇中学成为同事的。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也都气盛,经常一起讨论工作,讨论生活,也一起到学校周围的田野里散步,采集野菜野花编织着属于我们青春女孩们的梦想。在三个人中淑长得最美,身材高挑,五官端正,性格娴淑;她虽语言不多,却每每一语中的。而我与婷却都是咋咋呼呼一个争强一个斗胜的家伙,因此当仨人在一起时,总是我与婷俩人的嘴巴子斗得你死我活,烽火四起了,婷呢则在一边微笑着看热闹。而最让我与婷羡慕忌妒恨的是不管我们闹得如何不可开交,她呢总能一语中的,轻轻的把我们的死结打开。那一份气定神闲真是羡煞旁人,因此我们曾经戏谑她说:”如果我们是男人非取你为妻不可。”
就因为这些,当我与婷还在各自母亲的唠唠叨叨中躲避着过日子时,淑就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成为了小镇里某知名人家的媳妇,她的丈夫我们见过几次,是另一学校里的老师,人长得挺帅的,浪漫而多情,许多人都说他们俩是金童玉女般的绝配。
淑结婚后,就与翁婆们住到了一块,但她还是常常到我们宿舍里来与我们聊天,有时还给我们带一些小点心蔬菜瓜果等食物――据说是她婆婆做了让她带过来的。吃着她带来的这些食物,看着淑洋溢了一脸的幸福,我们打心眼里厦羡慕着。是的,红润的脸色,甜蜜的笑容无一不昭示着她的生活是幸福的。于是,茶余饭后的人们不管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小湖边的柳荫下,聊天时总喜欢拿她来说事。许多饭堂里的阿姨在给我们这些年轻女孩介绍对象时更是啧着嘴打着包票说”你放心好了,这户人家呀,就像淑家一样,嫁进去,绝对是享福的份。“
然而,淑结婚两年后,事情好像在发生着慢慢的变化,有时我们会发现她眉心间流露出点点的忧戚。记得1998那年,暑假来临的最后一天。学校开学期总结大会,会议结束时,人们在会议室前那棵荔枝树下说着告别的话。将近两个月的假期到来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与婷相约到BJ去旅游,淑沉闷地从会议室出来,我兴奋地迎上去揣了她一拳问:”BJ,你去不去?“
”什么?“也许我问得太突然了,淑有点茫然。
“假期去BJ玩玩,你去不去?”我重复了一遍。
“我……我家里有些事,不能去……祝你们玩得开心啦!”淑说完这句话后就转身离去了。婷看着淑的背影一脸沉思状的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劲呀……淑怎么了?”
经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异样。然而暑假的来临带给我们巨大的欢乐,刚刚的那一闪念很快就被我们完全忘记,在假期里我们不仅去BJ游了故宫,登长城做了一回“好汉”,还去了长江三峡……
八月尾新学年会议那天,学校教职员工们结束了多彩的假期生活,又从各地聚拢回来了。离开会还有几分钟,三三两两的人站在了校道两边的荔枝龙眼树下。快大开时淑才到来,她的脸色没有了先前的红润,也许是赶路过于匆忙吧,脸有点苍白。我担心的问她是不是病了,她随口应着说是有点感冒。后来会议结束后,我们把淑拉到宿舍里――这么久不见,心里有着许多的话要说。到了宿舍,婷缠着淑非要让她说说假期是怎么过的不可,是不是与老公去那里HAPPY了。在婷的一再纠缠下,淑沉吟了很久才说这个假期她根本就没出过门,一直都是在家里呆着。原来在放假时,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为了保险,都没计划出门远行。然而在假期临末了时才发现BB是女婴,结果做了人流“手术做完还不足一个星期。”淑平静地说。
是的,我们知道,淑的丈夫是独子,生个男孙是淑做为儿媳的必然使命。但是,计生法规定,禁止人为选择性的终止妊娠。难怪刚才淑在会议室门前一直推辞说是身体感冒,如果刚才说出来给别有用心的人听去了,那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可以让淑马上丢掉工作,就连给她检查胎儿性别,替她做手术的人都会受到连累。
“别担心,下次吧,下一次你一定能怀上男儿的。”我安慰她说。
“哎,听我妈说凤冈岭的送子观音很是灵验的,要不你去求求吧。”婷出主意说。
……
那之后,我不知道淑有没有去求过送子观音,但是在后来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淑进行了四次的人工流产,其中有一年做了三次流产手术,每一次手术都让淑好像大病一场那样。就这样,淑也由原来那个有名的大美人逐渐逐渐的变形――不仅脸上的红润完全消失,原来一直挂在上面的娴静的笑容也不见了,原先那丰满的体态也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高挑的身材一旦消瘦,便显出佝偻之态――美在淑的身上快速的流失着。
然而我与婷也都相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里――我们都结婚了,虽然我们曾经怀揣过梦想,但结婚了的女人不得不面对着横亘在我们女人面前的那一个沉重而无奈的话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上对于已经结婚的女子,虽然政府一再提倡男女平等,一再宣传”生男生女一个样“,但生个男孩是绝大多数男人心照不宣的愿望,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只能生一胎女公职人员来说便必须一箭中的,因此在人们的言语间便有了许多关于生男孩的秘诀,在性别相同的人群聚集的地方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永恒的话题。
然而不久,我就离开了那个小镇。与她们分别的前两天,我们有个小小的聚会,那是几个知心好友之间的聚会,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另两个已经结婚的女同事――都是年经人,只是她们遂心如意的生养到了儿子,那天,这两个生到男儿的同事告诉了我们一些生儿子的秘诀。
我不知道,淑与婷有没有按照秘诀那样去生育儿女,反正我没有――至于为什么没有,那是后话。
离开小镇后,我就没有再见过淑,只是常在QQ里与婷聊一些八卦事儿,有时也会说起淑,在这些零零碎碎的话语里,我知道淑一直都不怎么好――虽然老公,翁婆一如既往的待她好,但是她也一如既往的没生到男孩。还听说由于多次流产,淑闹上了盆腔炎等一些妇科疾病,常常往医院跑。当时听说她这么苦,在叹惜之余我总会在心里默默的祝福她,祝她早生贵子,脱离苦海。
然而我没想到最后听到的关于淑的竟是噩耗――死于宫外孕引发的大出血,我知道有些妇科疾病会引起宫外孕,也知道宫外孕的危险性。但我没想到淑竟然在身体没痊愈时会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受孕,我没想到这么美好的一段婚姻竟然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变成了淑的坟墓。我突然想,这一家子里的人真的懂得爱吗?她们,他们真的爱淑吗?
为何呀?为何我又听到了那呜呜咽咽的夜风的哭泣呢? 它们是在痛哭那流失了的美丽吗?
(注:这个为速写,为应蛤蟆挑战,未经怎么修改。抱歉。)
相似主题
正在浏览此帖子的用户
当前在线: 3 (会员: 0, 游客: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