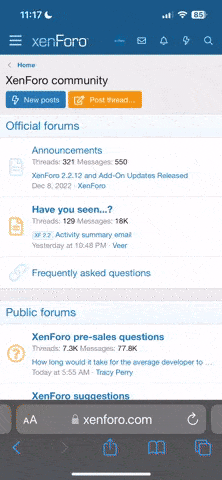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
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
一九九九年,人们所说的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那时候,我在湘西南和一个女孩恋爱。有一个下午,我走进奶奶家的木板房子,发现屋里真黑。灶台边却有一双很亮的眼睛。那个人身子小小的,灶火的红光照在她脸上。我问坐在一旁的姑妈,这就是樱子吗?姑妈笑着对小姑娘说,叫哥哥呀。
在此之前我见过樱子几次。那时她很小很小,但是她的眼睛很大很大,有一对罕见的单眼皮。我跟她说,有一次在堂屋里,我轮流背着你和你弟,满屋子跳,像只袋鼠。她咯咯直笑,又说,一点也记不得了。
又问她多大。说是满十一岁,吃十二岁的饭。一九九九年冬天的最后几天阳光像一群毛茸茸的小鸡跑满资江之滨那个小城的每个角落。我的手却是冰冰的。只是因为我的手一到冬天就很冰。在街道与街道之间,我拉着樱子小小的手,她的左手放在我右手的手心,有奇异的温暖。我在近乎金黄的河边反复说你不要放,一放我就冷了。樱子睁大了双眼,也许她认为我的手不应该像冬天的江水那样冷得不像个样子。但是她的手还是如我所愿地抓得更紧了,她一边摇晃我的手臂一边说,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呢?我回去以后,你怎么办?我说,走,我带你到山上去玩。
山是县城背后还没被挖开的山。还很胖的一座山。山上有很多树,还有各色野花野草。山深处草色很青,虫子安静地呆在自己的领地,春色关不住。不过高高的树的枝桠仍然什么也没有,朝天伸出硕大的手臂,天上呆满了动物。我们穿过一大片丛林和茅草,来到一小块草地。樱子抱着沿途采来的野花,让我给她编个花冠。我依言照办,花枝上的小刺刺破了我的手指,一抹淡红的血印在白色的花瓣上。我把那些小刺一个一个弄掉,她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你呢?她说我也不疼。她问我的时候盯着我的眼睛,眼神只是清澈得很。我笑了一下,很累地躺下。她把小小的头放在我的臂弯里说哥哥你看那儿有一只鸟。我朝她手指着的方向看,那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些云在活动。我摸到她脖子上有根细线,她说刚才真的有只鸟经过那里不过一下子就不见了。我问,这是什么?
这是一根线。她说。她把那线解开。是一根红线,勾着一个小小的玉坠。浅兰色的光。她爬起来把那东西系上我的粗脖子,勒得我很舒服。她说哥哥你脖子怎么这么粗啊。我感觉冬天忽然一闪不见了,像那只鸟。看来春天打算在这里住下,打算在我们身边修一座小茅屋。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情形是我在樱子的手心划来划去,问她暑假还来吗?樱子咬住她的而不是我的下嘴唇,出神地偏头思索,说,不知道。
我们就下山。发现路消失在杂树野草丛中。只听见各种声音在树外面叫。我跳下一堵不高的山崖下去找路。路找到了,路口就在我膝盖跪下的地方。我把膝盖碰在一快尖石上,血流出来,裤腿红了。我把樱子接下来,樱子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嚼一把茅柴叶子,嚼成糊状了就糊上伤口,血神奇地止住。我觉得她的泪有点多了影响了她眼睛和脸庞的美丽,就给她把泪水擦去,我觉得他她唇上的绿色汁液颜色有点深了就过去尝尝,我说真苦啊樱子,樱子笑了。
第二天她就走了。在车站我拉过她的小手亲了一下。姑妈看到了,樱子的脸飞起红云。
接着你应该可以猜出就是开学。开学了就是二000年了。在这一年里,我很想念樱子。我记起了日记。每天花一笔时间想她我觉得很不够,就记起了日记。还是不够呀,我必须让她知道我想她。我按她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过去,我每天去一趟收发室,但是并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后来我知道她把给我的信投进了邮电局的意见箱。在上述情形下,我想我必须见到她。
大概是二0000年四月份,我悄悄摸黑起床,清早搭上去她那里的汽车。
我从来没有去过湘西。姑妈家会在哪里?我只想见到樱子,于是去她的学校。在车上我看见散学的儿童背着书包在路上打闹。天色渐黑。我有点伤心。又担心。站在他们学校门口,里面的操场空空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走。这时,两个小女孩走过我的面前。其中一个打着伞,我没有看清她的面容。我看着这个拿伞者的背影,心想那真的是樱子吗?跟着她们两个,穿过了两条街,来到一个斜坡上。这是这个小镇最后一条街了,透过层层叠叠的房子,可以看见去年收割过的稻田。我试探地轻叫一声“樱子”,她转过头来了!跑过去举起她小小的身子,她鞋上的泥巴高兴地跑到我的裤腿上。
同行的小女孩说她先走了。樱子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哥哥你手又冷了。路边散学回家的学生一群一群地看着我们,我心里只想着我的小樱子,因此对不起我无法告诉你其中的女生长得如何。
甚至那个湘西的小镇是什么样子,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觉得十分亲切,仿佛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樱子陪我来到集市,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听她背书,背的是那课《武松打虎》。樱子用她好听的声音对我说:店家,筛三碗酒,切二斤熟牛肉来!
但是我只这样了一天,就不得不回去。姑妈说高三你怎么能跑这么远出来玩呢?我不知说什么好。樱子送我到一条叫渠河的河边,说哥哥等你再来我带你到这里来玩。
现在两年没见到樱子了。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告诉樱子我真喜欢她。我在一堆卵石上说我肯定要娶你的,樱子。不管在我身上发生多少游戏,这总归是句真话。二00一年的冬天到了,我的手又开始冰凉冰凉,使我很不舒服。
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
一九九九年,人们所说的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那时候,我在湘西南和一个女孩恋爱。有一个下午,我走进奶奶家的木板房子,发现屋里真黑。灶台边却有一双很亮的眼睛。那个人身子小小的,灶火的红光照在她脸上。我问坐在一旁的姑妈,这就是樱子吗?姑妈笑着对小姑娘说,叫哥哥呀。
在此之前我见过樱子几次。那时她很小很小,但是她的眼睛很大很大,有一对罕见的单眼皮。我跟她说,有一次在堂屋里,我轮流背着你和你弟,满屋子跳,像只袋鼠。她咯咯直笑,又说,一点也记不得了。
又问她多大。说是满十一岁,吃十二岁的饭。一九九九年冬天的最后几天阳光像一群毛茸茸的小鸡跑满资江之滨那个小城的每个角落。我的手却是冰冰的。只是因为我的手一到冬天就很冰。在街道与街道之间,我拉着樱子小小的手,她的左手放在我右手的手心,有奇异的温暖。我在近乎金黄的河边反复说你不要放,一放我就冷了。樱子睁大了双眼,也许她认为我的手不应该像冬天的江水那样冷得不像个样子。但是她的手还是如我所愿地抓得更紧了,她一边摇晃我的手臂一边说,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呢?我回去以后,你怎么办?我说,走,我带你到山上去玩。
山是县城背后还没被挖开的山。还很胖的一座山。山上有很多树,还有各色野花野草。山深处草色很青,虫子安静地呆在自己的领地,春色关不住。不过高高的树的枝桠仍然什么也没有,朝天伸出硕大的手臂,天上呆满了动物。我们穿过一大片丛林和茅草,来到一小块草地。樱子抱着沿途采来的野花,让我给她编个花冠。我依言照办,花枝上的小刺刺破了我的手指,一抹淡红的血印在白色的花瓣上。我把那些小刺一个一个弄掉,她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你呢?她说我也不疼。她问我的时候盯着我的眼睛,眼神只是清澈得很。我笑了一下,很累地躺下。她把小小的头放在我的臂弯里说哥哥你看那儿有一只鸟。我朝她手指着的方向看,那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些云在活动。我摸到她脖子上有根细线,她说刚才真的有只鸟经过那里不过一下子就不见了。我问,这是什么?
这是一根线。她说。她把那线解开。是一根红线,勾着一个小小的玉坠。浅兰色的光。她爬起来把那东西系上我的粗脖子,勒得我很舒服。她说哥哥你脖子怎么这么粗啊。我感觉冬天忽然一闪不见了,像那只鸟。看来春天打算在这里住下,打算在我们身边修一座小茅屋。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情形是我在樱子的手心划来划去,问她暑假还来吗?樱子咬住她的而不是我的下嘴唇,出神地偏头思索,说,不知道。
我们就下山。发现路消失在杂树野草丛中。只听见各种声音在树外面叫。我跳下一堵不高的山崖下去找路。路找到了,路口就在我膝盖跪下的地方。我把膝盖碰在一快尖石上,血流出来,裤腿红了。我把樱子接下来,樱子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嚼一把茅柴叶子,嚼成糊状了就糊上伤口,血神奇地止住。我觉得她的泪有点多了影响了她眼睛和脸庞的美丽,就给她把泪水擦去,我觉得他她唇上的绿色汁液颜色有点深了就过去尝尝,我说真苦啊樱子,樱子笑了。
第二天她就走了。在车站我拉过她的小手亲了一下。姑妈看到了,樱子的脸飞起红云。
接着你应该可以猜出就是开学。开学了就是二000年了。在这一年里,我很想念樱子。我记起了日记。每天花一笔时间想她我觉得很不够,就记起了日记。还是不够呀,我必须让她知道我想她。我按她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过去,我每天去一趟收发室,但是并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后来我知道她把给我的信投进了邮电局的意见箱。在上述情形下,我想我必须见到她。
大概是二0000年四月份,我悄悄摸黑起床,清早搭上去她那里的汽车。
我从来没有去过湘西。姑妈家会在哪里?我只想见到樱子,于是去她的学校。在车上我看见散学的儿童背着书包在路上打闹。天色渐黑。我有点伤心。又担心。站在他们学校门口,里面的操场空空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走。这时,两个小女孩走过我的面前。其中一个打着伞,我没有看清她的面容。我看着这个拿伞者的背影,心想那真的是樱子吗?跟着她们两个,穿过了两条街,来到一个斜坡上。这是这个小镇最后一条街了,透过层层叠叠的房子,可以看见去年收割过的稻田。我试探地轻叫一声“樱子”,她转过头来了!跑过去举起她小小的身子,她鞋上的泥巴高兴地跑到我的裤腿上。
同行的小女孩说她先走了。樱子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哥哥你手又冷了。路边散学回家的学生一群一群地看着我们,我心里只想着我的小樱子,因此对不起我无法告诉你其中的女生长得如何。
甚至那个湘西的小镇是什么样子,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觉得十分亲切,仿佛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樱子陪我来到集市,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听她背书,背的是那课《武松打虎》。樱子用她好听的声音对我说:店家,筛三碗酒,切二斤熟牛肉来!
但是我只这样了一天,就不得不回去。姑妈说高三你怎么能跑这么远出来玩呢?我不知说什么好。樱子送我到一条叫渠河的河边,说哥哥等你再来我带你到这里来玩。
现在两年没见到樱子了。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告诉樱子我真喜欢她。我在一堆卵石上说我肯定要娶你的,樱子。不管在我身上发生多少游戏,这总归是句真话。二00一年的冬天到了,我的手又开始冰凉冰凉,使我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