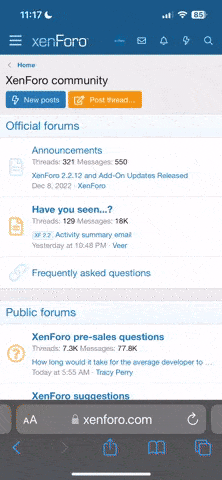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