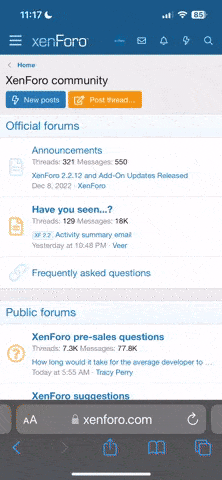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作者:连岳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作者:连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