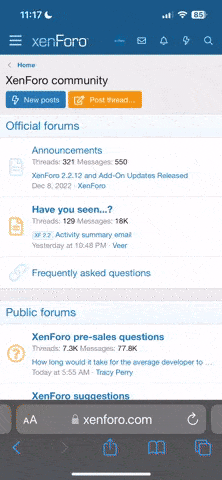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 注册
- 2004-09-06
- 帖子
- 65,791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61
我们知道,盘踞在中国北部的沙砾大集合正在以每年4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南扩张。这是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细想之又关系甚大的速度,这是一个无比引人关注的速度。然而,似乎同样应该令人注目的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起,一种几乎全新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方式已经悄然兴起,并且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了几乎所有存在中国青年的地方。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这种现象源自于“晕”――一种新的世界观。
“晕”,在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①昏迷;②头脑发昏;③日光或月光通过云层中的冰晶时经折射而形成的光圈;④光影、色彩四周模糊的部分。显然,这四种解释都是针对生理机能和物理现象而言,并不属于我们所谓的“晕”的讨论范畴。作为世界观的“晕”,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感知事物辨别事物的能力。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型网站上,“晕”被定义为:对某些不可预料的事件产生的较无奈的反应。其实这正是“晕”的雏形,我们可以理解为“晕”的世界观的萌芽状态。
哲学告诉我们,“感性认识是认识主体通过感觉器官在与对象发生实际的接触后产生的,它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具有直接性。”“晕”的第一次体现就发生在感性认识的短暂过程中。如果你有兴趣进行一次“晕”的体验,那么请你调动自己所有的积极性,将所有的好奇因子积压于胸口,然后以清晰的语音说出一个字――“晕”……好,祝贺你,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迄今为止,在所有已经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大概惟有“晕”的表达方式是最直接最简洁同时又最含糊不清的。也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它具有了巨大的潜力和凝聚力。假设“晕”是一团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空气。你把它压缩得无限小,此时,它所积聚起来的能量却是无限大。一旦获得释放,它将可以摧枯拉朽的波及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显而易见这只是一个过于夸张的比喻,但事实上,“晕”的实用性又的确已经被实践所证明。
也许你曾满心欢喜的赶赴一个约会,到达之后却发现对方通知错了地点;也许你曾毫无把握的参加一次考试,结果却出人意料地让你顺利通关;也许你曾毫不顾忌地将心事倾诉给朋友,却不料他会不加保留的将其转让于人;也许你曾满腹热忱地想要助人为乐,却没想到竟会讨上一个没好趣的冷眼……
当以上任一情况或者任一与之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统统可以用一个“晕”字来做个小结。“晕”是一种态度,它的作用在于让你不失态。当你失望或者惊喜的时候,它可让你的情绪不超过一个度,当你怨恼或者委屈的时候,它可让你的行为不超过一个极。它让你的思维在经历短暂的波动之后能够迅速回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它把惊喜、失望、气恼、委屈、指责、包容融为一体,并努力把你带入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由此,亦可以说,“晕”如同太极拳的刚柔相济,如同武学上的掌风骤起而止于发端,它的精彩在于它的点到为止。
李商隐眼里的爱情是“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泰戈尔则在他的诗歌里呼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说每个人的心里都装有一台天平,那么由于各人的性格、经历等诸多原因,天平将会沿着人的思维惯性,朝着与之对应的方向倾斜。简单地说,这样的方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朝想自己,即托盘;二是朝向远端,即砝码。这也是区别乐观主义者和悲观注意者的基本方法。但是,“晕”主义者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他们拥有一枚神奇的砝码,在面临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使天平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频率摆动,然后定格在一个可以维持两方平衡的位置。这不同于人们所说的“心如止水”,因为“心如止水”从开始便进入一种静态,它拒绝生活中一切渴望进入情感世界的请求。而“晕”主义者的情感大门则是完全敞开,他们的心灵托盘随时待命,准备着将计量的结果及时加入到思想的行列。此过程便是前面曾提到的“摆动”,摆动的目的是使其计量的结果尽量精确。从理论上讲,越是彻底的“晕”主义者,天平摆动的频率越快,时间越短,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越完善。
“晕”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既不能被完全了解,又能够被完全了解。(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还仅存于“晕”主义者的潜意识的最深处,因为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习惯性的思想居然也会被归结成文)乍听上去,会觉得这是悖论,其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但是,当我们对这个复句稍加揣摩,便会感觉,我们绝不能再以旧式的静止的局限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观点。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过程实质是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消亡的过程。照此看来,我们每了解一个事物,便会有更多的新事物产生。我们可以借助数轴来分析。假设我们面对世界上已知的最后一片未被开垦的领域,用了一个时间单位将它了解。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单位令为原点,那么原点以左的部分就是过去的时间和空间,原点以右的部分就是未来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把脚下的原点归入过去作为终点,我们便已经完全了解了世界上的事物;如果把脚下的原点并入未来作为起点,我们与终点的距离则是永远的遥遥无期。关键的问题是,脚下的原点到底该如何安置?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同样一片领域,假设我们有了解它的能力,并且已经将它了解。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已经完全被我们认识。但是忽略了一点――针对同一个事物,我们所了解的范围是可以扩展的。譬如对于我们居住的地球,就算我们准确地掌握了它的生物种类、地幔厚度、每一条河流的水文情况,甚至每一座火山爆发间隔的具体时间,但是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哑口无言――“太平洋里究竟有多少条鱼?”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难道要我们像智者那样回答“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吗?这样又得出了,未知领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被了解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果非要给这个时间加上一个期限,那么只能很遗憾地说,无限。“晕”主义者的观点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结论,它的本质是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没有准确的答案,解答是必要的,又是徒劳的。所以他们解答的时候往往会先说一句“晕”,然后再给出一个很随意的下文。
――去哪里吃饭?
――晕!这都要问我。随便去哪里好了。
以上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范本。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晕”的表达方式已经初步具有了地域性的差异。这恐怕是在其传播过程中,与具体的环境相结合所形成的。在网络中,“晕”的使用具有普遍性,但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天之骄子们常用的不是“晕”,而是“晕”的英文“faint”。随后在网络中还出现了“faint”的中文音译“奋特”。在语言的发展和交流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风”(广东话读作[taifuŋ])――typhoon――“台风”的借词回收现象。由此我们认为,“晕”不仅已经具有了全民性口头禅的趋势,还完全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气质。它的适应性是毋庸质疑的。
为了对“晕”了解得更深,我们不得不研究一下“晕”的形成背景。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产生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又以网络时代的兴起和繁荣作为一面最鲜明的旗帜,它昭示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已经进入全新的境界。
人类对世界的求知渴望随着网络世界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不断膨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后,网络的发展速度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而同时,对于已经存在的,人类又由于太过熟悉或者太过了解而不愿再深究。他们既渴望,又渴望不到,甚至就像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等待戈多一样,连戈多是谁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几乎全新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方式就自然而然应运而生了。
皮特•J•鲍勒在《思想进化史》中提到,“按照传统的观点,宇宙的历史并不太长,6天的创世纪就发生在几千年前。在17世纪,詹姆斯•厄谢尔主教试图通过将《圣经》中记载的祖先追溯到亚当来计算创世的时间,他认为创世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剑桥大学的副校长约翰•莱特弗特声称创造人类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9点。”
如果不考察约翰•莱特弗特是否属于无神论者,那么可以认为,“晕”的思想已经隐约地在他的大脑中起到了作用。我们看到,前人的解释已经足够荒谬,而他的更加荒谬的解释使整个事情看起来更像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其实本来就是),而且是场颇具影响的使人深思的闹剧。我们认为,当“晕”字已不直接存在于语言中,但能使语言的内涵存在“晕”的迹象,并能使人在与其接触的时候能产生“晕”的感觉,那么,“晕”就已经步入理性阶段了。
感性阶段的“晕”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上,而理性的“晕”则可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体育,以及由此衍生的更多细枝末节。当你看见“爱新觉罗•罗纳尔多”这样的网名,你感觉如何?当你看见《萌芽》红人luisborges在BBS上的签名“镜子和父性令人厌恶,因为他们使世界增殖”,你感觉如何?当英国记者格拉汉姆携带三个可疑包裹,以一本名字为“罗伯特•本•拉登”的通行证,顺利通过希腊政府耗费天价打造的安全系统时,你感觉又如何?晕!这真是个令宙斯神庙上方的众神也要为之一晕的世界。
作为我们所讨论的“晕”的发源地,网络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网络空间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世界,当网络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化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想要填补这片空白。但是,网络有它自己的精明,在别的文化到来之前,它已经率先诞生了自己的文化,并迅速开始越来越明显地作用于物质世界。目前,已经有人将网络中的一种文化命名为“Kuso”,意为某事物或某行为非常搞笑,属于笑死人不偿命一类。而“晕”的文化与Kuso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晕”不是纯粹的搞笑,甚至有时候它根本让人笑不起来,深刻的意蕴是“晕”的灵魂,其它的都只不是它的某种表面现象。
“孟加拉是个温柔的国度,风情浓郁,人民勤劳。但是,肆虐的洪水正在孟加拉的国土上汹涌,那里的人们流离失所,昔日的家园已成一片泽国。同为地球的居民,请为孟加拉的灾民祈福,求主保佑他们早日告别水患,重建家园。请将此条消息转发给至少10位网友,那样你的妈妈将会长命百岁,永远年轻。”如果有一天你打开QQ,接收到着这样的网友留言,千万不用惊讶。因为这正是网络中日益流行的一种连环性的问候方式,它在向需要帮助的人送出关爱的同时又给了你和你的家人一份美丽的祝愿。但是,这份祝愿只有在你为别人送出关爱和祝愿之后才能真正意义的收到。“晕”的精髓便蕴涵于此。
在创造互联网神话的网络游戏里,“晕”的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我们看见,一部分游戏玩家已经把虚拟的游戏人物当作了自己的第二生命,他们习惯将生活游走在现实与虚拟之间。他们也许在现实中失意,但在网络中得到了满足;他们也许在现实中得志,却在网络中面临着落魄。总之,频繁地时空交错使他们可以静下心来更平和地面对一些本来很复杂的问题,这是局外人费劲心机也不可抵达的心灵境界。
其实,不论是感性的“晕”抑或是理性的“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我们必须认识的。那就是它们都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中立性,这样的特点让我们对它的实质感觉到既随意又理智,既模糊又清晰,既沉郁又生动,既漫不经心又发人深省。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寻觅“晕”的影子,哪怕是与之相关的任何一点痕迹。这也是我们在前文中两次提到“几乎全新”的缘由。
老子说,“将欲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认为,人们想要把客观世界照主观意图加以认为的措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宇宙是自然的现象,是不可以改造的。改造它的人就会破坏它,坚持、执行它的人就会失掉它。老子从客观出发,提出了“无为”,但他却是个纯客观主义者,太纯注定了他太清醒,太清醒则致使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忽略了和清空了。这是老子学说的弊端,所以汉初统治者借用“无为”来休养生息,却没有将此作为一项长久的国策。
庄子则几乎与老子相反。《齐物论》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梦蝶,是其“物化”思想的必然产物。“物化”本是庄子思想体系的精华,可惜他却没有能够做到精益求精。庄子的“物化”,只注重了人与物、物与物(例如《逍遥游》中的鲲鹏)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具有浓郁的梦幻色彩。他没有将其进一步衍生为思想与思想的置换和辨证,而一味地在人与“蝴蝶”的角色位置上辗转反复,因此他的观点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无法对现实社会或者说社会存在产生更进步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庄子与“蝴蝶”纠缠太深,迷惘太深,终是止步于了后人所述的“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
中国古代文化的局限性是存在的,但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依然不会被撼动。诚如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说,“我没有现成的根据,没有可以照抄的模型。我是一位开拓者,所以我是渺小的,我希望读者诸君承认我成就的,原谅我未成就的。”老庄的年代已经过去数前年,他们所成就的文化正像作古的文明化石一样被我们陈列和瞻仰。老子是过于清醒了,庄子是太过迷梦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又该如何?
科学家们一直表明,“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并且它还在不断地扩大。”站在我们的角度看,既已无边,何来扩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很“晕”的定义。但是当任何一个答案都不能被我们完全肯定的时候,又似乎惟有这样的定义,才最能概括宇宙的内涵。这其实是一次折中的选择,“如果人的理念能积极地审视世界,事物的界限就变得透明了。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缘由和精神的存在。生命中最美的时刻莫过于此。” (爱默生)
至此,我们不得不将视线转移到民族的发展问题上来。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梦和醒有着本质的关联,醒着的可能影响着梦着的,梦着的也可能映射着醒着的。梦与醒本有界,细想之又无界,因为模糊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意蕴之美。从古至今,数千民族的兴衰存亡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永远梦着的民族是没有觉悟没有远见的民族;一个永远清醒着的民族是没有激情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惟有半梦半醒着,才能使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具备永恒的动力;惟有半梦半醒着,我们的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洗礼中不断前进,永葆青春。这也是某人费尽笔墨想要解释“晕”的意义所在。
“晕”,在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①昏迷;②头脑发昏;③日光或月光通过云层中的冰晶时经折射而形成的光圈;④光影、色彩四周模糊的部分。显然,这四种解释都是针对生理机能和物理现象而言,并不属于我们所谓的“晕”的讨论范畴。作为世界观的“晕”,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感知事物辨别事物的能力。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型网站上,“晕”被定义为:对某些不可预料的事件产生的较无奈的反应。其实这正是“晕”的雏形,我们可以理解为“晕”的世界观的萌芽状态。
哲学告诉我们,“感性认识是认识主体通过感觉器官在与对象发生实际的接触后产生的,它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具有直接性。”“晕”的第一次体现就发生在感性认识的短暂过程中。如果你有兴趣进行一次“晕”的体验,那么请你调动自己所有的积极性,将所有的好奇因子积压于胸口,然后以清晰的语音说出一个字――“晕”……好,祝贺你,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迄今为止,在所有已经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大概惟有“晕”的表达方式是最直接最简洁同时又最含糊不清的。也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它具有了巨大的潜力和凝聚力。假设“晕”是一团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空气。你把它压缩得无限小,此时,它所积聚起来的能量却是无限大。一旦获得释放,它将可以摧枯拉朽的波及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显而易见这只是一个过于夸张的比喻,但事实上,“晕”的实用性又的确已经被实践所证明。
也许你曾满心欢喜的赶赴一个约会,到达之后却发现对方通知错了地点;也许你曾毫无把握的参加一次考试,结果却出人意料地让你顺利通关;也许你曾毫不顾忌地将心事倾诉给朋友,却不料他会不加保留的将其转让于人;也许你曾满腹热忱地想要助人为乐,却没想到竟会讨上一个没好趣的冷眼……
当以上任一情况或者任一与之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统统可以用一个“晕”字来做个小结。“晕”是一种态度,它的作用在于让你不失态。当你失望或者惊喜的时候,它可让你的情绪不超过一个度,当你怨恼或者委屈的时候,它可让你的行为不超过一个极。它让你的思维在经历短暂的波动之后能够迅速回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它把惊喜、失望、气恼、委屈、指责、包容融为一体,并努力把你带入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由此,亦可以说,“晕”如同太极拳的刚柔相济,如同武学上的掌风骤起而止于发端,它的精彩在于它的点到为止。
李商隐眼里的爱情是“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泰戈尔则在他的诗歌里呼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说每个人的心里都装有一台天平,那么由于各人的性格、经历等诸多原因,天平将会沿着人的思维惯性,朝着与之对应的方向倾斜。简单地说,这样的方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朝想自己,即托盘;二是朝向远端,即砝码。这也是区别乐观主义者和悲观注意者的基本方法。但是,“晕”主义者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他们拥有一枚神奇的砝码,在面临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使天平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频率摆动,然后定格在一个可以维持两方平衡的位置。这不同于人们所说的“心如止水”,因为“心如止水”从开始便进入一种静态,它拒绝生活中一切渴望进入情感世界的请求。而“晕”主义者的情感大门则是完全敞开,他们的心灵托盘随时待命,准备着将计量的结果及时加入到思想的行列。此过程便是前面曾提到的“摆动”,摆动的目的是使其计量的结果尽量精确。从理论上讲,越是彻底的“晕”主义者,天平摆动的频率越快,时间越短,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越完善。
“晕”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既不能被完全了解,又能够被完全了解。(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还仅存于“晕”主义者的潜意识的最深处,因为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习惯性的思想居然也会被归结成文)乍听上去,会觉得这是悖论,其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但是,当我们对这个复句稍加揣摩,便会感觉,我们绝不能再以旧式的静止的局限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观点。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过程实质是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消亡的过程。照此看来,我们每了解一个事物,便会有更多的新事物产生。我们可以借助数轴来分析。假设我们面对世界上已知的最后一片未被开垦的领域,用了一个时间单位将它了解。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单位令为原点,那么原点以左的部分就是过去的时间和空间,原点以右的部分就是未来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把脚下的原点归入过去作为终点,我们便已经完全了解了世界上的事物;如果把脚下的原点并入未来作为起点,我们与终点的距离则是永远的遥遥无期。关键的问题是,脚下的原点到底该如何安置?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同样一片领域,假设我们有了解它的能力,并且已经将它了解。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已经完全被我们认识。但是忽略了一点――针对同一个事物,我们所了解的范围是可以扩展的。譬如对于我们居住的地球,就算我们准确地掌握了它的生物种类、地幔厚度、每一条河流的水文情况,甚至每一座火山爆发间隔的具体时间,但是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哑口无言――“太平洋里究竟有多少条鱼?”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难道要我们像智者那样回答“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吗?这样又得出了,未知领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被了解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果非要给这个时间加上一个期限,那么只能很遗憾地说,无限。“晕”主义者的观点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结论,它的本质是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没有准确的答案,解答是必要的,又是徒劳的。所以他们解答的时候往往会先说一句“晕”,然后再给出一个很随意的下文。
――去哪里吃饭?
――晕!这都要问我。随便去哪里好了。
以上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范本。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晕”的表达方式已经初步具有了地域性的差异。这恐怕是在其传播过程中,与具体的环境相结合所形成的。在网络中,“晕”的使用具有普遍性,但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天之骄子们常用的不是“晕”,而是“晕”的英文“faint”。随后在网络中还出现了“faint”的中文音译“奋特”。在语言的发展和交流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风”(广东话读作[taifuŋ])――typhoon――“台风”的借词回收现象。由此我们认为,“晕”不仅已经具有了全民性口头禅的趋势,还完全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气质。它的适应性是毋庸质疑的。
为了对“晕”了解得更深,我们不得不研究一下“晕”的形成背景。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产生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又以网络时代的兴起和繁荣作为一面最鲜明的旗帜,它昭示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已经进入全新的境界。
人类对世界的求知渴望随着网络世界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不断膨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后,网络的发展速度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而同时,对于已经存在的,人类又由于太过熟悉或者太过了解而不愿再深究。他们既渴望,又渴望不到,甚至就像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等待戈多一样,连戈多是谁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几乎全新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方式就自然而然应运而生了。
皮特•J•鲍勒在《思想进化史》中提到,“按照传统的观点,宇宙的历史并不太长,6天的创世纪就发生在几千年前。在17世纪,詹姆斯•厄谢尔主教试图通过将《圣经》中记载的祖先追溯到亚当来计算创世的时间,他认为创世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剑桥大学的副校长约翰•莱特弗特声称创造人类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9点。”
如果不考察约翰•莱特弗特是否属于无神论者,那么可以认为,“晕”的思想已经隐约地在他的大脑中起到了作用。我们看到,前人的解释已经足够荒谬,而他的更加荒谬的解释使整个事情看起来更像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其实本来就是),而且是场颇具影响的使人深思的闹剧。我们认为,当“晕”字已不直接存在于语言中,但能使语言的内涵存在“晕”的迹象,并能使人在与其接触的时候能产生“晕”的感觉,那么,“晕”就已经步入理性阶段了。
感性阶段的“晕”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上,而理性的“晕”则可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体育,以及由此衍生的更多细枝末节。当你看见“爱新觉罗•罗纳尔多”这样的网名,你感觉如何?当你看见《萌芽》红人luisborges在BBS上的签名“镜子和父性令人厌恶,因为他们使世界增殖”,你感觉如何?当英国记者格拉汉姆携带三个可疑包裹,以一本名字为“罗伯特•本•拉登”的通行证,顺利通过希腊政府耗费天价打造的安全系统时,你感觉又如何?晕!这真是个令宙斯神庙上方的众神也要为之一晕的世界。
作为我们所讨论的“晕”的发源地,网络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网络空间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世界,当网络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化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想要填补这片空白。但是,网络有它自己的精明,在别的文化到来之前,它已经率先诞生了自己的文化,并迅速开始越来越明显地作用于物质世界。目前,已经有人将网络中的一种文化命名为“Kuso”,意为某事物或某行为非常搞笑,属于笑死人不偿命一类。而“晕”的文化与Kuso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晕”不是纯粹的搞笑,甚至有时候它根本让人笑不起来,深刻的意蕴是“晕”的灵魂,其它的都只不是它的某种表面现象。
“孟加拉是个温柔的国度,风情浓郁,人民勤劳。但是,肆虐的洪水正在孟加拉的国土上汹涌,那里的人们流离失所,昔日的家园已成一片泽国。同为地球的居民,请为孟加拉的灾民祈福,求主保佑他们早日告别水患,重建家园。请将此条消息转发给至少10位网友,那样你的妈妈将会长命百岁,永远年轻。”如果有一天你打开QQ,接收到着这样的网友留言,千万不用惊讶。因为这正是网络中日益流行的一种连环性的问候方式,它在向需要帮助的人送出关爱的同时又给了你和你的家人一份美丽的祝愿。但是,这份祝愿只有在你为别人送出关爱和祝愿之后才能真正意义的收到。“晕”的精髓便蕴涵于此。
在创造互联网神话的网络游戏里,“晕”的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我们看见,一部分游戏玩家已经把虚拟的游戏人物当作了自己的第二生命,他们习惯将生活游走在现实与虚拟之间。他们也许在现实中失意,但在网络中得到了满足;他们也许在现实中得志,却在网络中面临着落魄。总之,频繁地时空交错使他们可以静下心来更平和地面对一些本来很复杂的问题,这是局外人费劲心机也不可抵达的心灵境界。
其实,不论是感性的“晕”抑或是理性的“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我们必须认识的。那就是它们都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中立性,这样的特点让我们对它的实质感觉到既随意又理智,既模糊又清晰,既沉郁又生动,既漫不经心又发人深省。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寻觅“晕”的影子,哪怕是与之相关的任何一点痕迹。这也是我们在前文中两次提到“几乎全新”的缘由。
老子说,“将欲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认为,人们想要把客观世界照主观意图加以认为的措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宇宙是自然的现象,是不可以改造的。改造它的人就会破坏它,坚持、执行它的人就会失掉它。老子从客观出发,提出了“无为”,但他却是个纯客观主义者,太纯注定了他太清醒,太清醒则致使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忽略了和清空了。这是老子学说的弊端,所以汉初统治者借用“无为”来休养生息,却没有将此作为一项长久的国策。
庄子则几乎与老子相反。《齐物论》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梦蝶,是其“物化”思想的必然产物。“物化”本是庄子思想体系的精华,可惜他却没有能够做到精益求精。庄子的“物化”,只注重了人与物、物与物(例如《逍遥游》中的鲲鹏)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具有浓郁的梦幻色彩。他没有将其进一步衍生为思想与思想的置换和辨证,而一味地在人与“蝴蝶”的角色位置上辗转反复,因此他的观点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无法对现实社会或者说社会存在产生更进步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庄子与“蝴蝶”纠缠太深,迷惘太深,终是止步于了后人所述的“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
中国古代文化的局限性是存在的,但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依然不会被撼动。诚如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说,“我没有现成的根据,没有可以照抄的模型。我是一位开拓者,所以我是渺小的,我希望读者诸君承认我成就的,原谅我未成就的。”老庄的年代已经过去数前年,他们所成就的文化正像作古的文明化石一样被我们陈列和瞻仰。老子是过于清醒了,庄子是太过迷梦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又该如何?
科学家们一直表明,“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并且它还在不断地扩大。”站在我们的角度看,既已无边,何来扩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很“晕”的定义。但是当任何一个答案都不能被我们完全肯定的时候,又似乎惟有这样的定义,才最能概括宇宙的内涵。这其实是一次折中的选择,“如果人的理念能积极地审视世界,事物的界限就变得透明了。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缘由和精神的存在。生命中最美的时刻莫过于此。” (爱默生)
至此,我们不得不将视线转移到民族的发展问题上来。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梦和醒有着本质的关联,醒着的可能影响着梦着的,梦着的也可能映射着醒着的。梦与醒本有界,细想之又无界,因为模糊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意蕴之美。从古至今,数千民族的兴衰存亡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永远梦着的民族是没有觉悟没有远见的民族;一个永远清醒着的民族是没有激情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惟有半梦半醒着,才能使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具备永恒的动力;惟有半梦半醒着,我们的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洗礼中不断前进,永葆青春。这也是某人费尽笔墨想要解释“晕”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