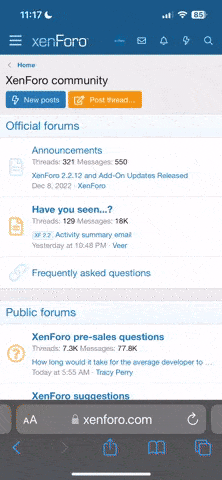电白狂人
小学一年级
- 注册
- 2006-09-14
- 帖子
- 120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0
教师责任正在演变成无限责任 压力增大健康透支
2006年10月23日 07:51: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打印】 【我要纠错】 【Email推荐: 】
“老师如果任由自己的责任心做事,早晚会被‘责任’这两个字累死。我决不让我的儿子再当老师。”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老师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不少有孩子的教师正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树立更为“远大”的理想,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再当老师了。
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
“从知道当老师那天起我就不自觉地背起了这个责任”,参加工作11年的魏东盈老师说。
“第一天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双渴望的眼睛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要把他们教育成才的冲动。”回忆当时,魏老师嘴唇有些轻轻地颤抖,“我知道这就是责任”。
和魏老师一样,不少老师从站在讲台上那天起便不知不觉地“严于律己”起来。别人可以适时地偷个懒,老师不行;别人可以不高兴时发个牢骚,老师不行;别人可以在不太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做点儿小坏事,老师不行……老师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老师在孩子们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如果没有极强的责任心,不仅会误人子弟,“我们首先就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快到退休年龄的张琳老师说。
就为了这个良心,不少教师自觉地让自己做得更多。
然而,这个责任似乎有了越来越重的趋势。
上个学期,魏老师班里两个学生放学时互相推搡,一个孩子倒地小腿骨折。因为“出事的地点就在学校门口”,骨折学生的家长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们并不是不想管学生,只是这一管就没边儿了”。
据了解,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取消了春游和秋游,不少学校的体育课也把“跳山羊”等危险运动取消了。只要一到课间,魏老师就守在自己班教室门口,为的就是“尽职尽责”地保护学生的安全。
“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张老师说。
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教师在透支健康
“现在社会上在宣传孟二冬,他确实是个好教师,但其实在我们普教系统这样的老师还很多。”在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担任校长的孙立老师说,他们学校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职业病。
“我们不是不想休息,是根本不敢休息。”魏老师说。
今年魏老师一个50岁的同事得癌症离开了人世,还有两个同事不到五十就得了冠心病,好几个将要退休的老师已经成了“药罐子”。“看着这些老师,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悲惨的未来”,魏老师说。
即使这样,老师们仍然不舍得专门拿出时间来休息,除非病倒了。
身为班主任的魏老师给记者描述了她典型的一天。
早上6:30来到学校上早自习,然后上课,课间到教室巡视,自己没课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判作业,不过这时通常会有其他科目的老师找到自己,跟她交流自己班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中午要看着在学校吃饭的学生吃饭,以免他们把吃不完的食物随手乱扔,而自己则要一点左右才能吃上饭。之后又开始了同上午相同的过程。学生下课后,还有打扫卫生、各种选修课、兴趣班,所有这些结束了也就到了下午六七点。这时距魏老师早上从家出门已经十二三个小时了,还不算给学生补课的时间。
晚上回家以后,魏老师还要备课、改作业。“有人形容我们睡得比猫少,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跑得比马快”,魏老师说,这种描述也许有些夸张,但却形象地反映出了普通教师的生活。
“近两年我们也意识到了老师的健康问题”,担任校领导的孙立老师介绍,从去年起他们学校规定,每天下班前半小时是老师锻炼身体的时间。刚开始,老师们还能坚持,但是慢慢地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少。每天校领导要挨着办公室去动员,老师们却说:“我们知道学校是为了我们好,可是我们都出去锻炼了,剩下的活儿谁帮我们做,您就别给我们增添负担了。”
竞争无止境减负让教师的负担明降暗升
如果说班主任的工作强度来自每天披星戴月地工作,那么普通老师的压力则来自日常教学。
“虽然上面规定评价学校不能只看分数,可每到高考结束,区里都会把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列出来,这些学生的学校就列在后面。”孙立老师说,“这不明摆着还是要我们向分数看齐吗”?
学生的成绩好,老师评级就容易,奖金也会高。
于是,学生的分数事实上成了衡量老师工作质量的最主要指标。老师们表面上和和气气,其实暗地里都在较着劲儿,生怕自己班学生的成绩不如别人。
比了考试成绩还要比学科竞赛成绩,没得比了就比纪律,比运动会成绩……
“这种竞争无休无止,只要想分出高下,你总能找出和别人竞争的项目”,张老师说。
但对副科老师来说,连参与这种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我还是希望成为正课老师,至少我可以有一个跟别人竞争的资格。”魏老师说。
魏老师除了班主任工作外,还教一个年级的政治课,一周12节。
今年5月,魏老师教的政治课就结业了。从5月到放假的两个月时间里,魏老师清闲了。
“确实是难得清闲,可这两个月的收入也大不一样”,魏老师说,因为没课学校就不发给她结构工资,奖金也没份儿。
这个结构工资可不容轻视。据知情人透露,北京市一些还算不错的学校,一个普通老师的“结构”大概有四五千元。
工资缩水还是小事,关键是副科老师在评级、评职称上也受很大影响。
魏老师1994年大学毕业,在北京一所郊区学校工作,工作12年了她的职称仍然是“初级”,而她的同学绝大多数早已经是中级了。“评级、评职称的时候中考成绩是一个挺大的加分指标,我是副科老师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为了自己的前途,魏老师现在又报了个英语大专班,每个周末她都要从郊区赶到市里的学校上课,“我的不少同学早就想办法转成主科老师了。我现在30多岁,再不改损失就太大了”。
魏老师还有一个6岁大的女儿,父母的身体也不好,但是她还是决然地把自己逼到了没有一点休息时间的境地。据她说,现在她这个年龄的教师,不少都跟她一样。“我们经常和女儿开玩笑,妈妈是要把咱们家打造成学习型家庭”。
有人说,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老师只要把课教好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现在的课可不像以前那么好教了”,已经教了30年书的张老师介绍,这些年教材经常变,而且不少教材的适用性较差。
张老师打了个比方:“学生掌握知识的顺序是A到B再到C,但现在的知识是先出现A,然后出现C,这中间的B则只能由老师自己补课”。
魏老师说,为了配合改革,现在年轻老师每学期都要“做课”,每次做课都要花上个把月的时间做准备,“如果一个学期做两次课,这个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魏老师说。
不再受人尊重让老师们难受
其实,苦点儿累点儿还不至于让老师们下决心不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自己的职业不再受人尊重才让老师们更痛苦。
“我现在在外人面前很少提自己的职业”,张琳老师说。她刚走上教师岗位时特自豪,说起自己的职业都会扬起脸。但现在,这个职业不再能带给她尊重。
“现在的年轻老师太看重钱,这不能全怪他们,整个社会都是以挣钱多少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在张老师眼里,是年轻教师的“向钱看”给教师这个职业抹了黑。
“以前我们课余给学生补课是分内的事”,张老师说,但现在她发现有些年轻老师给学生补课竟然是收费的。张老师介绍,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办补习班十分普遍。甚至还有一些家长把老师找到家里给孩子当家教。
以前的老师虽然清贫但是却赢得了整个社会的尊敬,现在老师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但是他们赢得的尊重却瘪了下去。
孙立校长说:“其实我们不用专门阻止孩子当老师”,孙老师自己的孩子还不大的时候,就经常跟他说:“你不用劝我,看见你我就够了,我决不会再走跟你一样的路。”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章老师文字均为化名)(樊未晨)
2006年10月23日 07:51: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打印】 【我要纠错】 【Email推荐: 】
“老师如果任由自己的责任心做事,早晚会被‘责任’这两个字累死。我决不让我的儿子再当老师。”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老师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不少有孩子的教师正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树立更为“远大”的理想,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再当老师了。
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
“从知道当老师那天起我就不自觉地背起了这个责任”,参加工作11年的魏东盈老师说。
“第一天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双渴望的眼睛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要把他们教育成才的冲动。”回忆当时,魏老师嘴唇有些轻轻地颤抖,“我知道这就是责任”。
和魏老师一样,不少老师从站在讲台上那天起便不知不觉地“严于律己”起来。别人可以适时地偷个懒,老师不行;别人可以不高兴时发个牢骚,老师不行;别人可以在不太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做点儿小坏事,老师不行……老师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老师在孩子们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如果没有极强的责任心,不仅会误人子弟,“我们首先就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快到退休年龄的张琳老师说。
就为了这个良心,不少教师自觉地让自己做得更多。
然而,这个责任似乎有了越来越重的趋势。
上个学期,魏老师班里两个学生放学时互相推搡,一个孩子倒地小腿骨折。因为“出事的地点就在学校门口”,骨折学生的家长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们并不是不想管学生,只是这一管就没边儿了”。
据了解,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取消了春游和秋游,不少学校的体育课也把“跳山羊”等危险运动取消了。只要一到课间,魏老师就守在自己班教室门口,为的就是“尽职尽责”地保护学生的安全。
“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张老师说。
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教师在透支健康
“现在社会上在宣传孟二冬,他确实是个好教师,但其实在我们普教系统这样的老师还很多。”在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担任校长的孙立老师说,他们学校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职业病。
“我们不是不想休息,是根本不敢休息。”魏老师说。
今年魏老师一个50岁的同事得癌症离开了人世,还有两个同事不到五十就得了冠心病,好几个将要退休的老师已经成了“药罐子”。“看着这些老师,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悲惨的未来”,魏老师说。
即使这样,老师们仍然不舍得专门拿出时间来休息,除非病倒了。
身为班主任的魏老师给记者描述了她典型的一天。
早上6:30来到学校上早自习,然后上课,课间到教室巡视,自己没课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判作业,不过这时通常会有其他科目的老师找到自己,跟她交流自己班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中午要看着在学校吃饭的学生吃饭,以免他们把吃不完的食物随手乱扔,而自己则要一点左右才能吃上饭。之后又开始了同上午相同的过程。学生下课后,还有打扫卫生、各种选修课、兴趣班,所有这些结束了也就到了下午六七点。这时距魏老师早上从家出门已经十二三个小时了,还不算给学生补课的时间。
晚上回家以后,魏老师还要备课、改作业。“有人形容我们睡得比猫少,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跑得比马快”,魏老师说,这种描述也许有些夸张,但却形象地反映出了普通教师的生活。
“近两年我们也意识到了老师的健康问题”,担任校领导的孙立老师介绍,从去年起他们学校规定,每天下班前半小时是老师锻炼身体的时间。刚开始,老师们还能坚持,但是慢慢地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少。每天校领导要挨着办公室去动员,老师们却说:“我们知道学校是为了我们好,可是我们都出去锻炼了,剩下的活儿谁帮我们做,您就别给我们增添负担了。”
竞争无止境减负让教师的负担明降暗升
如果说班主任的工作强度来自每天披星戴月地工作,那么普通老师的压力则来自日常教学。
“虽然上面规定评价学校不能只看分数,可每到高考结束,区里都会把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列出来,这些学生的学校就列在后面。”孙立老师说,“这不明摆着还是要我们向分数看齐吗”?
学生的成绩好,老师评级就容易,奖金也会高。
于是,学生的分数事实上成了衡量老师工作质量的最主要指标。老师们表面上和和气气,其实暗地里都在较着劲儿,生怕自己班学生的成绩不如别人。
比了考试成绩还要比学科竞赛成绩,没得比了就比纪律,比运动会成绩……
“这种竞争无休无止,只要想分出高下,你总能找出和别人竞争的项目”,张老师说。
但对副科老师来说,连参与这种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我还是希望成为正课老师,至少我可以有一个跟别人竞争的资格。”魏老师说。
魏老师除了班主任工作外,还教一个年级的政治课,一周12节。
今年5月,魏老师教的政治课就结业了。从5月到放假的两个月时间里,魏老师清闲了。
“确实是难得清闲,可这两个月的收入也大不一样”,魏老师说,因为没课学校就不发给她结构工资,奖金也没份儿。
这个结构工资可不容轻视。据知情人透露,北京市一些还算不错的学校,一个普通老师的“结构”大概有四五千元。
工资缩水还是小事,关键是副科老师在评级、评职称上也受很大影响。
魏老师1994年大学毕业,在北京一所郊区学校工作,工作12年了她的职称仍然是“初级”,而她的同学绝大多数早已经是中级了。“评级、评职称的时候中考成绩是一个挺大的加分指标,我是副科老师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为了自己的前途,魏老师现在又报了个英语大专班,每个周末她都要从郊区赶到市里的学校上课,“我的不少同学早就想办法转成主科老师了。我现在30多岁,再不改损失就太大了”。
魏老师还有一个6岁大的女儿,父母的身体也不好,但是她还是决然地把自己逼到了没有一点休息时间的境地。据她说,现在她这个年龄的教师,不少都跟她一样。“我们经常和女儿开玩笑,妈妈是要把咱们家打造成学习型家庭”。
有人说,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老师只要把课教好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现在的课可不像以前那么好教了”,已经教了30年书的张老师介绍,这些年教材经常变,而且不少教材的适用性较差。
张老师打了个比方:“学生掌握知识的顺序是A到B再到C,但现在的知识是先出现A,然后出现C,这中间的B则只能由老师自己补课”。
魏老师说,为了配合改革,现在年轻老师每学期都要“做课”,每次做课都要花上个把月的时间做准备,“如果一个学期做两次课,这个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魏老师说。
不再受人尊重让老师们难受
其实,苦点儿累点儿还不至于让老师们下决心不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自己的职业不再受人尊重才让老师们更痛苦。
“我现在在外人面前很少提自己的职业”,张琳老师说。她刚走上教师岗位时特自豪,说起自己的职业都会扬起脸。但现在,这个职业不再能带给她尊重。
“现在的年轻老师太看重钱,这不能全怪他们,整个社会都是以挣钱多少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在张老师眼里,是年轻教师的“向钱看”给教师这个职业抹了黑。
“以前我们课余给学生补课是分内的事”,张老师说,但现在她发现有些年轻老师给学生补课竟然是收费的。张老师介绍,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办补习班十分普遍。甚至还有一些家长把老师找到家里给孩子当家教。
以前的老师虽然清贫但是却赢得了整个社会的尊敬,现在老师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但是他们赢得的尊重却瘪了下去。
孙立校长说:“其实我们不用专门阻止孩子当老师”,孙老师自己的孩子还不大的时候,就经常跟他说:“你不用劝我,看见你我就够了,我决不会再走跟你一样的路。”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章老师文字均为化名)(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