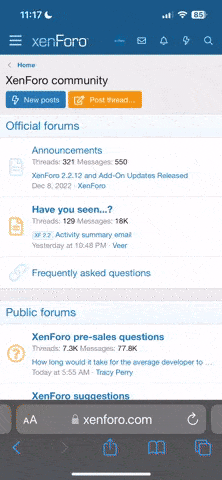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 注册
- 2005-04-12
- 帖子
- 2,489
- 反馈评分
- 452
- 点数
- 191
- 年龄
- 45
为了避免引咎辞职条款在公务员法施行过程中逐步蜕变成一纸空文,立法机关还有必要更上层楼,引进公务员弹劾制,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体系,并且进一步健全和改善对政府的实体性民主控制
□ 季卫东/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2006年1月1日开始生效。这部法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表明,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来加强对官吏守法性的监控,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因此,公务员的职业化、中立化、合理化以及加强责任观念和制裁机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最基本的规范指标。
根据现代科层制研究的先驱者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框架,中国传统的官僚系统属于家产制的范畴,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类似私有物品的特征。虽然科举本身具有普遍主义色彩,但考试的评判标准不是法律知识和职业化管理的技能,行政活动的担当者都被视为君主的家臣或者“天子门生”,甚至上官与僚属之间也往往靠个人化的眷顾、服从、忠诚的特殊纽带来维系,例如曾国藩之于湘军将领。其结果,国家机器的操作很容易偏离公共目的,纲纪往往因乡愿而废弛,正式的官职岗位也逐步蜕化成私下交易的对象或者某种势力集团所固守不放的寻租地盘。
为了打破这样的家产制窠臼、防止政府官员因公私混淆而产生的腐败堕落,在中国建立的现代公务员制度,首先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以及全体民众的公共目的,而不能为结党营私留下任何方便之门;各级官吏也必须恪守对事不对人的职务规则,超越个人信念和部门、集团的动机而以普遍性的国家利益为行动目的。一般而言,凭借公务员考试、任命资格以及行政组织内部的严格纪律等一整套制度设计,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官僚系统的非个人化和合理化。
但不能不指出,文官考试的障壁同时也有可能构成特权阶层的堡垒;公务员的身份保障难免导致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吃老本、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惰性以及在官官相护过程中不断趋于严重的行政低效。要克服这类流弊,还应该进一步采取适当的人事更迭政策,并加强对行政权的民主监控,使官僚系统成为某种形态的“责任科层制”。与承包责任制的内部追究、对上负责不同,所谓责任科层制,以问责程序为轴心,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对来自政府外部的民意代表、舆论以及公民个人的质询、批评以及控告,严格履行回应和说明的义务,直至依法接受正式的弹劾裁判。
结合时政并从“责任科层制”的观点来解读新施行的公务员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82条第三款(引咎辞职规定)和第四款(责令辞职规定)。按照这两个问责条款,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如因自身失职或严重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符合引咎辞职条件而本人不提出的,上级或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辞职。不言而喻,立法者的意图是要通过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方式,来调整官员正常退出机制、减少冗员、加快管理机构和各种职能组织的新陈代谢,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以制度化的方式发挥鞭策和警示作用,减少官僚阶层倦勤的习气。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靠整风运动来维持勤政和廉政。整风运动对克服科层制的僵化是颇有裨益的,但这种方式以具有超凡色彩的领袖和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共识为前提,对政府的职业化、制度化运作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以及副作用。在公务员法施行以后,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原理以及人事更迭政策,将更多地体现在该法第82条及其他日常性纲纪制裁的规章的执行过程之中,形成现代法理型统治方式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公务员法所正式确立的引咎辞职制度,在客观上已经否定了党政领导无谬误的神话,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与权力禅让、政绩延续性相联系的官场潜规则的紧箍咒,有助于在借助程序理性迅速改变人事布置之后,及时纠正过去的错误,化解民间的怨结不平之气,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局面。
毋庸讳言,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的报应和制裁机制,实际上或多或少陷于一种功能麻痹的状态。在企业,表现为科尔奈教授所说的“预算制约的软化”,国家父爱主义使管理层和职工都感觉不到经营失败的风险压力。在政府,官员不必接受议会质询,不必直接面对民意的监控,只要朝中有保护伞,就不必担心因工作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只要紧跟上司,哪怕群众意见再大,也还是可以不断升迁。按照承包原理追究责任者的做法虽然不无效果,但往往受阻于个人包办和相互包庇的黑箱操作。公务员法的引咎辞职条款,实际上是往承包制的旧瓶里注入了问责制的新酒,使报应和制裁机制的开启自动化,不受个人化特殊关系的羁绊。
引咎辞职制度显然大幅度扩展了从政生涯的风险和不可预测性,形成一种让人战战兢兢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增强执政者的责任伦理,也会使某些人望而却步,从而改变社会价值取向的官本位畸形。但不能不看到,这种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官僚阶层对公务员法第82条的集体抵制――很少有人引咎辞职,也很难让人责令辞职。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形:引咎辞职条款在执行之际被上下其手,最终扭曲成一种整人的权术,激化官场内部的派系倾轧,非到问责的逻辑在被推演到“人人有责”的极端并且反过来变成“人人不负责”的那一刻,谁也不肯善罢甘休。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公务员法第82条第三款和第四款都势必流于形式。
为了避免引咎辞职条款在公务员法施行过程中逐步蜕变成一纸空文,立法机关还有必要更上层楼,引进公务员弹劾制,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体系,并且进一步健全和改善对政府的实体性民主控制,其中特别重要的因素有两项,即宪法已经明文规定的代议机构的监督权和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如果没有这些配套要件和制度性保障,引咎辞职条款就很难有效地发挥作为激励装置的功能。-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本刊法学顾问
背景
“引咎辞职”入法
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实施。这部针对公务员的立法,涉及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职务职级、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位聘任、职务升降、奖励、纪律与处分、工资保险福利、培训、交流、回避、退休、申诉控告等内容。
《公务员法》第82条有关“引咎辞职”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这部法律的一大亮点。该条第三款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第四款则进一步规定:“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是国外常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常规做法。一般而言,“引咎辞职”有两个基本判断标准:一是非直接责任;二是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的自愿。这种官员退出机制不同于强制性组织纪律和法律处分,是公务员在其行为尚不够纪律法律处分、又必须退出公务员队伍的状态下,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
“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同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观念一脉相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拨乱反正,很多受“文革”冲击的老干部官复原职,但也出现了部门副职较多的现象。比如当时的冶金工业部,有一个正部长,26个副部长。淘汰机制缺乏,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状态普遍存在。除了个别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官员退出官场几乎鲜见。退出机制不畅,导致行政队伍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
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其中第四十条规定“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个人申请辞职和责令辞职”,从而开辟了官员退出的新机制。
此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机构改革,仅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
“引咎辞职”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事管理制度中,源于200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其第七条指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
2002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3年SARS爆发期间的高官问责,使得“引咎辞职”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此后一年间,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县元宵节踩踏事件以及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一系列事件都带来官员的“引咎辞职”。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并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
就在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前夕,2005年12月2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国务院免去其局长职务。这一事件,从某种意义上为《公务员法》的实施,尤其是引咎辞职条款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
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引咎辞职”真正纳入了法律制度,可谓意义重大。不过,目前《公务员法》在引咎辞职条款方面显然还停留在原则性规定方面。究竟什么样的情形、什么级别的官员、依照什么程序提出引咎辞职,都没有明确解释。中国的引咎辞职制度显然还有待完善。-
□ 季卫东/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2006年1月1日开始生效。这部法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表明,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来加强对官吏守法性的监控,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因此,公务员的职业化、中立化、合理化以及加强责任观念和制裁机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最基本的规范指标。
根据现代科层制研究的先驱者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框架,中国传统的官僚系统属于家产制的范畴,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类似私有物品的特征。虽然科举本身具有普遍主义色彩,但考试的评判标准不是法律知识和职业化管理的技能,行政活动的担当者都被视为君主的家臣或者“天子门生”,甚至上官与僚属之间也往往靠个人化的眷顾、服从、忠诚的特殊纽带来维系,例如曾国藩之于湘军将领。其结果,国家机器的操作很容易偏离公共目的,纲纪往往因乡愿而废弛,正式的官职岗位也逐步蜕化成私下交易的对象或者某种势力集团所固守不放的寻租地盘。
为了打破这样的家产制窠臼、防止政府官员因公私混淆而产生的腐败堕落,在中国建立的现代公务员制度,首先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以及全体民众的公共目的,而不能为结党营私留下任何方便之门;各级官吏也必须恪守对事不对人的职务规则,超越个人信念和部门、集团的动机而以普遍性的国家利益为行动目的。一般而言,凭借公务员考试、任命资格以及行政组织内部的严格纪律等一整套制度设计,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官僚系统的非个人化和合理化。
但不能不指出,文官考试的障壁同时也有可能构成特权阶层的堡垒;公务员的身份保障难免导致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吃老本、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惰性以及在官官相护过程中不断趋于严重的行政低效。要克服这类流弊,还应该进一步采取适当的人事更迭政策,并加强对行政权的民主监控,使官僚系统成为某种形态的“责任科层制”。与承包责任制的内部追究、对上负责不同,所谓责任科层制,以问责程序为轴心,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对来自政府外部的民意代表、舆论以及公民个人的质询、批评以及控告,严格履行回应和说明的义务,直至依法接受正式的弹劾裁判。
结合时政并从“责任科层制”的观点来解读新施行的公务员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82条第三款(引咎辞职规定)和第四款(责令辞职规定)。按照这两个问责条款,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如因自身失职或严重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符合引咎辞职条件而本人不提出的,上级或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辞职。不言而喻,立法者的意图是要通过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方式,来调整官员正常退出机制、减少冗员、加快管理机构和各种职能组织的新陈代谢,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以制度化的方式发挥鞭策和警示作用,减少官僚阶层倦勤的习气。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靠整风运动来维持勤政和廉政。整风运动对克服科层制的僵化是颇有裨益的,但这种方式以具有超凡色彩的领袖和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共识为前提,对政府的职业化、制度化运作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以及副作用。在公务员法施行以后,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原理以及人事更迭政策,将更多地体现在该法第82条及其他日常性纲纪制裁的规章的执行过程之中,形成现代法理型统治方式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公务员法所正式确立的引咎辞职制度,在客观上已经否定了党政领导无谬误的神话,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与权力禅让、政绩延续性相联系的官场潜规则的紧箍咒,有助于在借助程序理性迅速改变人事布置之后,及时纠正过去的错误,化解民间的怨结不平之气,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局面。
毋庸讳言,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的报应和制裁机制,实际上或多或少陷于一种功能麻痹的状态。在企业,表现为科尔奈教授所说的“预算制约的软化”,国家父爱主义使管理层和职工都感觉不到经营失败的风险压力。在政府,官员不必接受议会质询,不必直接面对民意的监控,只要朝中有保护伞,就不必担心因工作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只要紧跟上司,哪怕群众意见再大,也还是可以不断升迁。按照承包原理追究责任者的做法虽然不无效果,但往往受阻于个人包办和相互包庇的黑箱操作。公务员法的引咎辞职条款,实际上是往承包制的旧瓶里注入了问责制的新酒,使报应和制裁机制的开启自动化,不受个人化特殊关系的羁绊。
引咎辞职制度显然大幅度扩展了从政生涯的风险和不可预测性,形成一种让人战战兢兢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增强执政者的责任伦理,也会使某些人望而却步,从而改变社会价值取向的官本位畸形。但不能不看到,这种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官僚阶层对公务员法第82条的集体抵制――很少有人引咎辞职,也很难让人责令辞职。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形:引咎辞职条款在执行之际被上下其手,最终扭曲成一种整人的权术,激化官场内部的派系倾轧,非到问责的逻辑在被推演到“人人有责”的极端并且反过来变成“人人不负责”的那一刻,谁也不肯善罢甘休。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公务员法第82条第三款和第四款都势必流于形式。
为了避免引咎辞职条款在公务员法施行过程中逐步蜕变成一纸空文,立法机关还有必要更上层楼,引进公务员弹劾制,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体系,并且进一步健全和改善对政府的实体性民主控制,其中特别重要的因素有两项,即宪法已经明文规定的代议机构的监督权和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如果没有这些配套要件和制度性保障,引咎辞职条款就很难有效地发挥作为激励装置的功能。-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本刊法学顾问
背景
“引咎辞职”入法
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实施。这部针对公务员的立法,涉及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职务职级、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位聘任、职务升降、奖励、纪律与处分、工资保险福利、培训、交流、回避、退休、申诉控告等内容。
《公务员法》第82条有关“引咎辞职”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这部法律的一大亮点。该条第三款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第四款则进一步规定:“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是国外常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常规做法。一般而言,“引咎辞职”有两个基本判断标准:一是非直接责任;二是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的自愿。这种官员退出机制不同于强制性组织纪律和法律处分,是公务员在其行为尚不够纪律法律处分、又必须退出公务员队伍的状态下,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
“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同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观念一脉相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拨乱反正,很多受“文革”冲击的老干部官复原职,但也出现了部门副职较多的现象。比如当时的冶金工业部,有一个正部长,26个副部长。淘汰机制缺乏,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状态普遍存在。除了个别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官员退出官场几乎鲜见。退出机制不畅,导致行政队伍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
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其中第四十条规定“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个人申请辞职和责令辞职”,从而开辟了官员退出的新机制。
此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机构改革,仅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
“引咎辞职”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事管理制度中,源于200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其第七条指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
2002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3年SARS爆发期间的高官问责,使得“引咎辞职”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此后一年间,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县元宵节踩踏事件以及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一系列事件都带来官员的“引咎辞职”。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并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
就在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前夕,2005年12月2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国务院免去其局长职务。这一事件,从某种意义上为《公务员法》的实施,尤其是引咎辞职条款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
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引咎辞职”真正纳入了法律制度,可谓意义重大。不过,目前《公务员法》在引咎辞职条款方面显然还停留在原则性规定方面。究竟什么样的情形、什么级别的官员、依照什么程序提出引咎辞职,都没有明确解释。中国的引咎辞职制度显然还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