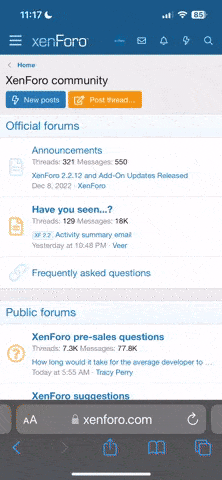新华网视频新闻: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4-05/11...ent_1462573.htm
是什么让余振东看到中国警察泪流满面?是什么让余振东选择在中国接受审判?为什么余振东涉案金额4.8亿美元却最多只可能服刑12年?[新闻会客厅]为你揭开疑惑。
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有很多经济犯罪的嫌疑人在东窗事发之后他跑到了国外,一段时间以来被我们认为好像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但是最近事情有了变化,这其中一位重头人物前不久被押送回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
白岩松:好,今天请进我们会客厅的就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分管境外缉捕工作的副局长高峰,欢迎您。
高峰:你好。
白岩松:第二位是收集国内犯罪证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的副主任陈东。欢迎你。他刚一下飞机您就去见到了他第一面,当时他的神态是什么样的?
高峰:他的神态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态,而且好像还有一种是回家的一种感觉。
白岩松:有什么交流吗?
高峰:有,在飞机上面,我跟他简短地交流了三五分钟,主要是告诉他回来以后他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将去哪儿,当天晚上还可能点什么。
白岩松:高局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以为说像他回来的时候应该是你们去美国把他给押送回来,结果大家看到是美国方面把他给押送回来,为什么是这样的选择和决定?
高峰:应该说这个案件能够办到这个程度,余振东被成功地遣返回国,是中美、中加、中国内地和香港警方互相之间密切协同,充分体现了合作精神的这么一个案件,也是中国和美国签署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以来,中方向美方提出请求的第一个案件。那么在长达两年半的多国警方的协同办案过程中间,美国的有关执法部门确实也体现了非常积极的协作精神。
白岩松:本来我们要提出要去美国押解,美方他们出于一种积极合作的考虑,他们主动提出来,并且承担相应的费用,由他们承担费用,遣送回国。
白岩松:这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高峰:对,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
白岩松:两年半的时间,高局,我们把时间往回推,在两年半前,刚你开始接到这件事的时候,你是否考虑过它的难度,因为毕竟以前大家知道,像类似的成功回来的先例并不多,当时您对这个难度是怎么判断的?
高峰:我曾经跟别的媒体介绍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我分管境外缉捕工作以来,感受到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首先他们这三个银行行长,也就是本案的三个主犯,他们作案时间长达十年,而且整个犯罪事实、犯罪过程不光涉及到中国内地,还涉及到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整个犯罪事实非常复杂,犯罪的面也是非常大,再加上他们逃亡的这些国家和我们之间又没有引渡协议,也没有遣返协议,以往的个案合作有过,但是出于那样、这样的原因,有些也不是很成功,所以说基于这些因素,我感觉到确实任务很重,压力也很大。
高峰:一开始对我们不太相信,没想到能把他抓回来,所以一开始他老逼我,到了后来抓回来……
白岩松:人家着急,可以理解。
高峰:现在我是很轻松,人回来了,就看你们的了。
白岩松:当时人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查到了很多东西,人不在我这儿,我有什么办法?
高峰:余振东的遣返回国,应该是专案组全体同志,我们全体战友的共同努力,也包括了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更取决于各国警方之间的协同作战。
白岩松:我们回到事实本身,高局,当跟美国最初开始交流的时候,他们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高峰:他们很积极,因为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决定签署了中美联合执法的联合的一个声明,就是加强执法合作,在这之后,中国和美国就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协定》,当然这个协定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的,它并不涉及到人员的遣返,它只涉及到一个调查取证,互相之间互通犯罪的情报,这样一个执法层面。当时根据这个管道、这个渠道,我们向美方提出正式的执法请求以后,美方是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因为他们也想把这个案件办成中美执法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白岩松:他给你的比较积极的行动回应是什么?
高峰:当然了,他向我们要证据,他向我们提了很多的问题,这样一提问题,说明他们很认真,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案子上面,美方确确实实,无论是从态度和从具体行动,他们从一开始都表示出了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势。
白岩松:陈主任涉及到证据了,你们在国内要针对他的三任,就是十年期间几个行长联手来做了,最后做出一个现在大家知道的值已经是4.8亿多美金的概念了。
白岩松:从你们证据的获得的角度来说,你们当时在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陈东:我们这一块做取证工作,始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现有境内的,作为我们的职能管辖部门、检察机关对他们所涉嫌的职务犯罪问题,所能取得的证据问题,所能追究的责任人,我们在有条不紊地按照方案一直在进行着。涉及到境外的这一块,他们把公款转移美国,通过洗钱手段,涉及到这一块的又是一方面的取证工作,这一块的工作就是我们和高局长经常保持沟通,链条上需要哪些部分,我们在境内积极地配合。另外一块就是广东开平当地有关人员的责任问题,银行本身资金的现状问题,当然这也集合了大量的审计工作来做,我们是这两块工作在同时进行。
高峰:这个过程是必然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在探索多边和双边执法合作模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大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彼此消除误解,来互相理解,互相了解对方的法律制度,因为在这个案件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对称,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刚才说了,每个办案部门的办案模式也不同,我们的取证规格也不同,当然就犯罪事实而言,就是说每个人吃饭的口味都不同,但是我必须要做出一盘来大家都喜欢吃的菜,这就是证据,就是说中国可以用,在香港也可以用,在美国也可以用,在加拿大也可以用。如何我们这些食客们或者说厨师们坐下来,来研究研究,你是喜欢吃甜的,他是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酸的,如何结合大家的口味,做出一盘色香味俱全,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盘好菜。
白岩松:高局,后来注意到,当要针对这件事要进行处理的时候,你们召开了一个三国四方会议,这三国指的是中国、美国、加拿大,四方加上一个香港,这三国四方是不是正好跟他们这个案件有关的这四个方面?
高峰: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三国四方会议结束的时候达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共识?
高峰:大家经过四五天的会议,也包括在这个会议之间也进行了调查取证,首先明确了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符合各国的利益和各个地区的利益,这么一个犯罪团伙,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实施了那么严重的犯罪,不论是对中国,对美国,对加拿大,对香港的警方来说,他都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而且打击这些犯罪,有利于各国的利益,这是我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三国四方会议是在前期我带领的公安部代表团四五次赴美,包括去香港和加拿大。就是说对整个案件,根据这个案件的特点,我们设立了一个证据模型,要证实这些犯罪分子,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犯有严重的犯罪行为,你就要复原犯罪过程,包括要复原他们当时的犯罪思维。
白岩松:这我要插一句话,从一个犯罪的角度来说,你要复原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复原它的过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型?
高峰:首先,要了解一个犯罪过程,就必须要把它各个行为,包括它的思维,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要把他想干什么事,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你要搞明白,所以说第一步要复原犯罪思维,你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如果要干这件事儿,你将怎么干。把他的思维活动复原了以后,再去复原他的行为过程,这也就是说按照认识论的规律特点。
白岩松:我思故我行,把这个思和行要结合起来。
高峰:行了以后第三步,要找到证据,如何来印证,来固定这种思维痕迹和行为痕迹。
白岩松:你们的判断是对的。
高峰:对,然后这个证据因为他们的案子,他们整个行为涉及的很多很多,就有一个不同的证据要素的组合,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原因,哪些是结果。哪些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它是主要的,在另外一个特定时期,又是一个次要的,互相之间的犯罪关联性,根据这种关联性,你要设立证据模型,这个证据模型并不是现有的证据,按照模型的设立,再去寻找证据。这当然了,最后能不能证明还要看证据本身,这个证据模型就是引导我们取证工作的一个体系。
白岩松:主要靠语言表达还是文本,还是在演示?
高峰:我在美国跟美国的联邦执法机构的特工们,我们一块讨论这个证据模型的时候,我在黑板上面写了将近两个小时,互相讨论。
白岩松:那得写多少黑板?
高峰:那就擦吧,写了擦,擦了写吧。
白岩松:但是大家是比较认同的最后。
高峰:大家比较忍痛,比较认同这个证据模型,因为警方的工作大家都是相通的。
白岩松:这意味着什么?对整个这个案件的向后走意味着什么?
高峰: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一开始我们提出执法请求的时候,美方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之后几次去美国,就是寻找一个我们如何开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就花费在我们彼此之间消除误解、消除隔阂,这只是一个,你了解了,我了解了,磨合过程,在磨合之后,就是大家可以终于联起手来做这件案件的时候,就考虑该怎么做,这个怎么做,也就是做这盘菜的时候,证据模型的确立,大家思想认识统一了,思路统一了,才具备了下面的工作。
白岩松:一开始每美方展现出来的是比较积极的态度,同时也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向你们询问证据等等方面,接下来是否有了更进一步它的举措,因为毕竟人跑到那儿去了,钱挪到那儿去了。
高峰:他本身来参加三国四方会议,加拿大、香港、美国执法部门,这就是一个很积极的进一步的举动,更何况在三国四方会议之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抓获了余振东,当然这个也是在我们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并且美方经过核实调查之后,将余振东缉捕到案,这些都是很积极的。
白岩松:钱呢?
高峰:钱是冻结了他转移到旧金山的355万美元,而且也一分钱不少返还给了中方。
白岩松:从这两点来说,一个是抓到了余振东,第二个是冻结了他的这些钱,是否跟以前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合作之中?
高峰:对,可以来说是比较异乎寻常的。
白岩松:异乎寻常?
高峰:异乎寻常,对。
白岩松:因为一般他可能不会采取这样的举动。
高峰:一般按照国际上面,对犯罪资产的追缴来说有个分享,因为各国执法部门为了侦查办案都要付出一定的执法成本,付出成本的时候,本国政府,本国的执法部门在本国执法,那当然是由国家税收、政府税收来支付,外国的执法部门为另外一个国家的案件来做出努力,做出付出,他当然需要在你得到的收益里面有一个回报,但在这个案件中间,美方没有提出分享的要求,他可以提出,但是他没有提出。
白岩松:陈主任,你们跟高局的合作方式是什么样?
陈东:应该说合作还是很密切的,在模型出台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沟通,然后出台之后,大家达成共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有针对性地,并且制定一些很具体的取证的方案,来把取证工作往前推入。
白岩松:你们有多少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主要是由高检负责的,还是依托开平当地,还是广东的?
陈东:要从大的案件来说,应该是相关的中央有十个部门吧参加这个案件的办理,办理的机制,刚才说了,有一个联席会,就检察这一块,我们所负责这一块的工作,包括开平当地的调查工作,当时我们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因事设人,因需要设人,人有时候可能多达五十、六十,有时候可能少到十个、五个,根据案件的切实发展需要来这样设定这个人员的配置。当然高局那边估计他们也有。
白岩松:事情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似乎可能比您想象得乐观,可能比很多人想象都乐观是吧?
高峰:从大的方面来讲,境外缉捕工作是为整个案件查办工作服务,但是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境内取证工作为境外缉捕工作服务,为填充这个证据模型。当理顺了一些工作关系之后,是不是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发展比较乐观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将这些犯罪分子缉拿归案。
白岩松:结果是第一位的。当你到美国的时候见余振东,然后讯问他的时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体,据您的观察?
高峰: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去美国是美国联邦执法机构邀请我去的,他就说,你可以和余振东谈一谈,看看他有什么想法,我去了以后,谈话的地点是安排在联邦检察官的图书馆搞了一个休息室,为什么这么安排呢?我知道余振东见了我肯定会非常紧张,会有一种惧怕心理,特意安排这么一个场景,就能够消除这种紧张的气氛。
白岩松:虽然是检察院,虽然是联邦的检察院,但是又是在图书馆相对来说气氛比较平和一点的地方。
高峰:对。他进来以后,我也很客气,让他坐下来,因为不论他犯了什么罪,从人格上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询问他一些生活的境况,我也知道,他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日子不太好过,饮食不习惯,再说了,人当失去自由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滋味,这谁都可以想象,同时那些其他人种的囚犯们还经常对他实施一些非礼,甚至一些打骂、歧视。更主要的一点是他对今后前途的渺茫和绝望,一种绝望心理,我找他谈,就是主要是当时第一次谈话就了解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他对今后到底是一种什么选择,在了解了他以后才能对症下药地做些工作。
白岩松:那结论呢?他当时在想什么,他想得到什么?
高峰:他当时对于他犯罪这一点,他是承认的,在这一点来说,余振东在认罪的问题上面还是坦诚的,当时他就是在考虑,留在美国好呢还是回去好呢?留在美国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回去以后又有什么好处,他不太了解,按照他的罪行和中美之间的有关的法律规定,他在美国服完刑以后,如果判定有罪服完刑以后,中国政府、中国公安部还在继续谋求将他遣返回中国,而且这作为和美国执法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回来以后,他还将面临中国法律的审判。在这件事情上不像有些法学界说的一事不二理,好像因为同一个行为在美国受到惩罚,回到中国就不应该再受到惩罚,这是两回事,他在中国的犯罪行为和在美国的犯罪行为是截然不同的犯罪行为。
白岩松: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又流露出某种他的心理的活动,他左右为难吗?我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去,有没有开始有一种倾向性或者怎么样,据你的观察?
高峰:据我的观察,他还是倾向于,就是你给他讲清楚这些利害关系之后,他还是倾向于回来,但是回来他有很多顾虑,你不要看他在中国银行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担任过领导职务,但事实上对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对公检法部门也不是很了解,他不知道回来以后会怎么样,也有针对性地给他做一些思想工作。
白岩松:从某种角度,您也是他的咨询者了。
高峰: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你对他主要要说的是什么?
高峰:我主要对他说的是,首先一个非常严肃地,也很严正地向他指明,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在中国犯有罪行,不光在中国犯有罪行,而且还在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犯有罪行,他是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这一点在我向他指出以后,他明白这一点。然后第二,对他来说,回国接受审判,是他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要将他缉捕归案,不仅仅是开平案件整案查处工作的需要,也是震慑其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那些外逃的,他以为逃到国外、境外就万事大吉了,就进入一个避风港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白岩松:很重要的是他心里一定会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不会吧,但是你跟他讯问的时候,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告诉他,你要告别侥幸心理。
高峰:这个策略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叫策略,事实是这样的,当我们收集不到证据的时候,那些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他当然是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不要说逃出去,就在国内他也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一旦当执法部门,特别是多边的和双边的执法部门互相合作,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指控的时候,他就是留在美国服刑,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处。接受美国法律的审判也是接受法律的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白岩松: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见面,第二次见面跟第一次做讯问的时候比较起来又前进了哪一块?
高峰:程度上面,更加进一步地打消了他的顾虑,更加进一步地坚定了他回国的意愿。同时,也跟美国的有关执法部门更加一致地协调了我们的行动。
白岩松:是否第二次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拥有的证据也比第一次要更丰富?
高峰:应该来讲事实上是这样。证据更充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毕竟有文化的差异,余振东在同美国的有关执法部门的人员在交流中间,他感到心里没有底。虽然他是个犯罪嫌疑人,中国的警方去了以后,在文化上面沟通比较容易,而且他感觉到,给我一种感觉,他见到我们好像还有一种见到家里人的一种感觉似的。
白岩松:就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心态。
高峰:对,又怕,又感觉到又很亲近,在整个案子办完以后,我到飞机上面见到余振东的时候,他似乎已经跟我建立起了某种新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跟我个人建立起了新的关系,是跟整个我们政府,跟国家的法律,他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这个案件上面,跟余振东的交道主要是体现了我们中国法律的尊严和中国政府的坦诚。
白岩松:在这两次讯问的过程中,余振东在你面前有没有流露出某种情感的表达?
高峰:情感的表达非常强烈,每次谈都哭。
白岩松:谈到什么地方会哭?
高峰:谈到他今后的出路,谈到他家人今后的,就是说他所实施的行为给他的家庭,给他本人所带来的应该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想流下的是一种悔恨和后悔的眼泪,很激动,确实很激动。
白岩松: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微妙的心态,怕你们,甚至躲你们,但是见着的时候毕竟又是讲同样母语的,这种心态在整个这两次谈话过程是不是都有流露的机会?
高峰:第一次是惧怕多于亲近,顾虑多于希望。第二次见面以后,可以说是在逐步逐步打消他的顾虑,他也愿意跟我们谈一些事情。在沟通和交流上面没什么障碍。
白岩松:最后的比较具有结局性的谈话是什么?
高峰:结局性的谈话就是我跟他就像咱们这样面对面坐着,我跟他讲,老余,我不远万里来到美国。
白岩松:真是。
高峰:我是第二次来见你,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来过不止这两次,从法律,从对你个人的考虑,你都是要签署认罪求情,对你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过了这村你就没那店,这是该到你选择的时候了,你已经走错了一步,你不能再走错一步,他当时表示,我会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白岩松:认罪求情的说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他的身上我们会拥有一个陌生的词,叫认罪求情?
高峰:这个词是一个法律术语,法律概念,在有些中文译名上面也有它译成控辩交易的,但是我认为用认罪求情更为确切,更为妥当。他的前提就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被告人可以针对检察机关、检察官提出的指控,他可以认罪,在作为认罪的一部分,他可以向检察机关和向法庭提出来减轻刑法的一个要求。经过双方协商,并且经过法庭的批准,可以确立这一点,类似于我们国家刑事政策里面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一个刑事政策。如果说你不认罪,警方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犯有罪行,经过法庭审判以后,有可能按照最高刑来判处刑法,是这么一个事情。具体到这个案件,认罪求情对余振东来说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有大量的证据,美方也有大量的证据,加拿大也有大量的证据,香港也有,可以这么说,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向美国提出了要把他遣返的要求,加拿大、香港也同时提出了要求遣返的请求。对余振东来说,如果说他不承认这个罪行,他不主动要求回来,他面临的将是中国的法律审判,加拿大的法律审判,美国的法律审判和香港的法律审判。
白岩松:余振东是否在第一次跟您见的时候,去问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点?
高峰:当然他不是太懂这些事,好在我们在跟他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律师,他请了一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比较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在场,刑事辩护律师对这些他很清楚,但是有一个,他对中国的法律不太清楚,向我提了很多有关于我们法律方面的比较肤浅,这个也难怪,甚至有些很可笑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对整个余振东的处境和今后的出路他是很清楚的。
白岩松:他在被抓之前他在美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高峰: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在美国一共搬过六次家,可以这么说吧,惊弓之鸟,疲于奔命,当然他搬家的因素并不完全是为了躲避,也有一种生活上的考虑。
白岩松:质量的提高。
高峰:不,就是子女就学方面。
白岩松:我以为是换了大房子了。
高峰:他要选择华人社区,大房子他早就买了,买了豪宅了,我都实地去看过。
白岩松:走之前就买了吗还是到了……
高峰:走之前就买了,他们在跑逃跑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之间他们预想就已经想到了败露的结局,后路,他们都准备好了,这也就是这些经济犯罪逃犯的共有的伎俩,他们在实施犯罪之前或者在实施犯罪之中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逃避法律惩处的准备。但是事实证明,这也是徒劳的。
白岩松:狡兔三窟,他在美国准备了几个地方?
高峰:在洛杉矶、旧金山,包括加拿大的温哥华,他们都有原来都购置过房产。你要是说他在逃跑之前,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是他们常去之地,他们这些人在那儿一掷几十万金,甚至几百万金,一个晚上就可以输掉几百万美金,那都是国家的资产、社会的财富、人民的血汗。
白岩松:他在美国是否有犯罪?
高峰:当然了,当然有犯罪了,他实施的这些行为同时也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当然也是犯罪,包括利用虚假的身份进入美国,而且他犯的罪还不止一个罪,是多项罪名,而且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是叫严重的重罪。
白岩松:既然有了认罪求情这个条款,他可能不会失去生命,会受到一定的从轻的处理?
高峰:这个他明白,这个应该他是很清楚的,其实对这些犯罪嫌疑人,把他们缉捕归案,而做出一定的,对他们做出一定的承诺,我觉得不是件坏事,也不是说一般公众理解,好像这些犯罪分子抓获归案以后十恶不赦,枪毙十个来回都够了,为什么对他们好像处理那么轻。这个是一种比较朴素的感情表达,对我们执法部门来说,重要的就是将这些人抓获归案以后有助于查清全案,来消除一些隐患,来今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同时也是对那些已经在逃和将要逃跑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是一种有力的震慑,对他们来说,就是十年、二十年、十五年惩罚都是一样,他们都将失去自由。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政策、刑事政策,当时那些战犯他们手里沾满了多少人民的鲜血,但是经过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
白岩松:这里也有一个利弊之选的问题。
高峰:对,确实是这样。
白岩松:大家可能也会说了,听到您的解释,就关于认罪求情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转不过来弯,但是转不过来弯可能也会想,比如我们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可能也是在利弊之中选择了利大于弊,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利大于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高峰:可以这么说,如果余振东他不签署这个认罪求情书,可以设想一下,他有可能在美国接受美国法庭的审判,
当然他会聘请律师来为自己做各种的辩解。辩解之后,如果罪名成立,他依旧要在美国监狱里面服刑,在美国监狱服刑的同时,我们当然还会继续要求美国将其遣返到中国来,时间上面就会拉得很大。时间拉得很大,不利于国内案件的查处,同时也不利于震慑犯罪分子。
白岩松:他们都得拖着。
高峰:都得拖着,也不利于查处震慑其他犯罪分子。针对余振东这个人而言,判他多少年我认为并不是太重要,而且他归案,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这本身就是我们中方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司法主权的体现,同时对其他犯罪分子也是一种震慑。
白岩松:有点像一场战争要开始的时候,发出的信号枪不一定一定要击毙一个敌人,但是可能对未来的战役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高峰:对,没错。或者说是这是打的一场中国对外缉捕工作的一个形象仗,是个示范仗。当然了,今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灵活务实的缉捕方式,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缉捕方式,所以说公众千万不能把它理解为今后执法合作都是按这个模式来进行。
白岩松:他顶多被判12年,但是一联想到,不管那个数据是不是像高局说的那样,还没有最后的,因为这是一个要最后的证据来说话的,是不是个证据,但是起码是个天文数字,不换成美元都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是美元,才裁判12年,是不是太亏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东:这个案子特别不同一般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中美司法一次合作的一个例子,十二年是个承诺,这个因素我觉得也是应该考虑的,但是最后的审理肯定是由法庭做出来的,我觉得到底他最后要判多少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法院来依法做出一个裁定、一个裁决。
白岩松: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陈东:我觉得这个问题,像刚才高局已经提到了,所谓的不理解也是一种出于一个很朴素的心情不理解,一种义愤心理。
白岩松:而且容易拿资金的数额来进行直接的对换?认为这个就是您刚才说,枪毙十个来回都够了,都富余了。
陈东:但是至于说最后的处理情况,应该说还不是我们侦查机关现在所能够决定了的。
白岩松:对,但我想这个问题您一定思考过,包括可能也有其他的人向您提过这样的问题,从他的案例来看,我挪用了这么多的公款,如果我没有跑,可能我死定了,但是我跑了,跑了之后,我回来了,但是顶多判我个十二年,那我还是得跑啊。
高峰:那就可以试一试,那些有这种侥幸心理的人可以去试一试,至于说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还是去尝一尝那种生不如死的备受心理煎熬的滋味,因为我们都无从去体会这种心情,也不是说这种行为,有这么一个模式在,就会激发很多人去作案,去犯罪,然后犯了罪以后跑出去,跑出去以后,回来以后可能就不杀头了,他有没有,如果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或者说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亲属,还有一点点的责任和留恋的话,他会考虑到,无论他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只要是犯罪行为,他本人死不死是另外一回事儿,会不会判死刑是另外一回事儿,而对他的家人,对一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白岩松:其实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高局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蛮有意思,说当时他跟您开玩笑的说,我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余振东回来了,现在你们面临的工作是什么?
陈东: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在4月16号已经正式开始,就是余振东下飞机,最后就开始,24小时之内的提审我们就进行。现在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有三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针对余振东本人的涉嫌犯罪问题,加强审讯,在这个工作的同时,第二项工作,加强外围的一些调查,就是根据他供述,根据我们以前掌握的情况,尽快就余振东所涉嫌的犯罪问题,尽快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脉络能够出来,这是第二块。第三个,在我们以前侦查过程当中,在余振东没有到案之前,有许许多多涉及到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若明若暗的,大多应该属于线上的问题,他来之后,我们很快地根据工作的方案,根据分工,尽快把这些问题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一个认识,当务之急就是要做这三个工作。广东检察机关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相对得力人员组成的调查组,有做具体的审讯工作的,有做外围调查的,还有做一些计策性补充材料的,这些工作现在有条不紊地正在紧张技术进行。
白岩松:余振东回来以后配合你们的审讯工作吗?
陈东:余振东本人的态度应该说还很好。
白岩松:有没有交代出新的事实,你们所不掌握的?
陈东:现在还正在提审当中,因为这仅仅是几天的时间。
白岩松:估计从现在的收集证据,包括提审,一直到最后的宣判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从司法程序上来看?
陈东:根据法律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应该说他如果从16号……
高峰:从被拘留到最后一审判决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
白岩松:八个多月的时间。
陈东:这是在一个罪名的情况下。
白岩松:高局,回到您这儿,现在可能很多人也在想,他回来了,可是老婆孩子还在国外是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高峰:这个不是说没有办法,首先看他的老婆孩子有没有涉嫌犯罪,要涉嫌犯罪了,那当然是一回事,没有涉嫌犯罪,你当然也不能让他回来。
白岩松:对,老百姓可能下意识地就会想,包括我们下意识就会想,他没回来,可能在美国用的钱就是曾经挪走的某些公款,只是你无法证明是挪用的公款而已。
高峰:这个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工作,包括美国执法部门的配合,该追的我们已经基本上都追了,除去他在赌场里面输掉的我们没法再追。他的老婆和子女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据我们了解,基本上是他的亲属,他亲友资助的,而他的亲友是在他翻案之前,或者说在犯罪之前很早就去了美国谋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白岩松:追回来的钱占的比例有多少?大致。
高峰:大致的比例,从我们境内追缴,全案三分之一左右。
陈东:全案三分之一多。
白岩松:还有可能增加吗?
高峰:有可能,那当然了,经过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增加的。
白岩松:接着我们要关心另外两个人,这个案件大家知道,从主犯的角度还有两个,也是开平银行的前行长等等,他们现在也外面,下一步工作他们是我们重要的目标吗?
高峰:我这么一说的话,他们就该紧张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都很紧张,余振东回来了,只是这个案件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工作。我相信余振东不会是最后一个。
白岩松:但是他是21世纪的第一个。
高峰:对,从美国抓回的第一个。
白岩松:所以就涉及到您的工作,你看你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分管境外缉捕工作的领导,大家也关心这些年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也比较多,有各种各样的数字,虽然从你们一再说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我们在外的经济犯罪的嫌疑人毕竟是很多的,有了余振东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头,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个什么样的期待?
高峰:可以这么说吧,今天来到会客厅,也是我们ECRD,就是国防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英文简称,第一次浮出水面,走出幕后,走向台前。因为以往境外缉捕工作,我们是只做不说,当然了刑侦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公安部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在提高我们公安部工作透明度,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和媒体的沟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从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共缉捕归案230多名逃犯,余振东的缉捕归案可以说有这么几个意义。首先,对检察机关查清全案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像这类的涉及到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的个案合作,在境外缉捕工作历史上面还是首次,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缉捕工作的概念了,是一个联合办案、联合执法的概念。所以在把办案模式,在多边和双边的国际执法模式上面,我们探索了一个执法合作,我们探索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和经验。第三,在跟美国这样的以往没有缉捕归国先例的国家达成了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我相信对于我们今后更加积极、全面、广泛地开展境外的国际执法合作和缉捕工作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同时,我也相信,跟美国的执法合作不会仅仅停留在余振东这个个案上。
白岩松:你看今天您坐在会客厅里是第一次浮出水面,我想第一次浮出水面肯定还有其它的一些,比如说对于很多逃到外面的,和没有逃,但是有可能心理活动,假如我成了犯罪嫌疑人我也会逃,这个余振东案又向他们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高峰:法律永远是所有犯罪嫌疑者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也许他们可能会得逞于一时,但得逞不了一世。从他们实施犯罪的那一天开始,他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就是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机不到,时机一到,立刻就报。
白岩松:陈主任,在您这么长的时间做关于余振东的收集等等的时候,您想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你提醒这个社会该反省,反思的又是什么?
陈东: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件,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作为一个办案人员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只要接手这个案件,就是案件涉及的,涉案款项之巨,涉及的人数之多,以及作案的时间之长,应该说还是很令人震惊的,这是首先我们办案人员都有这样的感觉。同时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在内部的监管方面,特别在银行系统也有很多的值得反思,或者是有启发的地方,比如它长达十年作案,反复地检查都没检查出来,就是监管这一个环节我们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地加强,设立一些有力的机制。当然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了解到,中国中行针对这个案子他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出台了一些政策,应该说对类似的这种事情的发生,现在来看他们认为是正在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高峰:在这方面我也有个体会,当然这个事情本身暴露出我们管理上面很多的漏洞,这个漏洞就具体个案上来说你可以说出很多来,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说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一种制度设计,我们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以往可能过多地放在了希望好人不要犯错误,希望好人不要干坏事这么一种设计理念和基础之上,恐怕今后要根据这种犯罪比较突出的情况,我们过多地要把我们的设计思想要建立在坏人干不了坏事,或者是假定你是坏人,也干不了太大的坏事,要放在这么一种设计基础上面,整个一个制度设计就比较合理、比较严密。
白岩松:个人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把精力放了让人不想干坏事上,今后可能是让人不能和不敢干坏事上。
高峰:对。 (文字来源: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