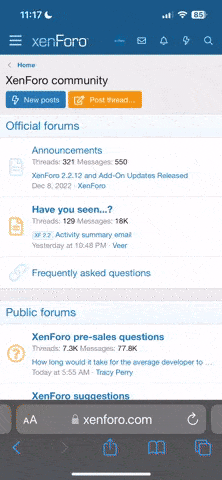Todo
初中二年级
- 注册
- 2005-08-26
- 帖子
- 470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1
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
张修林
一、 第三代诗歌及“第四代诗歌”(注1)的界定
把继朦胧诗之后,发端于一九八六年,以非非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先锋诗歌创作形态称为“第三代”,这一概念与界定已经进入中国文学史。给中国诗坛带来前所未有巨大冲击的“第三代”诗歌革命运动,以其破坏性、取消价值中心和反对传统诗歌的语言形态,为先锋诗歌的创作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机遇和影响,成为了中国先锋诗歌与世界接轨的发展基石。然而,由于社会境遇及“第三代”内部自身的原因,这场运动及其轰动效应逐渐微弱下去。“破坏破坏再破坏”的“第三代”,尽管非非主义史无前例地建造了一个“中国式乌托帮”的“前文化语言---反价值”的独立艺术语言理论系统(注2),但自身的理论严重脱离艺术现实环境以及建设意义的匮乏而未能解决先锋诗歌的语言社会能动性问题。诗歌是一种关于社会与文化命题的艺术,它必须具有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功能。对于诗歌,仅仅说出是不够的,说出必须就是行动。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察第三代诗歌,就会发现,它的语言层次更多的是文化/文明上的喧哗与骚动,而不是其它什么。
在第三代沉寂之后(注3),一些批评家(注4)认为先锋诗歌创作转入空白状态。实质是,这是一种文本批评视角的空白。从这时开始,一批更年轻的诗人象一支执行神圣使命的夜行军,静悄悄地民间报刊的形式占据着先锋诗歌的阵地。他们从第三代尤其是非非主义中获取启示与动力,寻找先锋诗歌更富于感性的、更切入人类生命与存在文明的表现手段。他们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现实斗争的精神表征。他们行进得缓慢,没有第三代那样的广告性、轰动性效应,但实在地接近着诗歌。他们或许并不完美,但他们在发展。这一批年轻诗人历史性地成为了“第四代”的主体力量。另外,“第四代”的范畴也包括曾经追随于第三代,但在第三代之后在理论与创作上严格区别于第三代,且其创作形态与上述第四代主体融为一体的先锋诗人。
二、 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
毫无疑问,在研究与阐述第四代的诗歌形态时,“第三代”是作为一个更具有比较与顺承性的参考传统。
关于第三代的语言理论与语言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非非主义的前语言(作为宇宙自身的体现,是一种“无语义语言”)和语言的价值变构 (注5);
韩东的“诗歌到语言为止”的主张以及“他们”的口语创作形态(注6);
整体主义的所谓古典式语言态度。
第三代中的非非主义的语言价值变构理论具有一定的文化现实意义,企图通过语言的价值变构达到文化的拨乱反正,但代表着第三代的最高水准的这种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发现认识到语言就是历史与现实本身。
所谓“语言就是现实”,是指语言与现实同构、同一,语言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现实。
这种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现实由原语言/原现实与再语言/再现实组成。自然本身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原语言/原现实,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再语言/再现实。艺术语言/艺术现实是一种本真的再语言/再现实。变化包括自然变化和人类参与的动性变化,亦即原变化与再变化,艺术变化是一种人性的本真变化,是所有变化中最富灵性、最具灵动的变化。
第四代诗人的这种区别于第三代的语言态度,无疑在创作中更为有效地体现了语言的现实倾向,这使第四代诗人在第三代之后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形态成为可能。
1、 取消诗歌语言的非现实性
“语言就是现实”这一理论对于诗歌而言,首要任务就是
要取消诗歌语言的非现实性,让诗歌成为一种与非现实性语言斗争的手段,让诗歌在取消非现实中凹现一种全新本真现实语言,而这种全新现实语言不仅作为一种诗歌现实革命行为,而且是作为一种更为彻底的人性反拨现实。
A、取消神话写作,重新规划人的能指
神话写作使人的臆造在伪现实中虚脱化、消解了人的生存现实、抹杀了文明的本质人性。神话的臆想使人的能指虚浮、淡化,人的能指在神话中成为非人,人未指向人。第四代诗歌取消非现实的手段之一就是取消神话写作,在“人话”写作中实现人的本体能指。反映神性思维与活动的描写叫做神话,第四代诗人的“人话”则是反映人性思维与活动的描写。人话作为人本体书写,其目的就是企图把人的能指从神话中解放出来。
a、性现实的诗歌
在第四代诗人看来,性是神话的组成部分,但首先是人话的组成部分。性现实是诗歌现实的有效的、本质人性的组成部分。所谓性现实,是指人本体的性意识、性思维、性行动的社会现实客观存在。伊沙在《和日本女人亲热》(注7)、《走向生活》(注8)、《春天的事件》(注9)等大量作品中,把人的性现实作为表现的唯一对象和可能。杨春光在《圆的和方的》(注10)、《榕榕小妹的消息》(注11)等不少作品中,纯粹人化的性揭示不仅消解了神话的性能指,而且消解了一些权威性词语表征的非现实政治性。张修林的《上学去》(注12)等作品,则是以人的性形态和性的本体潜意识瓦解巨大、深层的伪意识形态现实。狼人的《高速公路》通过性意识的无所谓状态表现科学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的无所谓现实。曹光辉《玩的爱情》(注13)表现了人本体的非神话性的由肉体而爱情的过程。另外,第四代的一些女诗人,如周凤鸣、李轻松、贾薇、于小尘等,以女性的角度表现了性的真实现实。
b、日常生活经验:个体性写作
取消神话的可能性之一是,随着神性的瓦解,个人成为自己的最高主宰,人的能指倾向个人性,由此引起个体性写作:发掘个人性的独特能指,表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形态及经验。应当指出,这种个人性能指亦是人性能指的组成部分,尽管它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这种写作状态,仍是对神话和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物欲膨胀的有效校正与反击。上述所列举的杨春光的一些“性意识作品”也可归入此类,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性的能指。另外,杨春光的《人在边缘》(注14)表现了极端个体的“边缘“体验,尽管杨春光这里不完全是处于日常生活范畴。伊沙的《关于春天命题的写作》(注15)基于对春天的个人细致感受反驳作为传统文明之一的古诗,而他的《教子有方》(注16)则是高度个人能指倾向的体现,至于《遥远的前世》(注17),伊沙企图通过对时空的重组在个体能指中达到消解所谓道德的目的。丁小村的《简单主义》则是在单调的人体能指中消解繁复的现实逻辑。夜林《我造的世界》(注19)通过个体能指的高度主宰企图达到诗歌对神话本质或神话的总象征体的消解。与第三代的所谓口语日常生活诗不同,第四代更大限度地抵达了对既有现实的本质性消解。于坚的日常生活创作,几乎更多只是停留在生活细节的真实描述,韩东则似乎想超越日常生活本身。但他提供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简单文化消解。可以说,第四代比第三代更进一步抵达了日常生活细节内部,并在其中大幅度地完成了消解的真实与超越。
c、反对神话与宗教的终极意义
神话往往外显一些虚无的所谓理想的化身,宗教仍然用一些不切合现实生存状态的所谓大同世界之类的教义蛊惑人心,人们对宗教和神话的神往,淡化与忽视了生存中刻不容缓的“硬问题”,企图承受不符合人性的灾难而等待所谓上帝的福音。第四代诗人认为,只有人本身、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的迫切改善是真实的,宗教与神话对现实斗争的严重消解,使人的本性呆滞、意志薄弱,越发恶劣了人的主体性状态。任何所谓上帝及宗教式幻想的终极意义,都必然阻碍社会进步。所以,第四代诗歌,表现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同这种环境的挑战。人永远处于这种挑战状态。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一次或几次挑战,挑战同步于无止境的人类进步中。而第三代诗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对生存的不满,对生存元素持一种本然的抵触。第四代是毫不保留地对生存宣战,对生存元素宣战,甚至对劣性的人性宣战。伊沙的《法西斯艺术》(注20)以反讽的形式批判专制的艺术制度,《星期天夜间的事件》(注21)深刻地揭露了“上帝意识”对人类的残害,《叛国者》(注22)则是对现实颠倒的反拨。余怒的《苦海》(注23)在具象中呈现对生存元素的始终介入中。张修林《零度的夏天》(注24)对不温不火的现实情绪及严峻的生存困境实现了宣战式的对比。邹赴晓《空虚的沙子》(注25)在回归的还原激情中反动了人的异化与价值逆差。周渔的《经验》(注26)作为对所谓存在的否定而实现未经的精神企图。第三代诗人有着深刻的对宗教神话的怀疑倾向,但其态度实质上更多只是情绪性的东西,而第四代诗人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而且大多是手段性的表现,而不是情绪性的表现。
B、取消语言的虚饰现实与暴力现实
作为现实的语言本体,它自足、充盈,表征着真实的、生成的现实结构。然而,语言现实存在着它自身的病态衍生物---伪语言现实。伪语言是一种虚饰现实与暴力现实的“现实操作形态”。一些政治手段、弱化人智的畸形人格,往往就表现出对语言的虚饰与暴力行为。艺术语言的任务就是反对语言的虚饰性与暴力性,复苏语言的真实现实结构功能。
a、 取消虚饰现实的诗歌
虚饰现实是对现实进行胡夸、曲解、对事实进行隐蔽的一种伪现实行为。虚饰现实有时利用伪逻辑作为手段构筑,貌似有理有据,实则胡搅蛮缠。在当代,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胡夸风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虚饰现实典型表现。虚饰现实历史性地存在于各种社会事实与艺术语言现实中。虚饰现实始自奴社会的诞生,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则是始自阶级的产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随着人类的内部分野---大多数人的主体客化---语言的现实错位开始产生,语言与本真现实统一、完全同一出现了空前的、持续而无期的裂解。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少数人组成的强力集团的伪善人性与自私的暴力人性相结合产生了历史上的伪逻辑系统。伪逻辑最初只是简单的借口、搪塞和表露性欺骗,而后在所谓文化/文明进步中发展成为了具有隐蔽性、系统性、理论性的伪逻辑系统。人类文明的发展实质就是承袭与发展伪逻辑系统的集团的覆灭与更替的历时性转换过程。艺术历史性地成为了伪逻辑系统的条理及实质诠释。艺术在发展,因为它的诠释性处在不断改善之中,但艺术并未真正发展,艺术总在这个系统中诠释。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不是改善这种艺术形态,而是实质性地改变这种艺术形态。第四代诗歌敏锐、高屋建瓴地发现并把握了这种巨大的混沌语言历史,并企图从这些复杂的文明遗骸中回复语言与现实同构、同一性,从而实质地改变人类的文明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第四代诗歌正在进行一场还未有结果的伟大的诗歌语言革命。张修林《历时的分析》(注27)描述性、持续性地表现这种历史逻辑与文明历时性的生成与转换。杨春光的《杀手》(注28)是以诗歌作为对这种文明形态的介入与清算手段。伊沙的《废品店》(注29)以对人化的铁的描述反映了在这种逻辑与文明中人本体自觉的、甚至是本然的反抗。步钊的《最先开放的花朵》(注30)粗放型地企图实现人性与生存现实的激情性逻辑对抗。千叶的《会有一阵白色的风吹起……》(注31)是对颓废文明的现象反击与揭露。达达的《在流放地》(注32)表面伪逻辑现实的庞大性与人性在其面前抗拒的艰难性。非非主义创始者周伦佑先生的反价值理论与第四代诗人的创作认知有一定的形似性和一致性,但显而易见的是,认知途径和根源不同,第四代诗人的认知来自对历史事实与生存状态的反思、研究与把握。更值得一谈的是,第三代的诗歌创作并未实现周伦佑先生的反价值手段,第三代诗人对待伪逻辑与虚饰现实的态度是含混的、不坚定而游移于伪逻辑表层结构的。第四代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已经对伪逻辑有了整体性的、要害性的认识,并已在其本质结构中开展了消解甚至企图重建的工作,尽管这种工作还显得非常不力。
b、 取消暴力现实的诗歌
暴力现实即是对本真现实施暴的行为。暴力现实的表现很多,范围很广。一般说来,暴力现实在各方面都体现为对本真人性的武力性、强制性扼杀。它与虚饰现实不同,虚饰现实更多的是利用欺骗、伪文化、伪逻辑等软鞭子实现愚民,或者作为团结一些独特人士,作为招兵买马、引起轰动与注视的手段,而暴力现实则是动用武力的机器直接运作或将其作为暴力现实的后盾。艺术的暴力现实体现为对艺术强加一套所谓制作指导方法,或者以暴力性质的力量作为后盾对不合乎所谓规则的艺术进行棒杀。暴力现实从各个方面对艺术进行渗透,并且,在从事所谓艺术的集团与个人之间,也同样惊心动魄地引发暴力现实行动,比如一些并未建立于学术角度的所谓艺术批评就属于此类。暴力现实只承认一种或一套规则的艺术。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专断的所谓前卫艺术家艺术理论家也扛上了暴力现实的工具。第四代诗人认为,中国从未出现过正常的争鸣习惯与形态,就是暴力现实存在的最直接体现,在中国,你难以见到学术角度的艺术批判文章。在这里面,艺术家们仍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传统的惰性让艺术家成为了精神不健全的人群。第四代诗人企图改变这样一种阻碍艺术进步的超常习惯性状态。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清除暴力现实中恢复诗歌的本真人性与本真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讲,第四代诗歌必定单不仅是诗歌的,人首先是精神的。诗歌的传统历来缺乏真正的、关键的与整体性反思的精神向度。我们可以看出,第三代诗人与第四代诗人的差距,在于第三代诗人的群体性社会意义体现为本能的、激情式的暴力现实反感态度,至少不是象第四代诗人那样具有自觉、寻求根源的反暴力现实态度。张修林《流落民间的艺术》(注33)就是对本真现实艺术的畸形存在状态的一种揭示,并同时呈现出一种反对暴力现实的自觉态度。朱杰的《饕餮者》(注34)以一个贪婪的形象表征暴力现实自身的虚伪以及在本真精神重创下的不堪一击。伊沙的《诺贝尔奖:永恒的答谢辞》(注35)是对暴力现实艺术的强力抗拒,而且,这首诗中,伊沙还体现出这样一种企图:用暴力现实产生的手段消灭暴力现实,而伊沙在《强奸犯小C》(注36)中,深刻地呈现了暴力现实的一种运行状态:以貌似反暴力的形式扼杀人性的本真行动与力量。党管生的《在传染科门前晒太阳》(注37)表明了暴力现实的硬在性与无所不在性。曹光辉的《是否》(注38)是一个反映暴力现实对艺术侵害的文本,不是艺术对艺术家构成伤害,而是艺术家在暴力现实面前因抗拒而自我伤害。与第三代相比,第四代诗人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本真艺术现实自足、锋利的自觉态度,并根源性地阐发了暴力现实的顽固存在以及对待暴力现实可能采用的消解性甚至毁灭性手段。可以这样认为,第四代诗歌是更接近于本真现实的诗歌,它的出现使抵达本真现实的诗歌企图成为可能。
2、 语言现实价值的重新界定和还原
现实语言包括原现实语言与再现实语言。作为一种再语言现实的艺术,艺术参与世界的变化体现了艺术最具灵动、最富灵性的特质。所以,艺术变化是世界的唯一心灵性运动。艺术的语言现实价值表现在它的独立性、对世界生成与变化的介入性。在这里,“世界”这一概念是指人的世界。然而,权力性语言---一种语言的衍生形态的暴力性操作瓦解了语言现实的独立、介入本真价值。人就是世界本身,但人(人的外在)的贪婪与残暴导致乱泄权欲而丧失了艺术,同时也丧失了人自我的本真性。从此艺术不再独立、不再有效地克制性地介入人的现实价值。艺术作为对人的自我约束的功能消解,而艺术作为对人的有效外延却发展得无以复加。这种权欲引起的不平甚至扭曲的操作形态,使语言现实成为了权力性语言现实的诠释与附庸,人成为了一个以权力话语为中心的世界。科学把人作为机器以及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也就是权欲支配下的语言现实丧失。这种倒挂与错位,导致了语言现实本真伦理的瓦解。所谓本真伦理,指本质现实内部的本真顺序与结构。艺术在权欲引起的错位中已经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第四代诗人认为,要实现诗歌语言现实的独立性和有效介入、有效拓展人的能动,就必须使诗歌语言服从而且仅仅是服从作为世界现实的语言,把诗歌从贪婪与残暴的权欲中解放出来,对其价值进行有效还原。还原是指使语言现实价值回复本真价值轨道。
A、语言现实本真价值的界定
把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定义为本真语言现实的价值趋向,即作为人的本真世界的价值秩序、形态、结构的总称。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特征,第四代诗歌(理论)把其界定为:独立性、对人性的有效制约、对人性外延的有效拓展。
a、 趋向独立价值形态的诗歌
毫无疑问,独立性是事物存在意义、存在价值的突出概念表征,同样,对于诗歌语言现实而言,独立性程度表明着它的本真性程度和被异化、肢解化程度。一种艺术是否走向成熟,最基本的、最直观的就是看它是否具有独立性。第四代诗人自觉地对诗歌语言现实的独立性程度保持警惕,把独立性作为诗歌本真价值形态的主要界定之一。
从一种宽容的、比较性的角度上讲,第三代诗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价值独立倾向,因为,第三代诗歌已经显而易见地区别于它之前的艺术形态(郭沫若等人的白话诗和北岛等人的朦胧诗)。如果我们严格一些地分析,第三代诗歌的独立性很成问题,象一个叛逆的小孩在家庭中所产生的风暴一样,小孩最终并未获得他所企图的独立。第三代诗歌对独立性的实现企图就是这样:风波产生但随之消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第三代首先是情绪的,其次是不彻底的。而第四代诗人的自觉性、主见性实现着诗歌本真价值独立的可能过程。第三代诗人成为了第四代诗人的活教材,所以,第四代诗人一开始就成为了有鲜明目的的精神独立者。马永波《文明的形式》(注39)对被侵扰、异化的价值形态实行形式性解构。伊沙的《野种之歌》(注40)在历史与文明的非独立价值中实现作为人本体的真实独立价值,诗的非道德化和非逻辑化赋予了作品的直接性和坚定性独立倾向,而他的《车过黄河》(注41)在无视所谓历史文明积淀和无视甚至敌意于暴力性非独立价值的人类权欲中获得了真实的价值独立态度。杨春光的《精品》(注42)对暴力价值的伪革命的权欲价值与权欲虚饰进行战略性进攻,由此获得价值独立性的精神理想。阿坚的《牵一只羊走进广场》(注43)则直接进入原初价值中,通过对现存非独立价值的反思批判而企图澄清价值的独立存在。姚辉的《镍币及其它》(注44)通过独立价值侵袭的象征体---镍币的深入描写以建立“主义”性的诗歌语言现实本真独立价值的体系。第四代诗人对价值形态的结构性深入体现了他们对价值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他们的有效行动维护了语言的价值独立性,第四代诗人的创作告诉我们:语言价值的独立绝对不是可能的,而是存在的。
b、 对人性的有效制约
人性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更不是简单的良性运动。艺术的价值作用之一,在于对人性的能动进行介入、制约,使人性的能动状态与过程始终保持符合人性自身的规范。但艺术与人性能动的启发性配合并非一直处于协调状况,而是恰恰相反,人性的恣肆能动不仅未得到艺术价值的有效调整与厄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艺术的本真价值,使艺术价值成为以人性恣肆能动为中心的附庸非本真价值。第四代诗人的态度,就是要使艺术价值成为对人性恣肆能动实行严格控制、规范的有力武器。伊沙的《请克林顿总统选择填空》(注45)对政治这一人性恣肆能动领域指代的客观总领下实行战争、独裁的人性恣肆行为与人的本真存在基础指代排列,实现语言价值的有力介入与制约。杨春光的《赝事》(注46)在对人性能动的深层存在的精神性批判中实现文本的制约力量。孙磊的《幻像》(注47)呈示一种坚持与等待的人性恣肆的最后消失。张修林的《消费战争》(注48)将战争这一人性的恣肆与迷失的实体作了一种独特的解构处理:既不是嫁接,也不是改造,而是瓦解战争的作为存在的存在,从而在“战争”之中得到系列的高度人性所指。第三代诗人在对人性恣肆的隐约感觉中采用的基本态度是迷惑与游戏,采用玩世不恭类型的诗歌语言放纵方法,由此引起的仅是对人性恣肆的疏远与隔膜,而第四代诗人是直接意识地介入人性能动的恣肆形态,不是放纵、疏远与隔离,而是自觉地达到动作与力量的诗歌体现。
c、 对人性能动的外延拓展
把人性能动的外延定义为人性能动中人类内在之间的溶触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外在溶触。人性能动的发展,在于其外延的历时性拓展。艺术同样肩负着人性能动的任务。艺术在对人类能动性的制约与拓展中获得自身的平衡,同时也使人性能动达到本然的平衡。无论怎样,艺术对人性能动外延的拓展有着一定的限制性:拓展必须建立于人性的基本内在本真形态。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科学和艺术造成人性异化及自然对人类的逆向关系(即对人类造成灾难),就是对人性的拓展偏离上述限制性的结果。诗歌必须服从这种限制性,但必须是在对人性能动的拓展中实施这种限制性。第四代诗人认为,诗歌对人性能动的拓展性,使诗歌成为历史与社会的一种手段。诗歌永远不会消亡,正如历史不会中断一样。历史感与现实感使第四代诗人成为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艺术群体。不是虚无,而是面对存在,在存在中求得诗歌拓展人性外延的本真文化意义。伊沙的《卡通片》(注50),不仅反对人性的惰性意识,而且在人与自然的溶触中实现人性的自然性能动拓展,而《档案》(注51)表明人性能动未知领域的多种可能。马永波《存在的深度》(注52)揭示人性周围的隐密热度使人性并不局限于已有的能动状态。狼人的《会飞的词》(注53)凹现出人性能动的外延拓展,超现实的物象与人性文化形态实现着人性的溶触进程。
B、语言现实本真价值的还原
第三代的理论家周伦佑先生提出价值变构亦即语言变构,并用取消“两值对立”结构、取消价值评价、清除价值词的方法实现语言变构,企图由此达到解放语言的目的。这种理论的解构性对价值进行的不是一般的清算,而是企图将其彻底消失。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文化性破坏理论。这种理论告诉我们:解构就是毁灭。实际上,并不是“价值”构成了对人类与社会本真的伤害,而是“伪价值”的呈现后果。取消了语言/现实或者语言----文化的一切价值倾向,诗歌的位置是否还可以存在?这是一种偏激的导致诗歌自我消亡的理论。不是不需要“价值”,而是应当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这才是诗歌的“价值”理论任务。在第四代诗人看来,对“价值”的解构是必须的,但必须使“解构”本身成为一种对“价值”的新型“结构”行为。对伪价值进行解构,以期结构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这就是第四代的全部“价值”中心行为。考察我们的语言现实所处价值系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伪价值---非伪价值对立结构。而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系统则是本真价值----伪本真价值(伪价值)对立结构。为此,必须通过对伪价值的解构从而还原“价值”的本真性,建构以本真价值为主体的本真价值----伪价值系统。虚饰现实与暴力现实是产生以伪价值为主体的价值系统的根源。所以,必须寻求未经虚饰与暴力的元度现实(本真性的再现实)对应的元度价值,建立新型的元度价值亦即本真价值的语言现实价值系统。
a、 本真价值的建立
本真价值是元度价值的人性能动发展语言现实价值。所以,对元度价值的提出旨在通过考察人性初始状态建立人性化的价值形态,而本真价值这个概念与目前阶段人性态势相对应,并迎合人性的未经发展。本真价值是人性化的历时性概念。要建立本真价值,就必须把伪人性---人性的虚饰与暴力语言现实作为对立对象,建立本真人性的形态,规范本真人性的范畴。人性的基本自由性与能动性是本真人性的基础。本真人性取消人的内部对立与人和自然的外部对立,实现生存与能动的谐和。顺应元度价值的人性能动,本真价值成为这样一种形态:
(1)、社会是个人的复合组成形式,它是一个包容个人个性化的总体人类本真人性指称;
(2)、文明是本真人性的发展过程与态势,政体是本真人性的结构性组织;
(3)、科技和文化是本真人性能动的触须。
考察第四代诗歌,就会发现,它存在着这样一种以本真人性为中心的本真价值趋向。千叶的《光线》(注54)实现着一种本真人性的集合性缝制。张修林的《最初的玫瑰》(注55)实现着元度价值的指称性呈现以及它与人性能动的现实遇合。杨春光的《我知道你的长方形》(注56)以爱情的精神形式显示一种政体性的本真人性组织。伊沙的《我是一笔被写错的汉字》(注57)标示着异化的人性向本真人性的本真价值系统过渡。
b、本真价值的评价与对比系统
与伪价值系统相似的是,本真价值系统仍然是一种两值对立结构的系统。本真价值系统的评价就是严格区分本真价值与伪本真价值,本真价值是褒义的,伪本真价值则是贬义的。区分方法是看待估价值是否符合本真价值的三中形态呈现,符合则是本真价值,不符合则非本真价值。本真价值系统一般性地运用现有的价值词汇和褒贬分类,取消中性词汇,将中性词汇划入褒义词汇或贬义词汇。凡现在的中性词汇中表征着本真人性或本真价值的内在外在谐和的,称为褒义词,反之,就是贬义词。如“战争”这一词汇,就是贬义词。在上述中,“非本真价值”与“伪价值”同义,也称“伪本真价值”,“非伪价值”则与“本真价值”同义。
三、 对此文的说明补充
1.本文的所谓理论不是诗学界所称的“语言中心论”那样的或类似的理论,因为本文所称的“语言”不是“语言中心论”所理解的那种语言。
2.这不是一篇对第四代诗歌的总结性批评文章,亦不是一篇纯粹的诗歌理论文章,它仅是作者的所谓创作理论与第四代诗人的创作趋向的遇合。
3. 作者并不试图在此文中对一些他所提出的概念作深入阐述。
4. 欢迎对本文进行批评,尤其是被他界定为“第四代”的每一个诗人。
1997-08
+-注:
(1)关于“第四代诗歌”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89年左右,用以指称区别与1989年之前的“第三代诗歌”,但当时显然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创作群体。在该文中,为了界定创作形态与群体的需要,借用这一概念。 (2)、(5)请参阅《非非创刊号》(成都1986)及《非非》第三期理论专号(成都1988)。
(3)关于第三代影响的蜕化期,众说不一,作者认为应当把1989年作为第三代的所谓“终结”时间。
(4)当时认为先锋诗歌处于空白状态的批评家主要是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和部分第三代批评家。
(6)请参阅“他们文学社”的诗刊《他们》各期。
(7)、(8)、(9)、(20)、(21)、(22)、(29)、(35)、(40)、(41)、(50)、(51)、(57)见《饿死诗人》(伊沙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4年版)页24、45、23、19、44、51、141、10、14、5、41、143、64。
(10)、(56)见周渔编《表达》95年12月总第二、三缉版七。
(11)、(31)见邹赴晓李步钊编《蓝族》94年第一缉版二、五。
(12)、(26)、(48)、(49)见周渔编97年8月总第五期版三,第六期版七。
(13)见麦子等编《杨子鳄》95年9月总第27期版三。
(14)见杨春光等编《空房子诗报》总第七期版二。
(15)、(16)见伊沙等著《一行乘三》(青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页85、91。
(17)、(18)、(19)、(32)见达达等编《倾斜诗刊》(杭州,1996)第五期页24、32、60、78。
(23)见杨春光等编《空房子诗报》总第五期版七。
(24)、(25)、(27)见潘友强等编《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94年版)页22、27、32。
(28)见《空房子诗报》总第四期。
(30)见邹赴晓李步钊张修林著《上升:青年诗人三家自选诗》(香港天马图书出版公司92年版)页78。
(33)、(42)、(46)见93年9月《锋刃》(吕叶编)总第一缉版二、六。
(34)、(36)、(52)、(55)见袁勇等编《诗歌创作与研究》94年上部页19、36、23、38。
(37)、(44)见吕叶编94年3月《锋刃》总第二缉页59、34。
(38)见潘友强编《魔岩》96年12月第六缉页3。
(39)、(53)见麦子等编《杨子鳄》95年6月总第26期版二。
(43)、(45)、(47)见中岛等编95年8月第十、十一期合刊《诗参考》版一、四。
(54)见周渔编《表达》97年1月总第四缉版四。
张修林
一、 第三代诗歌及“第四代诗歌”(注1)的界定
把继朦胧诗之后,发端于一九八六年,以非非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先锋诗歌创作形态称为“第三代”,这一概念与界定已经进入中国文学史。给中国诗坛带来前所未有巨大冲击的“第三代”诗歌革命运动,以其破坏性、取消价值中心和反对传统诗歌的语言形态,为先锋诗歌的创作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机遇和影响,成为了中国先锋诗歌与世界接轨的发展基石。然而,由于社会境遇及“第三代”内部自身的原因,这场运动及其轰动效应逐渐微弱下去。“破坏破坏再破坏”的“第三代”,尽管非非主义史无前例地建造了一个“中国式乌托帮”的“前文化语言---反价值”的独立艺术语言理论系统(注2),但自身的理论严重脱离艺术现实环境以及建设意义的匮乏而未能解决先锋诗歌的语言社会能动性问题。诗歌是一种关于社会与文化命题的艺术,它必须具有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功能。对于诗歌,仅仅说出是不够的,说出必须就是行动。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察第三代诗歌,就会发现,它的语言层次更多的是文化/文明上的喧哗与骚动,而不是其它什么。
在第三代沉寂之后(注3),一些批评家(注4)认为先锋诗歌创作转入空白状态。实质是,这是一种文本批评视角的空白。从这时开始,一批更年轻的诗人象一支执行神圣使命的夜行军,静悄悄地民间报刊的形式占据着先锋诗歌的阵地。他们从第三代尤其是非非主义中获取启示与动力,寻找先锋诗歌更富于感性的、更切入人类生命与存在文明的表现手段。他们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现实斗争的精神表征。他们行进得缓慢,没有第三代那样的广告性、轰动性效应,但实在地接近着诗歌。他们或许并不完美,但他们在发展。这一批年轻诗人历史性地成为了“第四代”的主体力量。另外,“第四代”的范畴也包括曾经追随于第三代,但在第三代之后在理论与创作上严格区别于第三代,且其创作形态与上述第四代主体融为一体的先锋诗人。
二、 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
毫无疑问,在研究与阐述第四代的诗歌形态时,“第三代”是作为一个更具有比较与顺承性的参考传统。
关于第三代的语言理论与语言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非非主义的前语言(作为宇宙自身的体现,是一种“无语义语言”)和语言的价值变构 (注5);
韩东的“诗歌到语言为止”的主张以及“他们”的口语创作形态(注6);
整体主义的所谓古典式语言态度。
第三代中的非非主义的语言价值变构理论具有一定的文化现实意义,企图通过语言的价值变构达到文化的拨乱反正,但代表着第三代的最高水准的这种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发现认识到语言就是历史与现实本身。
所谓“语言就是现实”,是指语言与现实同构、同一,语言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现实。
这种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现实由原语言/原现实与再语言/再现实组成。自然本身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原语言/原现实,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再语言/再现实。艺术语言/艺术现实是一种本真的再语言/再现实。变化包括自然变化和人类参与的动性变化,亦即原变化与再变化,艺术变化是一种人性的本真变化,是所有变化中最富灵性、最具灵动的变化。
第四代诗人的这种区别于第三代的语言态度,无疑在创作中更为有效地体现了语言的现实倾向,这使第四代诗人在第三代之后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形态成为可能。
1、 取消诗歌语言的非现实性
“语言就是现实”这一理论对于诗歌而言,首要任务就是
要取消诗歌语言的非现实性,让诗歌成为一种与非现实性语言斗争的手段,让诗歌在取消非现实中凹现一种全新本真现实语言,而这种全新现实语言不仅作为一种诗歌现实革命行为,而且是作为一种更为彻底的人性反拨现实。
A、取消神话写作,重新规划人的能指
神话写作使人的臆造在伪现实中虚脱化、消解了人的生存现实、抹杀了文明的本质人性。神话的臆想使人的能指虚浮、淡化,人的能指在神话中成为非人,人未指向人。第四代诗歌取消非现实的手段之一就是取消神话写作,在“人话”写作中实现人的本体能指。反映神性思维与活动的描写叫做神话,第四代诗人的“人话”则是反映人性思维与活动的描写。人话作为人本体书写,其目的就是企图把人的能指从神话中解放出来。
a、性现实的诗歌
在第四代诗人看来,性是神话的组成部分,但首先是人话的组成部分。性现实是诗歌现实的有效的、本质人性的组成部分。所谓性现实,是指人本体的性意识、性思维、性行动的社会现实客观存在。伊沙在《和日本女人亲热》(注7)、《走向生活》(注8)、《春天的事件》(注9)等大量作品中,把人的性现实作为表现的唯一对象和可能。杨春光在《圆的和方的》(注10)、《榕榕小妹的消息》(注11)等不少作品中,纯粹人化的性揭示不仅消解了神话的性能指,而且消解了一些权威性词语表征的非现实政治性。张修林的《上学去》(注12)等作品,则是以人的性形态和性的本体潜意识瓦解巨大、深层的伪意识形态现实。狼人的《高速公路》通过性意识的无所谓状态表现科学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的无所谓现实。曹光辉《玩的爱情》(注13)表现了人本体的非神话性的由肉体而爱情的过程。另外,第四代的一些女诗人,如周凤鸣、李轻松、贾薇、于小尘等,以女性的角度表现了性的真实现实。
b、日常生活经验:个体性写作
取消神话的可能性之一是,随着神性的瓦解,个人成为自己的最高主宰,人的能指倾向个人性,由此引起个体性写作:发掘个人性的独特能指,表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形态及经验。应当指出,这种个人性能指亦是人性能指的组成部分,尽管它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这种写作状态,仍是对神话和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物欲膨胀的有效校正与反击。上述所列举的杨春光的一些“性意识作品”也可归入此类,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性的能指。另外,杨春光的《人在边缘》(注14)表现了极端个体的“边缘“体验,尽管杨春光这里不完全是处于日常生活范畴。伊沙的《关于春天命题的写作》(注15)基于对春天的个人细致感受反驳作为传统文明之一的古诗,而他的《教子有方》(注16)则是高度个人能指倾向的体现,至于《遥远的前世》(注17),伊沙企图通过对时空的重组在个体能指中达到消解所谓道德的目的。丁小村的《简单主义》则是在单调的人体能指中消解繁复的现实逻辑。夜林《我造的世界》(注19)通过个体能指的高度主宰企图达到诗歌对神话本质或神话的总象征体的消解。与第三代的所谓口语日常生活诗不同,第四代更大限度地抵达了对既有现实的本质性消解。于坚的日常生活创作,几乎更多只是停留在生活细节的真实描述,韩东则似乎想超越日常生活本身。但他提供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简单文化消解。可以说,第四代比第三代更进一步抵达了日常生活细节内部,并在其中大幅度地完成了消解的真实与超越。
c、反对神话与宗教的终极意义
神话往往外显一些虚无的所谓理想的化身,宗教仍然用一些不切合现实生存状态的所谓大同世界之类的教义蛊惑人心,人们对宗教和神话的神往,淡化与忽视了生存中刻不容缓的“硬问题”,企图承受不符合人性的灾难而等待所谓上帝的福音。第四代诗人认为,只有人本身、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的迫切改善是真实的,宗教与神话对现实斗争的严重消解,使人的本性呆滞、意志薄弱,越发恶劣了人的主体性状态。任何所谓上帝及宗教式幻想的终极意义,都必然阻碍社会进步。所以,第四代诗歌,表现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同这种环境的挑战。人永远处于这种挑战状态。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一次或几次挑战,挑战同步于无止境的人类进步中。而第三代诗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对生存的不满,对生存元素持一种本然的抵触。第四代是毫不保留地对生存宣战,对生存元素宣战,甚至对劣性的人性宣战。伊沙的《法西斯艺术》(注20)以反讽的形式批判专制的艺术制度,《星期天夜间的事件》(注21)深刻地揭露了“上帝意识”对人类的残害,《叛国者》(注22)则是对现实颠倒的反拨。余怒的《苦海》(注23)在具象中呈现对生存元素的始终介入中。张修林《零度的夏天》(注24)对不温不火的现实情绪及严峻的生存困境实现了宣战式的对比。邹赴晓《空虚的沙子》(注25)在回归的还原激情中反动了人的异化与价值逆差。周渔的《经验》(注26)作为对所谓存在的否定而实现未经的精神企图。第三代诗人有着深刻的对宗教神话的怀疑倾向,但其态度实质上更多只是情绪性的东西,而第四代诗人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而且大多是手段性的表现,而不是情绪性的表现。
B、取消语言的虚饰现实与暴力现实
作为现实的语言本体,它自足、充盈,表征着真实的、生成的现实结构。然而,语言现实存在着它自身的病态衍生物---伪语言现实。伪语言是一种虚饰现实与暴力现实的“现实操作形态”。一些政治手段、弱化人智的畸形人格,往往就表现出对语言的虚饰与暴力行为。艺术语言的任务就是反对语言的虚饰性与暴力性,复苏语言的真实现实结构功能。
a、 取消虚饰现实的诗歌
虚饰现实是对现实进行胡夸、曲解、对事实进行隐蔽的一种伪现实行为。虚饰现实有时利用伪逻辑作为手段构筑,貌似有理有据,实则胡搅蛮缠。在当代,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胡夸风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虚饰现实典型表现。虚饰现实历史性地存在于各种社会事实与艺术语言现实中。虚饰现实始自奴社会的诞生,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则是始自阶级的产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随着人类的内部分野---大多数人的主体客化---语言的现实错位开始产生,语言与本真现实统一、完全同一出现了空前的、持续而无期的裂解。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少数人组成的强力集团的伪善人性与自私的暴力人性相结合产生了历史上的伪逻辑系统。伪逻辑最初只是简单的借口、搪塞和表露性欺骗,而后在所谓文化/文明进步中发展成为了具有隐蔽性、系统性、理论性的伪逻辑系统。人类文明的发展实质就是承袭与发展伪逻辑系统的集团的覆灭与更替的历时性转换过程。艺术历史性地成为了伪逻辑系统的条理及实质诠释。艺术在发展,因为它的诠释性处在不断改善之中,但艺术并未真正发展,艺术总在这个系统中诠释。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不是改善这种艺术形态,而是实质性地改变这种艺术形态。第四代诗歌敏锐、高屋建瓴地发现并把握了这种巨大的混沌语言历史,并企图从这些复杂的文明遗骸中回复语言与现实同构、同一性,从而实质地改变人类的文明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第四代诗歌正在进行一场还未有结果的伟大的诗歌语言革命。张修林《历时的分析》(注27)描述性、持续性地表现这种历史逻辑与文明历时性的生成与转换。杨春光的《杀手》(注28)是以诗歌作为对这种文明形态的介入与清算手段。伊沙的《废品店》(注29)以对人化的铁的描述反映了在这种逻辑与文明中人本体自觉的、甚至是本然的反抗。步钊的《最先开放的花朵》(注30)粗放型地企图实现人性与生存现实的激情性逻辑对抗。千叶的《会有一阵白色的风吹起……》(注31)是对颓废文明的现象反击与揭露。达达的《在流放地》(注32)表面伪逻辑现实的庞大性与人性在其面前抗拒的艰难性。非非主义创始者周伦佑先生的反价值理论与第四代诗人的创作认知有一定的形似性和一致性,但显而易见的是,认知途径和根源不同,第四代诗人的认知来自对历史事实与生存状态的反思、研究与把握。更值得一谈的是,第三代的诗歌创作并未实现周伦佑先生的反价值手段,第三代诗人对待伪逻辑与虚饰现实的态度是含混的、不坚定而游移于伪逻辑表层结构的。第四代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已经对伪逻辑有了整体性的、要害性的认识,并已在其本质结构中开展了消解甚至企图重建的工作,尽管这种工作还显得非常不力。
b、 取消暴力现实的诗歌
暴力现实即是对本真现实施暴的行为。暴力现实的表现很多,范围很广。一般说来,暴力现实在各方面都体现为对本真人性的武力性、强制性扼杀。它与虚饰现实不同,虚饰现实更多的是利用欺骗、伪文化、伪逻辑等软鞭子实现愚民,或者作为团结一些独特人士,作为招兵买马、引起轰动与注视的手段,而暴力现实则是动用武力的机器直接运作或将其作为暴力现实的后盾。艺术的暴力现实体现为对艺术强加一套所谓制作指导方法,或者以暴力性质的力量作为后盾对不合乎所谓规则的艺术进行棒杀。暴力现实从各个方面对艺术进行渗透,并且,在从事所谓艺术的集团与个人之间,也同样惊心动魄地引发暴力现实行动,比如一些并未建立于学术角度的所谓艺术批评就属于此类。暴力现实只承认一种或一套规则的艺术。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专断的所谓前卫艺术家艺术理论家也扛上了暴力现实的工具。第四代诗人认为,中国从未出现过正常的争鸣习惯与形态,就是暴力现实存在的最直接体现,在中国,你难以见到学术角度的艺术批判文章。在这里面,艺术家们仍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传统的惰性让艺术家成为了精神不健全的人群。第四代诗人企图改变这样一种阻碍艺术进步的超常习惯性状态。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清除暴力现实中恢复诗歌的本真人性与本真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讲,第四代诗歌必定单不仅是诗歌的,人首先是精神的。诗歌的传统历来缺乏真正的、关键的与整体性反思的精神向度。我们可以看出,第三代诗人与第四代诗人的差距,在于第三代诗人的群体性社会意义体现为本能的、激情式的暴力现实反感态度,至少不是象第四代诗人那样具有自觉、寻求根源的反暴力现实态度。张修林《流落民间的艺术》(注33)就是对本真现实艺术的畸形存在状态的一种揭示,并同时呈现出一种反对暴力现实的自觉态度。朱杰的《饕餮者》(注34)以一个贪婪的形象表征暴力现实自身的虚伪以及在本真精神重创下的不堪一击。伊沙的《诺贝尔奖:永恒的答谢辞》(注35)是对暴力现实艺术的强力抗拒,而且,这首诗中,伊沙还体现出这样一种企图:用暴力现实产生的手段消灭暴力现实,而伊沙在《强奸犯小C》(注36)中,深刻地呈现了暴力现实的一种运行状态:以貌似反暴力的形式扼杀人性的本真行动与力量。党管生的《在传染科门前晒太阳》(注37)表明了暴力现实的硬在性与无所不在性。曹光辉的《是否》(注38)是一个反映暴力现实对艺术侵害的文本,不是艺术对艺术家构成伤害,而是艺术家在暴力现实面前因抗拒而自我伤害。与第三代相比,第四代诗人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本真艺术现实自足、锋利的自觉态度,并根源性地阐发了暴力现实的顽固存在以及对待暴力现实可能采用的消解性甚至毁灭性手段。可以这样认为,第四代诗歌是更接近于本真现实的诗歌,它的出现使抵达本真现实的诗歌企图成为可能。
2、 语言现实价值的重新界定和还原
现实语言包括原现实语言与再现实语言。作为一种再语言现实的艺术,艺术参与世界的变化体现了艺术最具灵动、最富灵性的特质。所以,艺术变化是世界的唯一心灵性运动。艺术的语言现实价值表现在它的独立性、对世界生成与变化的介入性。在这里,“世界”这一概念是指人的世界。然而,权力性语言---一种语言的衍生形态的暴力性操作瓦解了语言现实的独立、介入本真价值。人就是世界本身,但人(人的外在)的贪婪与残暴导致乱泄权欲而丧失了艺术,同时也丧失了人自我的本真性。从此艺术不再独立、不再有效地克制性地介入人的现实价值。艺术作为对人的自我约束的功能消解,而艺术作为对人的有效外延却发展得无以复加。这种权欲引起的不平甚至扭曲的操作形态,使语言现实成为了权力性语言现实的诠释与附庸,人成为了一个以权力话语为中心的世界。科学把人作为机器以及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也就是权欲支配下的语言现实丧失。这种倒挂与错位,导致了语言现实本真伦理的瓦解。所谓本真伦理,指本质现实内部的本真顺序与结构。艺术在权欲引起的错位中已经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第四代诗人认为,要实现诗歌语言现实的独立性和有效介入、有效拓展人的能动,就必须使诗歌语言服从而且仅仅是服从作为世界现实的语言,把诗歌从贪婪与残暴的权欲中解放出来,对其价值进行有效还原。还原是指使语言现实价值回复本真价值轨道。
A、语言现实本真价值的界定
把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定义为本真语言现实的价值趋向,即作为人的本真世界的价值秩序、形态、结构的总称。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特征,第四代诗歌(理论)把其界定为:独立性、对人性的有效制约、对人性外延的有效拓展。
a、 趋向独立价值形态的诗歌
毫无疑问,独立性是事物存在意义、存在价值的突出概念表征,同样,对于诗歌语言现实而言,独立性程度表明着它的本真性程度和被异化、肢解化程度。一种艺术是否走向成熟,最基本的、最直观的就是看它是否具有独立性。第四代诗人自觉地对诗歌语言现实的独立性程度保持警惕,把独立性作为诗歌本真价值形态的主要界定之一。
从一种宽容的、比较性的角度上讲,第三代诗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价值独立倾向,因为,第三代诗歌已经显而易见地区别于它之前的艺术形态(郭沫若等人的白话诗和北岛等人的朦胧诗)。如果我们严格一些地分析,第三代诗歌的独立性很成问题,象一个叛逆的小孩在家庭中所产生的风暴一样,小孩最终并未获得他所企图的独立。第三代诗歌对独立性的实现企图就是这样:风波产生但随之消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第三代首先是情绪的,其次是不彻底的。而第四代诗人的自觉性、主见性实现着诗歌本真价值独立的可能过程。第三代诗人成为了第四代诗人的活教材,所以,第四代诗人一开始就成为了有鲜明目的的精神独立者。马永波《文明的形式》(注39)对被侵扰、异化的价值形态实行形式性解构。伊沙的《野种之歌》(注40)在历史与文明的非独立价值中实现作为人本体的真实独立价值,诗的非道德化和非逻辑化赋予了作品的直接性和坚定性独立倾向,而他的《车过黄河》(注41)在无视所谓历史文明积淀和无视甚至敌意于暴力性非独立价值的人类权欲中获得了真实的价值独立态度。杨春光的《精品》(注42)对暴力价值的伪革命的权欲价值与权欲虚饰进行战略性进攻,由此获得价值独立性的精神理想。阿坚的《牵一只羊走进广场》(注43)则直接进入原初价值中,通过对现存非独立价值的反思批判而企图澄清价值的独立存在。姚辉的《镍币及其它》(注44)通过独立价值侵袭的象征体---镍币的深入描写以建立“主义”性的诗歌语言现实本真独立价值的体系。第四代诗人对价值形态的结构性深入体现了他们对价值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他们的有效行动维护了语言的价值独立性,第四代诗人的创作告诉我们:语言价值的独立绝对不是可能的,而是存在的。
b、 对人性的有效制约
人性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更不是简单的良性运动。艺术的价值作用之一,在于对人性的能动进行介入、制约,使人性的能动状态与过程始终保持符合人性自身的规范。但艺术与人性能动的启发性配合并非一直处于协调状况,而是恰恰相反,人性的恣肆能动不仅未得到艺术价值的有效调整与厄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艺术的本真价值,使艺术价值成为以人性恣肆能动为中心的附庸非本真价值。第四代诗人的态度,就是要使艺术价值成为对人性恣肆能动实行严格控制、规范的有力武器。伊沙的《请克林顿总统选择填空》(注45)对政治这一人性恣肆能动领域指代的客观总领下实行战争、独裁的人性恣肆行为与人的本真存在基础指代排列,实现语言价值的有力介入与制约。杨春光的《赝事》(注46)在对人性能动的深层存在的精神性批判中实现文本的制约力量。孙磊的《幻像》(注47)呈示一种坚持与等待的人性恣肆的最后消失。张修林的《消费战争》(注48)将战争这一人性的恣肆与迷失的实体作了一种独特的解构处理:既不是嫁接,也不是改造,而是瓦解战争的作为存在的存在,从而在“战争”之中得到系列的高度人性所指。第三代诗人在对人性恣肆的隐约感觉中采用的基本态度是迷惑与游戏,采用玩世不恭类型的诗歌语言放纵方法,由此引起的仅是对人性恣肆的疏远与隔膜,而第四代诗人是直接意识地介入人性能动的恣肆形态,不是放纵、疏远与隔离,而是自觉地达到动作与力量的诗歌体现。
c、 对人性能动的外延拓展
把人性能动的外延定义为人性能动中人类内在之间的溶触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外在溶触。人性能动的发展,在于其外延的历时性拓展。艺术同样肩负着人性能动的任务。艺术在对人类能动性的制约与拓展中获得自身的平衡,同时也使人性能动达到本然的平衡。无论怎样,艺术对人性能动外延的拓展有着一定的限制性:拓展必须建立于人性的基本内在本真形态。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科学和艺术造成人性异化及自然对人类的逆向关系(即对人类造成灾难),就是对人性的拓展偏离上述限制性的结果。诗歌必须服从这种限制性,但必须是在对人性能动的拓展中实施这种限制性。第四代诗人认为,诗歌对人性能动的拓展性,使诗歌成为历史与社会的一种手段。诗歌永远不会消亡,正如历史不会中断一样。历史感与现实感使第四代诗人成为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艺术群体。不是虚无,而是面对存在,在存在中求得诗歌拓展人性外延的本真文化意义。伊沙的《卡通片》(注50),不仅反对人性的惰性意识,而且在人与自然的溶触中实现人性的自然性能动拓展,而《档案》(注51)表明人性能动未知领域的多种可能。马永波《存在的深度》(注52)揭示人性周围的隐密热度使人性并不局限于已有的能动状态。狼人的《会飞的词》(注53)凹现出人性能动的外延拓展,超现实的物象与人性文化形态实现着人性的溶触进程。
B、语言现实本真价值的还原
第三代的理论家周伦佑先生提出价值变构亦即语言变构,并用取消“两值对立”结构、取消价值评价、清除价值词的方法实现语言变构,企图由此达到解放语言的目的。这种理论的解构性对价值进行的不是一般的清算,而是企图将其彻底消失。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文化性破坏理论。这种理论告诉我们:解构就是毁灭。实际上,并不是“价值”构成了对人类与社会本真的伤害,而是“伪价值”的呈现后果。取消了语言/现实或者语言----文化的一切价值倾向,诗歌的位置是否还可以存在?这是一种偏激的导致诗歌自我消亡的理论。不是不需要“价值”,而是应当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这才是诗歌的“价值”理论任务。在第四代诗人看来,对“价值”的解构是必须的,但必须使“解构”本身成为一种对“价值”的新型“结构”行为。对伪价值进行解构,以期结构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这就是第四代的全部“价值”中心行为。考察我们的语言现实所处价值系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伪价值---非伪价值对立结构。而语言现实的本真价值系统则是本真价值----伪本真价值(伪价值)对立结构。为此,必须通过对伪价值的解构从而还原“价值”的本真性,建构以本真价值为主体的本真价值----伪价值系统。虚饰现实与暴力现实是产生以伪价值为主体的价值系统的根源。所以,必须寻求未经虚饰与暴力的元度现实(本真性的再现实)对应的元度价值,建立新型的元度价值亦即本真价值的语言现实价值系统。
a、 本真价值的建立
本真价值是元度价值的人性能动发展语言现实价值。所以,对元度价值的提出旨在通过考察人性初始状态建立人性化的价值形态,而本真价值这个概念与目前阶段人性态势相对应,并迎合人性的未经发展。本真价值是人性化的历时性概念。要建立本真价值,就必须把伪人性---人性的虚饰与暴力语言现实作为对立对象,建立本真人性的形态,规范本真人性的范畴。人性的基本自由性与能动性是本真人性的基础。本真人性取消人的内部对立与人和自然的外部对立,实现生存与能动的谐和。顺应元度价值的人性能动,本真价值成为这样一种形态:
(1)、社会是个人的复合组成形式,它是一个包容个人个性化的总体人类本真人性指称;
(2)、文明是本真人性的发展过程与态势,政体是本真人性的结构性组织;
(3)、科技和文化是本真人性能动的触须。
考察第四代诗歌,就会发现,它存在着这样一种以本真人性为中心的本真价值趋向。千叶的《光线》(注54)实现着一种本真人性的集合性缝制。张修林的《最初的玫瑰》(注55)实现着元度价值的指称性呈现以及它与人性能动的现实遇合。杨春光的《我知道你的长方形》(注56)以爱情的精神形式显示一种政体性的本真人性组织。伊沙的《我是一笔被写错的汉字》(注57)标示着异化的人性向本真人性的本真价值系统过渡。
b、本真价值的评价与对比系统
与伪价值系统相似的是,本真价值系统仍然是一种两值对立结构的系统。本真价值系统的评价就是严格区分本真价值与伪本真价值,本真价值是褒义的,伪本真价值则是贬义的。区分方法是看待估价值是否符合本真价值的三中形态呈现,符合则是本真价值,不符合则非本真价值。本真价值系统一般性地运用现有的价值词汇和褒贬分类,取消中性词汇,将中性词汇划入褒义词汇或贬义词汇。凡现在的中性词汇中表征着本真人性或本真价值的内在外在谐和的,称为褒义词,反之,就是贬义词。如“战争”这一词汇,就是贬义词。在上述中,“非本真价值”与“伪价值”同义,也称“伪本真价值”,“非伪价值”则与“本真价值”同义。
三、 对此文的说明补充
1.本文的所谓理论不是诗学界所称的“语言中心论”那样的或类似的理论,因为本文所称的“语言”不是“语言中心论”所理解的那种语言。
2.这不是一篇对第四代诗歌的总结性批评文章,亦不是一篇纯粹的诗歌理论文章,它仅是作者的所谓创作理论与第四代诗人的创作趋向的遇合。
3. 作者并不试图在此文中对一些他所提出的概念作深入阐述。
4. 欢迎对本文进行批评,尤其是被他界定为“第四代”的每一个诗人。
1997-08
+-注:
(1)关于“第四代诗歌”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89年左右,用以指称区别与1989年之前的“第三代诗歌”,但当时显然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创作群体。在该文中,为了界定创作形态与群体的需要,借用这一概念。 (2)、(5)请参阅《非非创刊号》(成都1986)及《非非》第三期理论专号(成都1988)。
(3)关于第三代影响的蜕化期,众说不一,作者认为应当把1989年作为第三代的所谓“终结”时间。
(4)当时认为先锋诗歌处于空白状态的批评家主要是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和部分第三代批评家。
(6)请参阅“他们文学社”的诗刊《他们》各期。
(7)、(8)、(9)、(20)、(21)、(22)、(29)、(35)、(40)、(41)、(50)、(51)、(57)见《饿死诗人》(伊沙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4年版)页24、45、23、19、44、51、141、10、14、5、41、143、64。
(10)、(56)见周渔编《表达》95年12月总第二、三缉版七。
(11)、(31)见邹赴晓李步钊编《蓝族》94年第一缉版二、五。
(12)、(26)、(48)、(49)见周渔编97年8月总第五期版三,第六期版七。
(13)见麦子等编《杨子鳄》95年9月总第27期版三。
(14)见杨春光等编《空房子诗报》总第七期版二。
(15)、(16)见伊沙等著《一行乘三》(青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页85、91。
(17)、(18)、(19)、(32)见达达等编《倾斜诗刊》(杭州,1996)第五期页24、32、60、78。
(23)见杨春光等编《空房子诗报》总第五期版七。
(24)、(25)、(27)见潘友强等编《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94年版)页22、27、32。
(28)见《空房子诗报》总第四期。
(30)见邹赴晓李步钊张修林著《上升:青年诗人三家自选诗》(香港天马图书出版公司92年版)页78。
(33)、(42)、(46)见93年9月《锋刃》(吕叶编)总第一缉版二、六。
(34)、(36)、(52)、(55)见袁勇等编《诗歌创作与研究》94年上部页19、36、23、38。
(37)、(44)见吕叶编94年3月《锋刃》总第二缉页59、34。
(38)见潘友强编《魔岩》96年12月第六缉页3。
(39)、(53)见麦子等编《杨子鳄》95年6月总第26期版二。
(43)、(45)、(47)见中岛等编95年8月第十、十一期合刊《诗参考》版一、四。
(54)见周渔编《表达》97年1月总第四缉版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