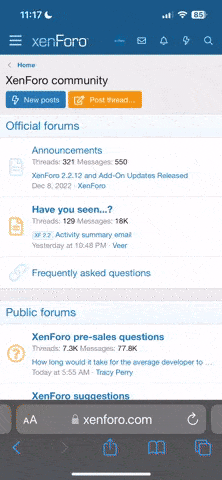我在路上颠簸了6个小时。技术太好的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都能把车开得忐忑不安。幸好车上人不多,我一直稳稳地占据了两个位置,姿态极其放肆夸张地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夜色徐徐。
回家的路总是无聊得让人心灰意冷,我用右脚踢了踢前面男人无知的屁股。他显然睡着了。鼾声轻轻地环绕在车厢里。只有我头顶的灯亮着,无所遁形。
每次经过隆昌我就欢喜发狂。因为这是吉吉的家。亲爱的,看看这美丽的一刻吧。我离你这么近,你离我这么远。我坐在一辆怪物般的铁皮车里怒吼着从你们的身躯上大肆招摇地经过,所有的信念终究将毁于一旦。只有历史还继续厚颜无耻地存留在那里。磐石般地无法转移。你在拉萨还好吗。你终于拥有最最美丽的高原红了吗。
多年以后我的姑娘越来越多。无可辩驳我是一个花心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多情而专一地对待每一个人。因为你们都是那样的不同。美得眩目。小七总是和我遇到同样的事,这大概和同年同月同日生有关系。她的文字也被抄袭。我相当喜欢那些字,奇突而美好。虽然我总是不能够很顺畅地一次读完。然而我们都不想再写字了,没法写。只在一席之博里撒撒野,闹腾闹腾。很多朋友都在忙长篇,忙约稿,忙着拍电影。多热闹。可是这热闹终究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我们什么也不缺。
绿绿不写了。我们不写了。
绿只女人总是发信息来告诉我最近的稿子特难凑。我昨晚梦到她离开了长沙去到深圳。她说因为深圳的圈子更单纯。我一直在想她能够在那家杂志社呆得长吗。还梦到一个疯了似的到处贴寻人启事的姑娘,她在找一个叫何涛的男人,她还记得他的公司叫东旭广告,还有他去丝路的时候拍的照片被做成了很漂亮的集子,翻山越岭地寄到她的手里。他曾经问她能否爱他。想起来是有点模糊了,我一直是一个健忘的姑娘,但对某些东西又有着偏执狂般固执的记忆。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真的能够再相遇,但我是在想念他吗。我们能够相爱吗。
雨越下越大。真冷。
忍不住在长长的羽绒服里打了一阵愉快的哆嗦。我还是喜欢冬天的。寒冷使人清醒。过度的寒冷又让人麻木。而这两种状态我都可以接受。冷空气肆无忌惮地吮吸着紧张的毛孔,直到所有的吻痕都呈现出苍白和青紫色,世界忽然如同水晶球被砸个粉碎,在泥泞的缝隙里夸张地光彩熠熠,寒冷使人忘记了曾经多么咬牙切齿的恨,于是我们寒颤着微笑着互相依偎,如同一场真正的爱情。
但这个姑娘已经厌倦了随时玩些暧昧的小把戏。她甚至没有兴趣抬起眼皮看任何男人。她甚至不再好色。这显然是一件对谁都有好处的事情。利人利己,爱国爱民。她旋转着手里的棉花棒狠狠地戳进自己的耳蜗里,疼痛就好象异族人的舞蹈,火苗在夜色里腾地燃烧,沾满暖甜的血腥。她在耳膜上锈出一朵血红色的蔷薇,暗暗绽放,暗暗枯萎。你一定无法想象那有多美。
戴着啤酒盖耳环的姑娘走上街,成为狂欢节日里人们注目的焦点。她的心脏周围开始破裂。慢慢撑裂。最后看上去像安装了一条丑陋而劣质的黑色拉链。
仿佛轻轻一拉,就有什么掉出来。
回家的路总是无聊得让人心灰意冷,我用右脚踢了踢前面男人无知的屁股。他显然睡着了。鼾声轻轻地环绕在车厢里。只有我头顶的灯亮着,无所遁形。
每次经过隆昌我就欢喜发狂。因为这是吉吉的家。亲爱的,看看这美丽的一刻吧。我离你这么近,你离我这么远。我坐在一辆怪物般的铁皮车里怒吼着从你们的身躯上大肆招摇地经过,所有的信念终究将毁于一旦。只有历史还继续厚颜无耻地存留在那里。磐石般地无法转移。你在拉萨还好吗。你终于拥有最最美丽的高原红了吗。
多年以后我的姑娘越来越多。无可辩驳我是一个花心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多情而专一地对待每一个人。因为你们都是那样的不同。美得眩目。小七总是和我遇到同样的事,这大概和同年同月同日生有关系。她的文字也被抄袭。我相当喜欢那些字,奇突而美好。虽然我总是不能够很顺畅地一次读完。然而我们都不想再写字了,没法写。只在一席之博里撒撒野,闹腾闹腾。很多朋友都在忙长篇,忙约稿,忙着拍电影。多热闹。可是这热闹终究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我们什么也不缺。
绿绿不写了。我们不写了。
绿只女人总是发信息来告诉我最近的稿子特难凑。我昨晚梦到她离开了长沙去到深圳。她说因为深圳的圈子更单纯。我一直在想她能够在那家杂志社呆得长吗。还梦到一个疯了似的到处贴寻人启事的姑娘,她在找一个叫何涛的男人,她还记得他的公司叫东旭广告,还有他去丝路的时候拍的照片被做成了很漂亮的集子,翻山越岭地寄到她的手里。他曾经问她能否爱他。想起来是有点模糊了,我一直是一个健忘的姑娘,但对某些东西又有着偏执狂般固执的记忆。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真的能够再相遇,但我是在想念他吗。我们能够相爱吗。
雨越下越大。真冷。
忍不住在长长的羽绒服里打了一阵愉快的哆嗦。我还是喜欢冬天的。寒冷使人清醒。过度的寒冷又让人麻木。而这两种状态我都可以接受。冷空气肆无忌惮地吮吸着紧张的毛孔,直到所有的吻痕都呈现出苍白和青紫色,世界忽然如同水晶球被砸个粉碎,在泥泞的缝隙里夸张地光彩熠熠,寒冷使人忘记了曾经多么咬牙切齿的恨,于是我们寒颤着微笑着互相依偎,如同一场真正的爱情。
但这个姑娘已经厌倦了随时玩些暧昧的小把戏。她甚至没有兴趣抬起眼皮看任何男人。她甚至不再好色。这显然是一件对谁都有好处的事情。利人利己,爱国爱民。她旋转着手里的棉花棒狠狠地戳进自己的耳蜗里,疼痛就好象异族人的舞蹈,火苗在夜色里腾地燃烧,沾满暖甜的血腥。她在耳膜上锈出一朵血红色的蔷薇,暗暗绽放,暗暗枯萎。你一定无法想象那有多美。
戴着啤酒盖耳环的姑娘走上街,成为狂欢节日里人们注目的焦点。她的心脏周围开始破裂。慢慢撑裂。最后看上去像安装了一条丑陋而劣质的黑色拉链。
仿佛轻轻一拉,就有什么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