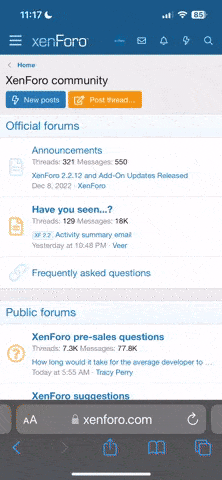suchislife
研究生
- 注册
- 2005-08-13
- 帖子
- 1,172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61
爱在云端的日子
1
2005年 7月26日 阴天 闷热
“你最好把帽子摘了。”
“天气很热,我的空调坏了。”
他拘窘地看了我一眼,再度把毛巾从身后小冰箱的冷冻库里拿出来。
我顺从地摘了帽子,妻子像机器人那样转过头来看一眼,有生锈的嘎吱声从她的脖子底下传过来。
“手续都办妥了,现在,只要各自在这儿签个字就行了。”
我停顿了一下才拿起桌上的水笔。
妻子没有犹豫,等我把笔拿稳时,她已经签完了。
“恭喜两位,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夫妻了。”
律师想绞毛巾里的水,又发现周围没有盛水的物件,只好暂且放到一边。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么?”
妻子谁也不看,摇摇头,然后,站起来。
“那…就这样了。”
我也站了起来。
外面一点阳光也没有,天气又闷又热,空气里的湿度很粘稠,估计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的前妻走在前面,并开始加快脚步。
“我说,你一定要这样么?”
我忍不住追上去问她,这是我一直很想知道的问题,但是,她从来就没有回答过我。
“你还是不肯说么?给我个理由,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
她还是不肯回过头来,不过,也不打算继续往前赶。
雷声从前方不远的地方传到我们停留的地区上方。
“以后,你也打算只爱她一个人么?”
“我是说,我们离婚以后。”
我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这就是你的理由?”
“她并不存在,她不是我人生里的人,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
“但是,却要跟着你一辈子。”
“对不起,我受不了这个,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忍受了。”
雷声变成霹雳从头顶呼啸而过。
前妻重新迈开脚步,这次,她走得飞快,好像被前路尽头的乌云吸了进去,就这么永远地消失在天边。
手机响起来,我大约知道是谁,虽然阵雨已经开始下了,我还是决定要冒雨和他见上一面。
“爸爸,是我,你已经到了,好,还是老地方,我马上就到。”
和父亲第一次面谈就是在那里。
小砂锅馄饨面的老板娘前年去世了,从那以后,父亲就不再去那里了。
我的父亲是我妻子的父亲,现在,我已经和他女儿不再有任何关系,于是,我们又可以恢复到初识时的样子,像亲生父子那样在馄饨面馆里头喝啤酒,只是,不能和以前一样喝得烂醉,因为,再也没有好心的老板娘叫车送我们回家了。
“你们最终还是分手了。”
父亲很平静,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我对他的愧疚。
“她嫁给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她,要和一个心里有着别的女人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他心里有着别的女人这件事,可惜,她最终还是没能做到,白白浪费了一段缘分。”
“她和她母亲一点也不像。”
“她像我,对人、对事都太执著,尤其是那些都已经过去的事,这是她的错,不是你的,你没有对不起她,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好女婿,我真替她惋惜。”
“你不要这样说,都是我不好,是我对她不够好,她才不要我的。”
父亲凝视我的眼睛。
许久,我们就只能这么凝视着而一句话也不说。
“还记得我们认识的那天么?”
“当然。”
“我还是觉得我的记性有问题,到你那里洗过那么多次车,怎么就从来没注意到你呢?”
“你问我会不会开车,我说会,你又问那你愿不愿意帮我开?我说好。”
父亲微笑。
“那是缘分。你和她,我和你,这都是缘分。有了缘分的人,是怎么也躲不开的,不管躲到哪里,总归还是要碰见的。”
雷雨越下越大。
店小二把冰镇啤酒端上了桌。
“这雨要下好一阵子了。”
“看样子是。”
“跟我说说你的故事。”
“你和她的故事。”
“你老婆,哦不,是你以前的老婆,只跟我说了一点点,就是她想答应你的求婚又不得不征求我意见的那天,现在,我想听你亲口说,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最起码得让我弄明白我女儿到底输给了谁?这个权利我总还有的。”
“说出来,怕你笑话。”
“为什么?”
“我是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偶然认识她的。”
“现在说起来就好像是前辈子的事,那天的天气和今天一样热,我一直盼着能下一场雨,可是,直到晌午也没看见一片乌云……”
2
1987年 7月17日 晴天 酷热
天气从未那么好过,太阳辣到抬头低头都睁不开眼,树都被晒傻了,找不见半块阴凉地。
当时,我刚从少年劳教中心放出来,那是我第五次重获自由,出来前,我把装着上等香烟的盒子包进防水的牛皮纸,藏到劳教中心男厕所的水箱里,以备下次再进去的时候还能有烟抽。
我没想到这次那么快就会被放出来,我和阿三头那伙人差点把吴家的杂货铺给烧了,是他儿子先打了我的人,我放火烧他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也只是吓唬吓唬,没想到真会烧起来。警察赶到时,能溜的都溜了,我因为忙着救火居然把逃跑那么重要的事给忘了,结果就这样,把我给抓了进去。
出来的头一个礼拜,二叔像猫看老鼠似地看着我,不敢让我踏出门槛半步,后来,没了耐性,就跑去居委会问有什么活可以给我干,正好小区的外墙要重新粉刷,那年夏天,我就因此而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个油漆工人。
油漆的活本来就不好干,尤其是要长时间吊在半空中,我又不是杂技演员,没学过那种功夫。天气一天胜一天地热,碰到有阴影的墙还好,至少不必惨遭太阳的暴晒,可是,那天,倒楣的那一天,我吊在二楼一家朝南窗户外面的时候,几乎觉得自己就快要死掉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点预兆都没有。
其实,哪怕只要有那么一点动静,我想我就会立即放松绳子爬下去,而不至于造成那种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误会里。
她在那里干什么呢?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一点声息也没有,真是活见鬼了。
我很小心地放下绳子,半空状态让我丝毫没有安全感。接着,我在二楼朝南的一家敞开的窗户前面停下,正儿八经地用刷子沾上油漆开始涂抹,这种情况下,要我不对窗户里探头探脑是不可能的,我发誓,那不是我小偷习性的卷土重来,只是,除了油漆、太阳,我的眼睛就只能面对那扇窗子,而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供停留。
那是一间明显有钱人家的屋子,可惜,酷热的下午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很为这家主人的安全担忧,可是,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开始哼歌,很轻很轻地哼,这时候,事情发生了,等我反应过来时,只能大叫一声,然后手上的绳子跟着一松,连人带桶整个掉了下去。
那个睡眼朦胧的女孩不晓得是从屋子的哪个房间里冒出来的。她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走到朝南的窗户前面,一边伸懒腰一边开始脱衣服,等到只剩下一条白色小裤衩的时候,被我的迎面而来的尖叫惊醒,不过,她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谁,我就已经坐在一楼的水泥地上了。
这导致我发出了另一声恐怖的哀号,不仅仅因为我的屁股开了花,还因为我那开了花的屁股是坐在木炭烤熟了的铁板上面,晌午的太阳本来就把我的脑袋晒得又昏又胀,屁股这一家伙更是让我眼冒金星小鸟乱飞。
于是,一溜串的脏话就劈里啪啦从嘴里倒出来了,这怪不得我,那对我来说真的和打嗝放屁没什么两样。
我琢磨着还能不能自己从地上爬起来,这时,公寓底楼的铁门嘎吱敞开一条缝,一张眼屎还没完全擦干净却依旧显得相当清秀的脸蛋从那里面探出来。
“我说,你…还好吧?”
我彻底傻了。
是刚才那个对着我脱衣服的女孩。
我想站起来,然后撒腿就跑,满身的油漆并不能为我证明什么,刚才那一幕是毫无疑问的流氓行为,说给谁听谁也不会相信。
可是,我爬不起来,屁股疼得好像散了架似的。
不说话,连看也不能看,虽然,她已经把衣服穿好了,而刚才我也确实没把她的上半身看清楚,问题是我也没想看她的上半身,只是,被她吓着了。
“说话呀?要不要我打电话送你去医院?”
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她索性走了出来,蹲下身子瞪着我的眼睛看。
“难道……变白痴了?”
我忽地一声从地上爬起来。
从来没人敢骂我是白痴,完了完了,她可把我惹火了,这下她死定了。
“说什么说什么!是你站在窗户前面对着我脱衣服,害我差点没摔死,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到底有没有脑子啊?大白天的站在窗口脱衣服,这这这叫什么事嘛……”
“二楼摔不死人的,顶多半身不遂。”
她平淡地插嘴。
“你!!……你个臭……”
“臭什么?我很臭么?”
她立刻抬起胳膊嗅。
“不会啊……我刚刚才洗过澡…奇怪,怎么会臭呢……”
我快昏了,我这就要昏。
这时,她突然想起刚才好像确实发生过什么事来着。
“你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什么了我。”
“我的身体啊。”
“没有,绝对没有,你你你那不是还穿着一条小裤衩呢么?”
“还是看见了……”
她喃喃自语地总结道。
然后,歪头想了一想,继续看着我,说:
“看见就看见呗,也没什么大不了了,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小,那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是看见你脱衣服,还是从二楼摔下来?”
她又想了一想,表情挺认真,这时候,我发现她的嘴唇很好看,眼睛也不错,就是眼角那颗小眼屎怎么瞧怎么别扭。
“现在看起来你是没什么事,我是说,那桶油漆怎么办?还有你身上这些,不赶快洗就洗不掉了。”
难道她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在想什么?”
她很警惕地用手指戳戳我意志不坚的肩胛。
“没,没想什么呀,我到没事,可我今天的活怎么办,总得干完那。”
“要不你再去弄点漆来,我跟你一起刷,你从外面刷,我从里面刷。”
终于松了口气,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万一我找漆的时候她打110把我当流氓给抓了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那你在这等着,不许跑掉,知道么?我马上就回来。”
“不许走啊,你可别再玩我了啊!”
我一边端着屁股跑一边回头大叫。
她站起来,两手交叉在胸,远远望去好像摆在门前的一个白玉雕琢的玩偶。
“要跑也是你跑!偷看我脱衣服的是你又不是我!!”
她故意叫得整栋楼的人都听见,致使我在半道上又狠狠摔了一跟头。
她的笑声更响亮了,我的头、胸、肚子屁股膝盖大腿没有一处不在疼,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心里却觉得说不出的好笑。
3
1987年 7月20日 晴天 还是热
7月17日的那个下午过得极其漫长。
她本来要和我换个位置再刷刷,说很想尝尝吊在半空的感觉,我没敢答应,这个下午已经够乱的了,再出什么纰漏,我就真的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
刷完时,已近黄昏,太阳慢慢地从外墙的阴影中褪去。
“我觉得颜色不够均匀。”
我用一只脚将垂悬的绳子离墙踢开一段距离,假装审视。
她把刷子丢进油漆桶,险些甩到我的肚皮上。
“哦?为什么?”
她看看自己的手,上面沾满了油漆,其实,她的脸上也有,我只是不方便讲而已。她一边有意无意地和我答话,一边继续研究手掌正反面的油漆,看着看着居然很满足地笑起来。
“我看咱们还得再重复刷几遍才行。”
“再说吧,我现在要去洗澡了。”
她不再理我,自顾自从窗台上爬下去。
我顿感无趣,只好把绳子收回原位,傻傻地看着她又回到最初发现我的位置上。她几乎立刻就转身要往浴室去了,可是,走了一半,忽然又转回头来看我。
“喂,你还吊在那里干什么?难道还想偷看我洗澡不成?”
我立刻抓起搁在她家窗台外面的油漆桶,滋溜一声滑到底。
正收拾残局的当口,忽听她的声音再度从二楼传下来:
“喂!你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刷呀?喂!喂!”
我头也不回打算就这么走了,可是,她还在一个劲地嚷嚷。
我琢磨着她肯定是个特无聊的女人。
“过两天,等我把前面那栋刷完了再说!”
我丢下这句话的时候也还是没有回头。
再遇见她是三天后的上午,手头的油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但我还是将油漆工的服装穿戴整齐,并且把那些必备的行头全部偷了出来。
我答应她过两天要再来漆那堵墙的,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如果,如果她因为我没去,又告我耍流氓怎么办?
那是个很馨宁的上午,沿着人工河道一路走去,四周的鲜花、树木、青草、绿荫都好像是活人装扮的道具,贼溜溜地踮起脚尖或跟在我后头,或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向我爱你拢,仿佛靠近了就能听见我心里的秘密似的。我依旧哼着我的歌,脚步也越踏越轻快,走近她家时我的声音更响了,迸发出那种高昂的走调的雄伟力量。她就趴在老地方等着我,我确定她是故意等我来着,因为她把长头发全部放到窗子外面来让它们像拉面师傅手里的细面条似地迎风招展,和前两天不同,那天她穿了件很体面的洋装,前半身几乎全部送出了窗外,仿佛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自己看见那扇窗户的霎那,隐藏在愚钝的十八岁少年心底所有的自作多情都被呼唤了起来,那种由衷的痴心妄想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幸福,甚至,在还没有从屋顶滑落到她面前时就已经飘在空中了。
我在云端看她,她像一个化身为人的天使。
只有我能看见她的翅膀,只有我。
“喂!我来了。”
我站在底楼仰头叫道。
她先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然后漫不经心地低头俯瞰。
我离她不近,但是,却能看见她脸上的表情好像一只在青苔上停留了24个时辰的蜗牛那么懒散。
“今天要不要跟我一起漆啊?”
我继续问她。
她不说话。
我觉得无趣,于是自己行动起来。
“我说!”
她终于开口了。
“你能不能先不要漆?”
“不漆?不漆干什么?”
“上来跟我聊聊天,行么?”
我低下头,心里怦怦怦跳了几个来回,迅速冷静下来。可我的手却一直在腰间粗糙的绳子上磨擦,直到发现已经搓出一堆碎皮子来。
“那那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一起带上来啊,反正你还是要漆的不是么?你按一下202的门铃,我帮你开门。”
我不打算磨蹭,于是就这样顺利地进了她的屋子,那间我已经窥视了很久也基本摸清底细的有钱家的屋子。
其实,装潢也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好。
她的家不大不小,看上去很干净很典雅,和我那离了婚的二叔的乱窝窝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也难怪,家里就我和他两个男人,谁空谁收拾,没空就不收拾,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她说刚好冰了解渴的大麦茶,要我在客厅里坐一下,这就端出来。
我觉得别扭,这屋子的气场跟我不合,坐哪里都不太合适,所以就一直站着。她觉得奇怪,并且对我这种行为表示鄙视,让我觉得自己更加猥琐。
“叫你坐你就坐,还嫌我的椅子脏么?”
“哦。”
我坐了下来,身上的绳索发出咣啷啷的声响,她并没有强迫我把那些累赘解下来,这让我感到舒适的安慰。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看你不像油漆工人。”
她语气变和缓了,金黄色的大麦茶沿着玻璃徐徐倒入。
这个问题很复杂,该怎么回答比较好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看你也没比我大多少,还在念书么?”
“没有,我父母死得早,我跟着二叔过日子。”
“我不会读书,我不是读书的料。”
“那你靠刷墙过日子?”
“没没,没有,我是个无业游民,就是你们经常说的街头小混混。”
这是我坦率的底线,说什么也不想告诉她我一个月前才刚从劳教所出来。
“哦,那到好。”
“好?好什么?”
她突然放下盛满大麦茶的塑料壶,安静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有些乱,但是不想让她看出来,只好也愣愣地看着她。
她的眉宇间有很多东西是我所无法了解的,但是,那些东西在我偶然照镜子的时候也曾经不小心看见过,它们也潜伏在我难以查明的五官深处,而我,也永远琢磨不透它们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意义。
她继续倒茶,直到即将漫溢为止。
“我父母也不在了,我最近刚休学,因为爷爷死了。”
我看看她,她的表情很平淡,但是却让我感到哀伤。
“看得出我是扫把星么?”
她突然问,表情很专注。
我摇摇头,不明白她的意思。
“谁跟我碰上谁就倒楣,你也一样,没摔死算你命大。”
“我爸妈就是生下我没多久出车祸死的,当时我也在车上,但是我没事,他们却死了,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初二那年,奶奶晚自习时来接我,半路上突发心脏病,救护车没到医院就断了气,一个月前,我爷爷好端端地在阳台上乘凉,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现在,终于剩下我一个人了,就我一个到也清净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仍然不懂。
“为了警告你。”
她很认真,但是,有种说不出的凄凉隐藏在她的表情后面,仿佛预示着她内心所想的一切。
“警告你最好不要太听我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把你的小命给掳走了。”
两个人相视片刻,不语。
然后同时笑出来。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呆住了,静静打量我的面孔,就像一只突然受到猎人惊吓又被猎人的保护所感动的柔弱的小白兔。
“那你要对我负责。”
“负责?负什么责?”
“你看了我的身体,就必须对我负责?”
“啊?这……”
“别害怕,我又没叫你干什么,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行。”
“什么事?”
“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每天到我窗外刷一次墙。”
“为什么?”
“我喜欢看你吊在半空的样子。”
“原来你还有这种嗜好……”
“隔着窗户,在没有人的下午,一个陌生的少年从天而降……这不是很有趣么?”
她又开始喃喃自语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她刚才的话,蓦然追问:
“你说,在你离开之前,你要离开这里了么?你要去哪里啊?”
她背过身去,不看我,然后,独自走到我们碰面的窗台边上,眺望看不见的远方。
4
1987年 7月26日 多云 或者会下雨
就这样,我又一次重操就业干起了小偷的勾当,整整六天,天天准时从居委会的旧仓库里偷出工具打扮成油漆匠,倒挂在66号202的窗外。
我很乐于做这件事,尽管那让我的腰每天都疼得直不起来,乌青一个接一个地从布满勒痕的皮肤底下冒出来。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因为自从我对她负起那场“意外”的责任开始,她就再也没重提要离开这里的这件事,渐渐地我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只是很单纯地享受着一边刷墙一边和她隔着窗户聊天的乐趣。
在一起的时间总是那么悠哉宁静,无人知晓。
炎热的小区在晌午时分是比深夜还要寂静的,能睡的都睡了,不能睡的也晕了,只有我们,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在一扇朝南的太阳大到不行的窗户内外用一种无人知晓的纳凉般的心情悠闲地虚度着我们的光阴。
感觉很熟悉,从未有过的那种,对父母、亲人、乃至任何一个曾经认识过的人都不曾有过。
起先的话题总是漫无目的的,尔后,她忽然对我小混混的生涯产生出浓厚的兴趣来。对于就快要满十八足岁的自己迄今为止从来没干过一件长脸的事我始终保持着无所畏惧的心态,可是,当她真的问起那些事时,那种感觉却比死去的父母从坟墓中爬起来审判我还要痛苦百倍。
可是,她期待我开口的眼神看上去那么地透彻干净,找不到丝毫蕴藏嘲辱的玄机。
相信我,我仅仅,只是好奇。
她就一直这么鼓励地看着我,等待我把先前那个无所畏惧的家伙找回来。
于是,我不再害怕,那种原本应该在她面前无地自容的卑贱仿佛在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就被她善良的热浪湮没了。我开始告诉她那些有关我的事情:我第一次逃学那天干了些什么,我第一次偷东西是因为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取笑我是个连包烟都买不起的穷小子,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小道江湖之间微不足道的恩恩怨怨。她听得津津有味,时而专注、时而讶异、时而高声欢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事,因为那实在是些无赖又胡闹到极点的事情,可是,她却听得那么过瘾笑得如此开心,仿佛,我是一个仗义勇为豪气冲天的英雄,所有的故事里,只有我是主角,轮到丑陋的情节时就是别的什么配角的事了,跟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这样,说着说着,最后连我自己都有点沾沾自喜起来。
天知道,我有多喜欢看她对我那样欢笑。
那善良的,对一个失足少年宽容到近乎宠爱的欢笑。
我从不曾想过要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辩解,可是,在她眼里我看到的竟然是一个我从不认识的,胆大妄为的少年,以及,那少年身上始终被我忽略了的数不尽的孩子气的美好。
我不停地,不停地说,把能告诉她的细节全部一一呈现,好像这便是我今生今世对某个人倾诉的唯一机会似的,我要一次性把它用光,用到最最最后的那一刻,就好像,我这一生所有的快乐都是为了她此刻的欢笑而存在的。
我说,我说,说到想要笑,笑了,又忽然想哭。
她依旧把整个身体倾倒下来,仿佛为了要更清楚地听见我所说的每个字,数不清有多少次,我不得不放下刷子,撇去干扰我视线的黑色长发,每每这个时候,她便突然把整个头仰起来,让发丝从我胸前一路飘过湿漉漉的额顶。
或许,她真的是个在盛夏的午睡中永远清醒不过来的特无聊的女孩。
但是,却有着让我无比臣服的力量。
这是任何人,甚至主宰我命运的神灵,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你呢?除了是个扫把星,喜欢看人家吊在窗户外面刷油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或者,特异功能?”
在又一阵狂笑结束之后,我忍不住反过来问她。
“我?嗯……我有天眼!”
“天眼?什么意思?”
“我能预知未来,从一个人的现在准确无误地看到他的未来。”
我暗自思忖,忽然联想到,她说这话的意思是否暗示着她曾经预料到她的亲人们会相继离开她的事实呢?
说完这句,她就突然不说话了。
我没有继续往下想,也不能这样想,只是,默默凝视她不再关注在我身上的眉目,然后,和她一起懒洋洋地将自己安置在夕阳西下的暖光中。
“你信不信?我的预感是很准的,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错。”
“所以,他们说我是个很邪乎的人。”
“他们?谁是他们?”
“福利院的人。”
“爷爷好像知道自己就快不行了,临走之前把我所有的资料都移交给了福利院,他一走,我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了,离成年的日子还有一年多,他总得给我找个监护人不是么?”
“那,你现在就一个人过?”
“嗯,一个人,不过,这种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对外国夫妇领养了我,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忽然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刚才,始终盘旋在窗户、长发、油漆、绳索,以及,热火朝天大太阳底下的那些没有尽头的快乐,忽然间,全都消失不见了。
两个人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觉得腰间悬空的承受力就快支持不住了,眼看,要断。
“……很快么……”
“很快是多快呢?……”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又不自觉地在嚅动。
她悄然收回流放的目光,无比讶异地注视我的眼睛。
终于,我也把头抬了起来。
5
1987年 8月4日 阴天 有时有雨
雨天。
我的皮肤骚痒难耐。
居委会的老太婆叨叨了整整一个早上,问我为什么66号202窗外的那堵墙的颜色会那么深?所有的大楼,就那一块地方的颜色和其他楼不一样,问我要怎么解决这影响到小区容貌整齐的严重问题!
“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抖着我的右脚,嗑着我的手指甲,拼命摇晃我的脑袋。
“什么叫没办法?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漆都干了,如果再把它刷白了就更难看。”
“我说你…你你没事刷那么多遍干嘛,啊?这不是给我添乱么?”
“您老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哦,人画家随便泼几滩颜料就叫抽象,我不过是把颜色反复涂得更深更均匀一点,您就不能当一回景观来欣赏?”
老太婆嘴里顿时发出各种古怪的惊叹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我马上抓起桌上的扇子把她当刚点着的煤球炉扇,眼看这就要口吐白沫了,那滑稽的表情让我完全失去继续胡诌下去的热情。
“那您老先歇着,我再去看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好不好?”
她挥挥手,话都说不出来。
“气死我了,真正被这个小赤佬气死……”
我暗自偷笑,脚底一滑就溜了号。
我摊开十个手指数日子。
翻过来覆过去。
都过去十来天了,她还是不肯告诉我她到底什么时候会走。
我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患得患失地过着孤枕难眠的鬼日子。
十五。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数字。直至今天,我和她已经足足相处了十五天,现在,我的秘密被那块颜色触目的墙壁给揭发了,我已经不能再吊在半空和她幽会,可是,我必须去找她,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哪怕顺着水管爬上二楼的窗台,哪怕爬到一半我就会活活摔死,我也认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仅仅只是十五天,十五天而已,我却已经在每一个24小时往返中那个固定时辰的漩涡里阵亡了。
我是那么想念她,想念到如果再也没有了那个与她短暂相处的时辰我会马上死掉的地步。
可奇怪的是,我对她,完全没有占有欲。
我没有邪念。
没有那种面对她的时候,就想对她干嘛干嘛的冲动。
甚至,她曾一度意外裸露在我眼中的身体也全然模糊了起来。
我只是,单纯地被一种奇特的想念主宰了。
更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无法从这样的想念中遁逃出来,我被困住了,如同她是吐丝的蚕,我是成型的茧,只要她不停地吐,我便再也无法自由地动弹,最终,我们都会静止。
那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并非肉体,而是精神。
我揣摩到了她可能会死在我蛹里的事实。
抑或,我因她而落地成茧。
又或者,那不是死亡,而是,永久的沉睡。
她会永远在我的茧里长眠不醒,因此再也不能变成那只自由翱翔的蝴蝶。
我会永远背负着日渐风化的壳,因此再也不能修炼成形状各异的自己。
想到这里,我突然哭了。
发疯似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奔跑。
风嗖嗖地吹过我的耳边,将我呼之欲出的热汗弹起,我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为什么会徒升一种没有头也没有尾的生离死别般的痛。
她不是我人生里的人,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可能是。
我们,只是两个在1987的夏天,偶然遭遇的孩子。
可是,痛楚越来越压迫我的心脏,让我随时预备着狠狠地栽倒。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一个还不曾体尝过爱情是什么滋味的无知少年,却在数日间变成一个疯了、爱了、给了、痛了、最后仍然一无所有的男人。
她又在想什么呢?
即将就此销声匿迹的那个女孩,她此时此刻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我的疯跑兜过好大一个圈,最终于落在了老地方。
她不在窗口。
大约过了五分钟,铁门开了。
“你来啦。”
她从门缝里钻出来,第一次那么正式地,面对面站在我跟前。
很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样子。
我聚精会神,一点小差也不敢开,我必须仔细看清楚她,当她的长发不再阻挡我的视线,当她的眼光不再逃离渴望与我面对面的安分,她便是真正的她,那个这一瞬间给我毕生烙印的人。
可是,那条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纯白连衣裙刺伤了我,徒劳的难受重又回到我的脑海。
长发、白衣、盈盈浅笑。
这是在履行最后的告别仪式么?
她用了一种最简明扼要的方式回答了我的问题:
对,我就是那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记得的,最无聊最孤独的女孩子,所以,请你可千万不要忘记我。
我抹了一把汗,顺便擦掉那些她并未觉察的可笑眼泪。
“要走啦?”
“你怎么知道?”
“你穿成这样白痴都晓得了。”
“哦,是么?”
她有点尴尬地低头打量自己。
喉结处有股哽咽在翻滚,我硬是咕噜一声把它吞下去。
“我今天不能漆墙了。”
“为什么?”
“被居委会的老太婆发现了。”
“可不是,这墙已经被我们搞得够难看的了,已经没法再继续搞下去了,呵呵呵!”
她又欢笑起来,这次很文雅地掩了嘴,仿佛要让我故意看到她异常可爱的那一面。
“我明天就走了。”
“我猜就是,所以特地来给你送行啦,东西都收拾好了?”
“都收拾好了。”
“路上小心点,一个人出门在外的,哎对了,你到底去哪个国家呀?”
“瑞士。”
“瑞士说的是什么话来着?”
“我养父母是华侨,人很好,就是没孩子,他们英文、中文都会说,我一到那里就会继续念书,虽然对他们印象一般,但总比一个人在这里好你说是不是?”
“哦,那那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
“……”
“我想和你去小花园坐坐,你还有时间么?”
“为什么没有?我今天不用刷墙,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她笑了,笑得很惬意很满足。
于是,我们第一次像两个为了彼此喜欢的人特意打扮好了去赴约的小情人那样,肩并肩地,朝着标准的约会地点走去。
我从来没有真的在小区的花园里坐过。
那是一个很茂盛的庭院,没有繁花似锦的奢靡,只有郁郁葱葱的明朗。
我和她很安静地坐在仅此一只的旧石凳上,感到屁股凉凉的很舒服,清晨的细雨在石凳上并没有留下多少潮濡的痕迹,我们都有些担心它还会在不适时宜的时候突然下起来,如果真这样,我们也不会离开,在一切终归要消蚀之前,永远也不离开。
“我说,我甚至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忍不住还是说了这样的话,有点矫情,好像念台词似的。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么?”
她反问我,我摇摇头。
说些什么,我在她沉默的间隙祈祷,请求你再说些什么,哪怕无关紧要的废话也可以,我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机会,来记住你的声音。
“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哦?什么话?好的还是坏的。”
“有好有坏。”
“是关于我的未来么?”
她顿时惊诧。
“你怎么知道?”
我笑笑:“你不是说能预测别人的未来么?”
“我说你就信呀?”
“为什么不信呢?”
我坦然面对她。
“告诉我,你看到了些什么?”
她又一次将眼光放逐到我揣测不出目的地的地方。
“我看见你十年后的样子了,很高大很成熟,留着络腮胡子。我走了以后,你就不再江湖上混了,可能,会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你并不在乎自己想干什么,而只在乎自己能干什么……若干年以后,你会在一家汽车修理铺当学徒,到时候,你会认识一个人,一个即将影响你整个后半生的人……而且……”
她忽然说不下去了。
“而且什么?”
“而且……你会和他的女儿结婚。”
我呆呆地看着她当真到近乎痴傻的表情,半晌,扑哧一声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拜托你另外编个版本好不好,这个太逊了,你看我像那种人么?像么?像么?”
“不管你像不像。”
她拦截了我夸张的语调。
“总之,这就是你的未来,我所能看到的你的未来。”
我输给她了,真的输给她。
“那好,就算是这样,你到说说看你的未来又如何呢?既然你有天眼,能看到别人,没理由看不到自己啊?”
她的脸色立刻暗沉下来。
我有些迷惑,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怎么?看不见呀?看不见就算了,算了。”
“不,我看见了。”
她慢慢地,很慢很慢地抬起了面孔。
就这样,我的眼睛和她重叠到了一起。
就是那短短的几分钟。
就是那几分钟的重叠,改变了我的一切。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不好的事。”
“不好,真的很不好。”
“因为,我看见,明天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
“那让我害怕,非常害怕。”
“为什么?”
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很沉很沉,怎样努力都托不起来。
“因为,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再喜欢一个人像现在喜欢你这样了。”
说到这里,她突然哭了。
泪水从眼球滑落的那一刻,我的心终于成了形,但在成形的同时却死了。
而她的,也紧随其后静止了下来。
很静很静,仿佛就这样在活着中永远地睡去了。
“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
她含着眼泪问我。
“就一下,一下就好。”
我没有哭,心如止水,一点想哭的头绪也没有。
我只是很顺从地握住她的手,把嘴唇迎了上去,轻轻地和她的重叠在一起,眼、唇、心统统都在一起了。
这个吻持续的时间大约只有四秒,只因我和她都还不太会接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感觉就像完成了一场翻云覆雨的做爱那样美满、富足。
我拉过她的肩膀,紧紧地,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离开这里。”
“嗯,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不再哭泣,不再对我有任何要求。
再也没有。
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让我抱着,从这天的黄昏一直坐到第二天的凌晨。
我仍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总之,在1987的那个夏天,我遇见了她,亲吻了她,拥抱了她,最后,离开了她。
不久,通过居委会某热心干部的推荐和担保,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得到了成年后的第一份职业,成为了早期为数不多的骑自行车的快递员,这份工一干就是四年,后来,又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直到我二叔退休那年,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修汽车的朋友,从此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
那个夏天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依然在城市四处过着游手好闲的逍遥日子,因此,几乎很快就把她所说的关于我未来的那些事抛在脑后了,直到十年后遇见我父亲的那日也没想起来。
但是,我还是为她做了一件事。
那是她离开一个月之后的一个很晴朗的早晨,我忽然非常想念她,于是,便拿上家伙撬开了仓库的门,再次把油漆时用过的绳索偷了出来。
当时,天刚蒙蒙亮,小区里一个人影也不见,当我再次滑到那堵墙上时,惊奇地发现她家的窗户还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但是,屋里已经全部清空,除了朝南的那扇,其他所有的门户也都早已关闭了。
我伸出脚把窗户开大,很容易就进去了。
我只想做一件事情,一件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事。
于是,我走到窗户边寻找,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角落。
然后,便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刀,一笔一划,尽可能不出错地刻下了那句话。
6
2005年 7月26日 黄昏 雨过天晴
“什么话?”
“这我不能告诉你,总得让我保留一个最后的秘密吧。”
“这就是你的故事?”
“是的。”
“全部?”
我点点头。
父亲很坦然地看着我,没有感怀,也不藏隐忧。
“其实,也就是一段年少的回忆,陈年往事,就像一张不舍得丢掉的照片。”
“但也就只是一张照片,仅此而已。”
“可是,我女儿她不理解,是么?”
那种平淡却依旧很遗憾的情绪让我再次不得不对他点头。
父亲不说话,举杯喝完最后一杯酒。
“不过,我理解。”
然后,忽然说道。
“你还爱着她么?那个1987年夏天的小女孩。”
“是的,我没法忘记,这是我唯一不能掌握的事,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你错了,她在你心里。”
“即使她已经死了,或者,你死了,她还是在你心里,永远,永远都在那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抹去,永远都不晓得……可悲的是,真正应该寻找答案的人却不寻找,而不该寻找答案的人却一直在寻找,最后,当她发现那根本就找不到时,也早已心力交瘁干涸枯槁了。”
父亲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仿佛连走完短短的回家的路都显得尤为困难。
“再见了,孩子。”
父亲抱住我的肩膀,我感到很放松,许多许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放松。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他当着我的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轻轻地,把它压在一只空啤酒瓶下面,然后,拿起桌边的雨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馄饨面馆。
我重新坐下来,从酒瓶下抽出那张照片,仔细端详。
是一张合影。
一张约莫很多年前,馄饨面馆的老板娘和父亲并肩站在一起的合影。
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有些青涩地靠着彼此的肩膀,但是,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鲜活那样动人……
黄昏的街道上,雨过天晴。
父亲独自远去的身影显得无比柔韧刚毅。
我想,他是在和我一起完成了对那场久违的迷情的告别。
这样的告别,没有任何忧伤。
因为,那将会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同样面对年老色衰的时刻,再也不会感到孤独。
入夜前夕,我独自追寻记忆的脚步,找到了1987年夏天,我曾居住过的那个地方。房子还是那时的房子,小区内也依旧回荡着最令人熟悉和怀恋的纳凉人的嬉笑声,一切都显得那么悠然安稳,让我得以细细重温那种缓慢的,如小桥流水般清澈言绵的幸福。
我还是来到了那扇熟悉的窗户下,闭上眼睛,想像着自己在这个时候,穿戴整齐地从屋顶悬空而下,无声无息地停留在那依旧深色突兀的墙壁前面。
此时此刻,透过那窗,还能看见些什么呢?
…… ……
…… ……
空无一人的屋子。
不大不小,看上去很干净很典雅。
夜风吹起窗帘的一角,一行不知何时刻上去的,歪歪扭妞的字隐约呈现在月色之下:
我想,我会一直这样爱你,直到……
1
2005年 7月26日 阴天 闷热
“你最好把帽子摘了。”
“天气很热,我的空调坏了。”
他拘窘地看了我一眼,再度把毛巾从身后小冰箱的冷冻库里拿出来。
我顺从地摘了帽子,妻子像机器人那样转过头来看一眼,有生锈的嘎吱声从她的脖子底下传过来。
“手续都办妥了,现在,只要各自在这儿签个字就行了。”
我停顿了一下才拿起桌上的水笔。
妻子没有犹豫,等我把笔拿稳时,她已经签完了。
“恭喜两位,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夫妻了。”
律师想绞毛巾里的水,又发现周围没有盛水的物件,只好暂且放到一边。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么?”
妻子谁也不看,摇摇头,然后,站起来。
“那…就这样了。”
我也站了起来。
外面一点阳光也没有,天气又闷又热,空气里的湿度很粘稠,估计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的前妻走在前面,并开始加快脚步。
“我说,你一定要这样么?”
我忍不住追上去问她,这是我一直很想知道的问题,但是,她从来就没有回答过我。
“你还是不肯说么?给我个理由,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
她还是不肯回过头来,不过,也不打算继续往前赶。
雷声从前方不远的地方传到我们停留的地区上方。
“以后,你也打算只爱她一个人么?”
“我是说,我们离婚以后。”
我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这就是你的理由?”
“她并不存在,她不是我人生里的人,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
“但是,却要跟着你一辈子。”
“对不起,我受不了这个,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忍受了。”
雷声变成霹雳从头顶呼啸而过。
前妻重新迈开脚步,这次,她走得飞快,好像被前路尽头的乌云吸了进去,就这么永远地消失在天边。
手机响起来,我大约知道是谁,虽然阵雨已经开始下了,我还是决定要冒雨和他见上一面。
“爸爸,是我,你已经到了,好,还是老地方,我马上就到。”
和父亲第一次面谈就是在那里。
小砂锅馄饨面的老板娘前年去世了,从那以后,父亲就不再去那里了。
我的父亲是我妻子的父亲,现在,我已经和他女儿不再有任何关系,于是,我们又可以恢复到初识时的样子,像亲生父子那样在馄饨面馆里头喝啤酒,只是,不能和以前一样喝得烂醉,因为,再也没有好心的老板娘叫车送我们回家了。
“你们最终还是分手了。”
父亲很平静,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我对他的愧疚。
“她嫁给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她,要和一个心里有着别的女人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他心里有着别的女人这件事,可惜,她最终还是没能做到,白白浪费了一段缘分。”
“她和她母亲一点也不像。”
“她像我,对人、对事都太执著,尤其是那些都已经过去的事,这是她的错,不是你的,你没有对不起她,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好女婿,我真替她惋惜。”
“你不要这样说,都是我不好,是我对她不够好,她才不要我的。”
父亲凝视我的眼睛。
许久,我们就只能这么凝视着而一句话也不说。
“还记得我们认识的那天么?”
“当然。”
“我还是觉得我的记性有问题,到你那里洗过那么多次车,怎么就从来没注意到你呢?”
“你问我会不会开车,我说会,你又问那你愿不愿意帮我开?我说好。”
父亲微笑。
“那是缘分。你和她,我和你,这都是缘分。有了缘分的人,是怎么也躲不开的,不管躲到哪里,总归还是要碰见的。”
雷雨越下越大。
店小二把冰镇啤酒端上了桌。
“这雨要下好一阵子了。”
“看样子是。”
“跟我说说你的故事。”
“你和她的故事。”
“你老婆,哦不,是你以前的老婆,只跟我说了一点点,就是她想答应你的求婚又不得不征求我意见的那天,现在,我想听你亲口说,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最起码得让我弄明白我女儿到底输给了谁?这个权利我总还有的。”
“说出来,怕你笑话。”
“为什么?”
“我是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偶然认识她的。”
“现在说起来就好像是前辈子的事,那天的天气和今天一样热,我一直盼着能下一场雨,可是,直到晌午也没看见一片乌云……”
2
1987年 7月17日 晴天 酷热
天气从未那么好过,太阳辣到抬头低头都睁不开眼,树都被晒傻了,找不见半块阴凉地。
当时,我刚从少年劳教中心放出来,那是我第五次重获自由,出来前,我把装着上等香烟的盒子包进防水的牛皮纸,藏到劳教中心男厕所的水箱里,以备下次再进去的时候还能有烟抽。
我没想到这次那么快就会被放出来,我和阿三头那伙人差点把吴家的杂货铺给烧了,是他儿子先打了我的人,我放火烧他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也只是吓唬吓唬,没想到真会烧起来。警察赶到时,能溜的都溜了,我因为忙着救火居然把逃跑那么重要的事给忘了,结果就这样,把我给抓了进去。
出来的头一个礼拜,二叔像猫看老鼠似地看着我,不敢让我踏出门槛半步,后来,没了耐性,就跑去居委会问有什么活可以给我干,正好小区的外墙要重新粉刷,那年夏天,我就因此而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个油漆工人。
油漆的活本来就不好干,尤其是要长时间吊在半空中,我又不是杂技演员,没学过那种功夫。天气一天胜一天地热,碰到有阴影的墙还好,至少不必惨遭太阳的暴晒,可是,那天,倒楣的那一天,我吊在二楼一家朝南窗户外面的时候,几乎觉得自己就快要死掉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点预兆都没有。
其实,哪怕只要有那么一点动静,我想我就会立即放松绳子爬下去,而不至于造成那种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误会里。
她在那里干什么呢?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一点声息也没有,真是活见鬼了。
我很小心地放下绳子,半空状态让我丝毫没有安全感。接着,我在二楼朝南的一家敞开的窗户前面停下,正儿八经地用刷子沾上油漆开始涂抹,这种情况下,要我不对窗户里探头探脑是不可能的,我发誓,那不是我小偷习性的卷土重来,只是,除了油漆、太阳,我的眼睛就只能面对那扇窗子,而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供停留。
那是一间明显有钱人家的屋子,可惜,酷热的下午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很为这家主人的安全担忧,可是,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开始哼歌,很轻很轻地哼,这时候,事情发生了,等我反应过来时,只能大叫一声,然后手上的绳子跟着一松,连人带桶整个掉了下去。
那个睡眼朦胧的女孩不晓得是从屋子的哪个房间里冒出来的。她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走到朝南的窗户前面,一边伸懒腰一边开始脱衣服,等到只剩下一条白色小裤衩的时候,被我的迎面而来的尖叫惊醒,不过,她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谁,我就已经坐在一楼的水泥地上了。
这导致我发出了另一声恐怖的哀号,不仅仅因为我的屁股开了花,还因为我那开了花的屁股是坐在木炭烤熟了的铁板上面,晌午的太阳本来就把我的脑袋晒得又昏又胀,屁股这一家伙更是让我眼冒金星小鸟乱飞。
于是,一溜串的脏话就劈里啪啦从嘴里倒出来了,这怪不得我,那对我来说真的和打嗝放屁没什么两样。
我琢磨着还能不能自己从地上爬起来,这时,公寓底楼的铁门嘎吱敞开一条缝,一张眼屎还没完全擦干净却依旧显得相当清秀的脸蛋从那里面探出来。
“我说,你…还好吧?”
我彻底傻了。
是刚才那个对着我脱衣服的女孩。
我想站起来,然后撒腿就跑,满身的油漆并不能为我证明什么,刚才那一幕是毫无疑问的流氓行为,说给谁听谁也不会相信。
可是,我爬不起来,屁股疼得好像散了架似的。
不说话,连看也不能看,虽然,她已经把衣服穿好了,而刚才我也确实没把她的上半身看清楚,问题是我也没想看她的上半身,只是,被她吓着了。
“说话呀?要不要我打电话送你去医院?”
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她索性走了出来,蹲下身子瞪着我的眼睛看。
“难道……变白痴了?”
我忽地一声从地上爬起来。
从来没人敢骂我是白痴,完了完了,她可把我惹火了,这下她死定了。
“说什么说什么!是你站在窗户前面对着我脱衣服,害我差点没摔死,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到底有没有脑子啊?大白天的站在窗口脱衣服,这这这叫什么事嘛……”
“二楼摔不死人的,顶多半身不遂。”
她平淡地插嘴。
“你!!……你个臭……”
“臭什么?我很臭么?”
她立刻抬起胳膊嗅。
“不会啊……我刚刚才洗过澡…奇怪,怎么会臭呢……”
我快昏了,我这就要昏。
这时,她突然想起刚才好像确实发生过什么事来着。
“你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什么了我。”
“我的身体啊。”
“没有,绝对没有,你你你那不是还穿着一条小裤衩呢么?”
“还是看见了……”
她喃喃自语地总结道。
然后,歪头想了一想,继续看着我,说:
“看见就看见呗,也没什么大不了了,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小,那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是看见你脱衣服,还是从二楼摔下来?”
她又想了一想,表情挺认真,这时候,我发现她的嘴唇很好看,眼睛也不错,就是眼角那颗小眼屎怎么瞧怎么别扭。
“现在看起来你是没什么事,我是说,那桶油漆怎么办?还有你身上这些,不赶快洗就洗不掉了。”
难道她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在想什么?”
她很警惕地用手指戳戳我意志不坚的肩胛。
“没,没想什么呀,我到没事,可我今天的活怎么办,总得干完那。”
“要不你再去弄点漆来,我跟你一起刷,你从外面刷,我从里面刷。”
终于松了口气,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万一我找漆的时候她打110把我当流氓给抓了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那你在这等着,不许跑掉,知道么?我马上就回来。”
“不许走啊,你可别再玩我了啊!”
我一边端着屁股跑一边回头大叫。
她站起来,两手交叉在胸,远远望去好像摆在门前的一个白玉雕琢的玩偶。
“要跑也是你跑!偷看我脱衣服的是你又不是我!!”
她故意叫得整栋楼的人都听见,致使我在半道上又狠狠摔了一跟头。
她的笑声更响亮了,我的头、胸、肚子屁股膝盖大腿没有一处不在疼,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心里却觉得说不出的好笑。
3
1987年 7月20日 晴天 还是热
7月17日的那个下午过得极其漫长。
她本来要和我换个位置再刷刷,说很想尝尝吊在半空的感觉,我没敢答应,这个下午已经够乱的了,再出什么纰漏,我就真的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
刷完时,已近黄昏,太阳慢慢地从外墙的阴影中褪去。
“我觉得颜色不够均匀。”
我用一只脚将垂悬的绳子离墙踢开一段距离,假装审视。
她把刷子丢进油漆桶,险些甩到我的肚皮上。
“哦?为什么?”
她看看自己的手,上面沾满了油漆,其实,她的脸上也有,我只是不方便讲而已。她一边有意无意地和我答话,一边继续研究手掌正反面的油漆,看着看着居然很满足地笑起来。
“我看咱们还得再重复刷几遍才行。”
“再说吧,我现在要去洗澡了。”
她不再理我,自顾自从窗台上爬下去。
我顿感无趣,只好把绳子收回原位,傻傻地看着她又回到最初发现我的位置上。她几乎立刻就转身要往浴室去了,可是,走了一半,忽然又转回头来看我。
“喂,你还吊在那里干什么?难道还想偷看我洗澡不成?”
我立刻抓起搁在她家窗台外面的油漆桶,滋溜一声滑到底。
正收拾残局的当口,忽听她的声音再度从二楼传下来:
“喂!你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刷呀?喂!喂!”
我头也不回打算就这么走了,可是,她还在一个劲地嚷嚷。
我琢磨着她肯定是个特无聊的女人。
“过两天,等我把前面那栋刷完了再说!”
我丢下这句话的时候也还是没有回头。
再遇见她是三天后的上午,手头的油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但我还是将油漆工的服装穿戴整齐,并且把那些必备的行头全部偷了出来。
我答应她过两天要再来漆那堵墙的,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如果,如果她因为我没去,又告我耍流氓怎么办?
那是个很馨宁的上午,沿着人工河道一路走去,四周的鲜花、树木、青草、绿荫都好像是活人装扮的道具,贼溜溜地踮起脚尖或跟在我后头,或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向我爱你拢,仿佛靠近了就能听见我心里的秘密似的。我依旧哼着我的歌,脚步也越踏越轻快,走近她家时我的声音更响了,迸发出那种高昂的走调的雄伟力量。她就趴在老地方等着我,我确定她是故意等我来着,因为她把长头发全部放到窗子外面来让它们像拉面师傅手里的细面条似地迎风招展,和前两天不同,那天她穿了件很体面的洋装,前半身几乎全部送出了窗外,仿佛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自己看见那扇窗户的霎那,隐藏在愚钝的十八岁少年心底所有的自作多情都被呼唤了起来,那种由衷的痴心妄想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幸福,甚至,在还没有从屋顶滑落到她面前时就已经飘在空中了。
我在云端看她,她像一个化身为人的天使。
只有我能看见她的翅膀,只有我。
“喂!我来了。”
我站在底楼仰头叫道。
她先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然后漫不经心地低头俯瞰。
我离她不近,但是,却能看见她脸上的表情好像一只在青苔上停留了24个时辰的蜗牛那么懒散。
“今天要不要跟我一起漆啊?”
我继续问她。
她不说话。
我觉得无趣,于是自己行动起来。
“我说!”
她终于开口了。
“你能不能先不要漆?”
“不漆?不漆干什么?”
“上来跟我聊聊天,行么?”
我低下头,心里怦怦怦跳了几个来回,迅速冷静下来。可我的手却一直在腰间粗糙的绳子上磨擦,直到发现已经搓出一堆碎皮子来。
“那那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一起带上来啊,反正你还是要漆的不是么?你按一下202的门铃,我帮你开门。”
我不打算磨蹭,于是就这样顺利地进了她的屋子,那间我已经窥视了很久也基本摸清底细的有钱家的屋子。
其实,装潢也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好。
她的家不大不小,看上去很干净很典雅,和我那离了婚的二叔的乱窝窝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也难怪,家里就我和他两个男人,谁空谁收拾,没空就不收拾,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她说刚好冰了解渴的大麦茶,要我在客厅里坐一下,这就端出来。
我觉得别扭,这屋子的气场跟我不合,坐哪里都不太合适,所以就一直站着。她觉得奇怪,并且对我这种行为表示鄙视,让我觉得自己更加猥琐。
“叫你坐你就坐,还嫌我的椅子脏么?”
“哦。”
我坐了下来,身上的绳索发出咣啷啷的声响,她并没有强迫我把那些累赘解下来,这让我感到舒适的安慰。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看你不像油漆工人。”
她语气变和缓了,金黄色的大麦茶沿着玻璃徐徐倒入。
这个问题很复杂,该怎么回答比较好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看你也没比我大多少,还在念书么?”
“没有,我父母死得早,我跟着二叔过日子。”
“我不会读书,我不是读书的料。”
“那你靠刷墙过日子?”
“没没,没有,我是个无业游民,就是你们经常说的街头小混混。”
这是我坦率的底线,说什么也不想告诉她我一个月前才刚从劳教所出来。
“哦,那到好。”
“好?好什么?”
她突然放下盛满大麦茶的塑料壶,安静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有些乱,但是不想让她看出来,只好也愣愣地看着她。
她的眉宇间有很多东西是我所无法了解的,但是,那些东西在我偶然照镜子的时候也曾经不小心看见过,它们也潜伏在我难以查明的五官深处,而我,也永远琢磨不透它们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意义。
她继续倒茶,直到即将漫溢为止。
“我父母也不在了,我最近刚休学,因为爷爷死了。”
我看看她,她的表情很平淡,但是却让我感到哀伤。
“看得出我是扫把星么?”
她突然问,表情很专注。
我摇摇头,不明白她的意思。
“谁跟我碰上谁就倒楣,你也一样,没摔死算你命大。”
“我爸妈就是生下我没多久出车祸死的,当时我也在车上,但是我没事,他们却死了,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初二那年,奶奶晚自习时来接我,半路上突发心脏病,救护车没到医院就断了气,一个月前,我爷爷好端端地在阳台上乘凉,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现在,终于剩下我一个人了,就我一个到也清净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仍然不懂。
“为了警告你。”
她很认真,但是,有种说不出的凄凉隐藏在她的表情后面,仿佛预示着她内心所想的一切。
“警告你最好不要太听我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把你的小命给掳走了。”
两个人相视片刻,不语。
然后同时笑出来。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呆住了,静静打量我的面孔,就像一只突然受到猎人惊吓又被猎人的保护所感动的柔弱的小白兔。
“那你要对我负责。”
“负责?负什么责?”
“你看了我的身体,就必须对我负责?”
“啊?这……”
“别害怕,我又没叫你干什么,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行。”
“什么事?”
“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每天到我窗外刷一次墙。”
“为什么?”
“我喜欢看你吊在半空的样子。”
“原来你还有这种嗜好……”
“隔着窗户,在没有人的下午,一个陌生的少年从天而降……这不是很有趣么?”
她又开始喃喃自语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她刚才的话,蓦然追问:
“你说,在你离开之前,你要离开这里了么?你要去哪里啊?”
她背过身去,不看我,然后,独自走到我们碰面的窗台边上,眺望看不见的远方。
4
1987年 7月26日 多云 或者会下雨
就这样,我又一次重操就业干起了小偷的勾当,整整六天,天天准时从居委会的旧仓库里偷出工具打扮成油漆匠,倒挂在66号202的窗外。
我很乐于做这件事,尽管那让我的腰每天都疼得直不起来,乌青一个接一个地从布满勒痕的皮肤底下冒出来。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因为自从我对她负起那场“意外”的责任开始,她就再也没重提要离开这里的这件事,渐渐地我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只是很单纯地享受着一边刷墙一边和她隔着窗户聊天的乐趣。
在一起的时间总是那么悠哉宁静,无人知晓。
炎热的小区在晌午时分是比深夜还要寂静的,能睡的都睡了,不能睡的也晕了,只有我们,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在一扇朝南的太阳大到不行的窗户内外用一种无人知晓的纳凉般的心情悠闲地虚度着我们的光阴。
感觉很熟悉,从未有过的那种,对父母、亲人、乃至任何一个曾经认识过的人都不曾有过。
起先的话题总是漫无目的的,尔后,她忽然对我小混混的生涯产生出浓厚的兴趣来。对于就快要满十八足岁的自己迄今为止从来没干过一件长脸的事我始终保持着无所畏惧的心态,可是,当她真的问起那些事时,那种感觉却比死去的父母从坟墓中爬起来审判我还要痛苦百倍。
可是,她期待我开口的眼神看上去那么地透彻干净,找不到丝毫蕴藏嘲辱的玄机。
相信我,我仅仅,只是好奇。
她就一直这么鼓励地看着我,等待我把先前那个无所畏惧的家伙找回来。
于是,我不再害怕,那种原本应该在她面前无地自容的卑贱仿佛在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就被她善良的热浪湮没了。我开始告诉她那些有关我的事情:我第一次逃学那天干了些什么,我第一次偷东西是因为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取笑我是个连包烟都买不起的穷小子,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小道江湖之间微不足道的恩恩怨怨。她听得津津有味,时而专注、时而讶异、时而高声欢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事,因为那实在是些无赖又胡闹到极点的事情,可是,她却听得那么过瘾笑得如此开心,仿佛,我是一个仗义勇为豪气冲天的英雄,所有的故事里,只有我是主角,轮到丑陋的情节时就是别的什么配角的事了,跟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这样,说着说着,最后连我自己都有点沾沾自喜起来。
天知道,我有多喜欢看她对我那样欢笑。
那善良的,对一个失足少年宽容到近乎宠爱的欢笑。
我从不曾想过要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辩解,可是,在她眼里我看到的竟然是一个我从不认识的,胆大妄为的少年,以及,那少年身上始终被我忽略了的数不尽的孩子气的美好。
我不停地,不停地说,把能告诉她的细节全部一一呈现,好像这便是我今生今世对某个人倾诉的唯一机会似的,我要一次性把它用光,用到最最最后的那一刻,就好像,我这一生所有的快乐都是为了她此刻的欢笑而存在的。
我说,我说,说到想要笑,笑了,又忽然想哭。
她依旧把整个身体倾倒下来,仿佛为了要更清楚地听见我所说的每个字,数不清有多少次,我不得不放下刷子,撇去干扰我视线的黑色长发,每每这个时候,她便突然把整个头仰起来,让发丝从我胸前一路飘过湿漉漉的额顶。
或许,她真的是个在盛夏的午睡中永远清醒不过来的特无聊的女孩。
但是,却有着让我无比臣服的力量。
这是任何人,甚至主宰我命运的神灵,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你呢?除了是个扫把星,喜欢看人家吊在窗户外面刷油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或者,特异功能?”
在又一阵狂笑结束之后,我忍不住反过来问她。
“我?嗯……我有天眼!”
“天眼?什么意思?”
“我能预知未来,从一个人的现在准确无误地看到他的未来。”
我暗自思忖,忽然联想到,她说这话的意思是否暗示着她曾经预料到她的亲人们会相继离开她的事实呢?
说完这句,她就突然不说话了。
我没有继续往下想,也不能这样想,只是,默默凝视她不再关注在我身上的眉目,然后,和她一起懒洋洋地将自己安置在夕阳西下的暖光中。
“你信不信?我的预感是很准的,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错。”
“所以,他们说我是个很邪乎的人。”
“他们?谁是他们?”
“福利院的人。”
“爷爷好像知道自己就快不行了,临走之前把我所有的资料都移交给了福利院,他一走,我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了,离成年的日子还有一年多,他总得给我找个监护人不是么?”
“那,你现在就一个人过?”
“嗯,一个人,不过,这种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对外国夫妇领养了我,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忽然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刚才,始终盘旋在窗户、长发、油漆、绳索,以及,热火朝天大太阳底下的那些没有尽头的快乐,忽然间,全都消失不见了。
两个人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觉得腰间悬空的承受力就快支持不住了,眼看,要断。
“……很快么……”
“很快是多快呢?……”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又不自觉地在嚅动。
她悄然收回流放的目光,无比讶异地注视我的眼睛。
终于,我也把头抬了起来。
5
1987年 8月4日 阴天 有时有雨
雨天。
我的皮肤骚痒难耐。
居委会的老太婆叨叨了整整一个早上,问我为什么66号202窗外的那堵墙的颜色会那么深?所有的大楼,就那一块地方的颜色和其他楼不一样,问我要怎么解决这影响到小区容貌整齐的严重问题!
“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抖着我的右脚,嗑着我的手指甲,拼命摇晃我的脑袋。
“什么叫没办法?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漆都干了,如果再把它刷白了就更难看。”
“我说你…你你没事刷那么多遍干嘛,啊?这不是给我添乱么?”
“您老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哦,人画家随便泼几滩颜料就叫抽象,我不过是把颜色反复涂得更深更均匀一点,您就不能当一回景观来欣赏?”
老太婆嘴里顿时发出各种古怪的惊叹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我马上抓起桌上的扇子把她当刚点着的煤球炉扇,眼看这就要口吐白沫了,那滑稽的表情让我完全失去继续胡诌下去的热情。
“那您老先歇着,我再去看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好不好?”
她挥挥手,话都说不出来。
“气死我了,真正被这个小赤佬气死……”
我暗自偷笑,脚底一滑就溜了号。
我摊开十个手指数日子。
翻过来覆过去。
都过去十来天了,她还是不肯告诉我她到底什么时候会走。
我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患得患失地过着孤枕难眠的鬼日子。
十五。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数字。直至今天,我和她已经足足相处了十五天,现在,我的秘密被那块颜色触目的墙壁给揭发了,我已经不能再吊在半空和她幽会,可是,我必须去找她,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哪怕顺着水管爬上二楼的窗台,哪怕爬到一半我就会活活摔死,我也认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仅仅只是十五天,十五天而已,我却已经在每一个24小时往返中那个固定时辰的漩涡里阵亡了。
我是那么想念她,想念到如果再也没有了那个与她短暂相处的时辰我会马上死掉的地步。
可奇怪的是,我对她,完全没有占有欲。
我没有邪念。
没有那种面对她的时候,就想对她干嘛干嘛的冲动。
甚至,她曾一度意外裸露在我眼中的身体也全然模糊了起来。
我只是,单纯地被一种奇特的想念主宰了。
更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无法从这样的想念中遁逃出来,我被困住了,如同她是吐丝的蚕,我是成型的茧,只要她不停地吐,我便再也无法自由地动弹,最终,我们都会静止。
那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并非肉体,而是精神。
我揣摩到了她可能会死在我蛹里的事实。
抑或,我因她而落地成茧。
又或者,那不是死亡,而是,永久的沉睡。
她会永远在我的茧里长眠不醒,因此再也不能变成那只自由翱翔的蝴蝶。
我会永远背负着日渐风化的壳,因此再也不能修炼成形状各异的自己。
想到这里,我突然哭了。
发疯似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奔跑。
风嗖嗖地吹过我的耳边,将我呼之欲出的热汗弹起,我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为什么会徒升一种没有头也没有尾的生离死别般的痛。
她不是我人生里的人,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可能是。
我们,只是两个在1987的夏天,偶然遭遇的孩子。
可是,痛楚越来越压迫我的心脏,让我随时预备着狠狠地栽倒。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一个还不曾体尝过爱情是什么滋味的无知少年,却在数日间变成一个疯了、爱了、给了、痛了、最后仍然一无所有的男人。
她又在想什么呢?
即将就此销声匿迹的那个女孩,她此时此刻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我的疯跑兜过好大一个圈,最终于落在了老地方。
她不在窗口。
大约过了五分钟,铁门开了。
“你来啦。”
她从门缝里钻出来,第一次那么正式地,面对面站在我跟前。
很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样子。
我聚精会神,一点小差也不敢开,我必须仔细看清楚她,当她的长发不再阻挡我的视线,当她的眼光不再逃离渴望与我面对面的安分,她便是真正的她,那个这一瞬间给我毕生烙印的人。
可是,那条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纯白连衣裙刺伤了我,徒劳的难受重又回到我的脑海。
长发、白衣、盈盈浅笑。
这是在履行最后的告别仪式么?
她用了一种最简明扼要的方式回答了我的问题:
对,我就是那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记得的,最无聊最孤独的女孩子,所以,请你可千万不要忘记我。
我抹了一把汗,顺便擦掉那些她并未觉察的可笑眼泪。
“要走啦?”
“你怎么知道?”
“你穿成这样白痴都晓得了。”
“哦,是么?”
她有点尴尬地低头打量自己。
喉结处有股哽咽在翻滚,我硬是咕噜一声把它吞下去。
“我今天不能漆墙了。”
“为什么?”
“被居委会的老太婆发现了。”
“可不是,这墙已经被我们搞得够难看的了,已经没法再继续搞下去了,呵呵呵!”
她又欢笑起来,这次很文雅地掩了嘴,仿佛要让我故意看到她异常可爱的那一面。
“我明天就走了。”
“我猜就是,所以特地来给你送行啦,东西都收拾好了?”
“都收拾好了。”
“路上小心点,一个人出门在外的,哎对了,你到底去哪个国家呀?”
“瑞士。”
“瑞士说的是什么话来着?”
“我养父母是华侨,人很好,就是没孩子,他们英文、中文都会说,我一到那里就会继续念书,虽然对他们印象一般,但总比一个人在这里好你说是不是?”
“哦,那那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
“……”
“我想和你去小花园坐坐,你还有时间么?”
“为什么没有?我今天不用刷墙,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她笑了,笑得很惬意很满足。
于是,我们第一次像两个为了彼此喜欢的人特意打扮好了去赴约的小情人那样,肩并肩地,朝着标准的约会地点走去。
我从来没有真的在小区的花园里坐过。
那是一个很茂盛的庭院,没有繁花似锦的奢靡,只有郁郁葱葱的明朗。
我和她很安静地坐在仅此一只的旧石凳上,感到屁股凉凉的很舒服,清晨的细雨在石凳上并没有留下多少潮濡的痕迹,我们都有些担心它还会在不适时宜的时候突然下起来,如果真这样,我们也不会离开,在一切终归要消蚀之前,永远也不离开。
“我说,我甚至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忍不住还是说了这样的话,有点矫情,好像念台词似的。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么?”
她反问我,我摇摇头。
说些什么,我在她沉默的间隙祈祷,请求你再说些什么,哪怕无关紧要的废话也可以,我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机会,来记住你的声音。
“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哦?什么话?好的还是坏的。”
“有好有坏。”
“是关于我的未来么?”
她顿时惊诧。
“你怎么知道?”
我笑笑:“你不是说能预测别人的未来么?”
“我说你就信呀?”
“为什么不信呢?”
我坦然面对她。
“告诉我,你看到了些什么?”
她又一次将眼光放逐到我揣测不出目的地的地方。
“我看见你十年后的样子了,很高大很成熟,留着络腮胡子。我走了以后,你就不再江湖上混了,可能,会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你并不在乎自己想干什么,而只在乎自己能干什么……若干年以后,你会在一家汽车修理铺当学徒,到时候,你会认识一个人,一个即将影响你整个后半生的人……而且……”
她忽然说不下去了。
“而且什么?”
“而且……你会和他的女儿结婚。”
我呆呆地看着她当真到近乎痴傻的表情,半晌,扑哧一声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拜托你另外编个版本好不好,这个太逊了,你看我像那种人么?像么?像么?”
“不管你像不像。”
她拦截了我夸张的语调。
“总之,这就是你的未来,我所能看到的你的未来。”
我输给她了,真的输给她。
“那好,就算是这样,你到说说看你的未来又如何呢?既然你有天眼,能看到别人,没理由看不到自己啊?”
她的脸色立刻暗沉下来。
我有些迷惑,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怎么?看不见呀?看不见就算了,算了。”
“不,我看见了。”
她慢慢地,很慢很慢地抬起了面孔。
就这样,我的眼睛和她重叠到了一起。
就是那短短的几分钟。
就是那几分钟的重叠,改变了我的一切。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不好的事。”
“不好,真的很不好。”
“因为,我看见,明天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
“那让我害怕,非常害怕。”
“为什么?”
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很沉很沉,怎样努力都托不起来。
“因为,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再喜欢一个人像现在喜欢你这样了。”
说到这里,她突然哭了。
泪水从眼球滑落的那一刻,我的心终于成了形,但在成形的同时却死了。
而她的,也紧随其后静止了下来。
很静很静,仿佛就这样在活着中永远地睡去了。
“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
她含着眼泪问我。
“就一下,一下就好。”
我没有哭,心如止水,一点想哭的头绪也没有。
我只是很顺从地握住她的手,把嘴唇迎了上去,轻轻地和她的重叠在一起,眼、唇、心统统都在一起了。
这个吻持续的时间大约只有四秒,只因我和她都还不太会接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感觉就像完成了一场翻云覆雨的做爱那样美满、富足。
我拉过她的肩膀,紧紧地,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离开这里。”
“嗯,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不再哭泣,不再对我有任何要求。
再也没有。
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让我抱着,从这天的黄昏一直坐到第二天的凌晨。
我仍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总之,在1987的那个夏天,我遇见了她,亲吻了她,拥抱了她,最后,离开了她。
不久,通过居委会某热心干部的推荐和担保,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得到了成年后的第一份职业,成为了早期为数不多的骑自行车的快递员,这份工一干就是四年,后来,又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直到我二叔退休那年,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修汽车的朋友,从此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
那个夏天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依然在城市四处过着游手好闲的逍遥日子,因此,几乎很快就把她所说的关于我未来的那些事抛在脑后了,直到十年后遇见我父亲的那日也没想起来。
但是,我还是为她做了一件事。
那是她离开一个月之后的一个很晴朗的早晨,我忽然非常想念她,于是,便拿上家伙撬开了仓库的门,再次把油漆时用过的绳索偷了出来。
当时,天刚蒙蒙亮,小区里一个人影也不见,当我再次滑到那堵墙上时,惊奇地发现她家的窗户还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但是,屋里已经全部清空,除了朝南的那扇,其他所有的门户也都早已关闭了。
我伸出脚把窗户开大,很容易就进去了。
我只想做一件事情,一件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事。
于是,我走到窗户边寻找,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角落。
然后,便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刀,一笔一划,尽可能不出错地刻下了那句话。
6
2005年 7月26日 黄昏 雨过天晴
“什么话?”
“这我不能告诉你,总得让我保留一个最后的秘密吧。”
“这就是你的故事?”
“是的。”
“全部?”
我点点头。
父亲很坦然地看着我,没有感怀,也不藏隐忧。
“其实,也就是一段年少的回忆,陈年往事,就像一张不舍得丢掉的照片。”
“但也就只是一张照片,仅此而已。”
“可是,我女儿她不理解,是么?”
那种平淡却依旧很遗憾的情绪让我再次不得不对他点头。
父亲不说话,举杯喝完最后一杯酒。
“不过,我理解。”
然后,忽然说道。
“你还爱着她么?那个1987年夏天的小女孩。”
“是的,我没法忘记,这是我唯一不能掌握的事,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你错了,她在你心里。”
“即使她已经死了,或者,你死了,她还是在你心里,永远,永远都在那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抹去,永远都不晓得……可悲的是,真正应该寻找答案的人却不寻找,而不该寻找答案的人却一直在寻找,最后,当她发现那根本就找不到时,也早已心力交瘁干涸枯槁了。”
父亲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仿佛连走完短短的回家的路都显得尤为困难。
“再见了,孩子。”
父亲抱住我的肩膀,我感到很放松,许多许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放松。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他当着我的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轻轻地,把它压在一只空啤酒瓶下面,然后,拿起桌边的雨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馄饨面馆。
我重新坐下来,从酒瓶下抽出那张照片,仔细端详。
是一张合影。
一张约莫很多年前,馄饨面馆的老板娘和父亲并肩站在一起的合影。
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有些青涩地靠着彼此的肩膀,但是,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鲜活那样动人……
黄昏的街道上,雨过天晴。
父亲独自远去的身影显得无比柔韧刚毅。
我想,他是在和我一起完成了对那场久违的迷情的告别。
这样的告别,没有任何忧伤。
因为,那将会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同样面对年老色衰的时刻,再也不会感到孤独。
入夜前夕,我独自追寻记忆的脚步,找到了1987年夏天,我曾居住过的那个地方。房子还是那时的房子,小区内也依旧回荡着最令人熟悉和怀恋的纳凉人的嬉笑声,一切都显得那么悠然安稳,让我得以细细重温那种缓慢的,如小桥流水般清澈言绵的幸福。
我还是来到了那扇熟悉的窗户下,闭上眼睛,想像着自己在这个时候,穿戴整齐地从屋顶悬空而下,无声无息地停留在那依旧深色突兀的墙壁前面。
此时此刻,透过那窗,还能看见些什么呢?
…… ……
…… ……
空无一人的屋子。
不大不小,看上去很干净很典雅。
夜风吹起窗帘的一角,一行不知何时刻上去的,歪歪扭妞的字隐约呈现在月色之下:
我想,我会一直这样爱你,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