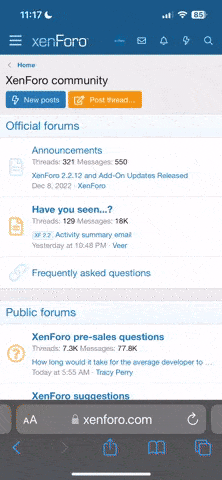Todo
初中二年级
- 注册
- 2005-08-26
- 帖子
- 470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1
――《非非》2001年第九卷流派专号重要文本研究
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就是战斗,语言就是价值,语言就是存在,语言就是时间和空间!
中国诗人必须立即从传统汉语意义上的反语言中突破出来,进行一个有血性中国人倾其一生而致力的伟大事业:重建新世纪诗歌和汉语言的价值体系!
――摘自2002年《诗歌札记》
在《非非》2001年第九卷非非流派专号上,有两个不仅对非非主义也对当下整个中国诗歌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常文本――周伦佑的《遁辞》和陈亚平的《诗歌白皮书》。我之所以说它们是两个极具重要的非常文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对诗歌语言价值体系的重建有着突破百年的领衔功能。在这里我们不必对中国的百年诗歌做一个工程浩大而繁杂的清理和清算,只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朦胧诗以及之后的先锋流派诗作一简要的回顾就可以开始进入本文研讨的主题。
80年代对中国诗歌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启蒙革命。随前朦胧诗破土而来的先锋实验写作出现了众多叛逆当时特定的体制文化和传统理性规范的诗歌群体,理论和作品呈鱼龙混杂之势翻搅于整个中国诗坛。此阶段的诗歌运动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1、诗歌整体凸出表现主义抽象化风格,艺术特征是拆除语言能指和所指的传统固定关系。这也是当时很时髦的一种反语言、反文化、反语法、反传统观。2、超现实主义的提升或者说淡化和还原,其艺术特征是抛弃已有的价值体系而走向客体和空无,这是另一种与崇高、传统道德和审美的进一步对抗和逆反。
一、反叛诗歌从出场到今天的变构的主要阶段性途径:
1、前朦胧诗为反叛诗歌的出场设定了必然的历史舞台
前朦胧诗的发生背景和动因:要对中国的前朦胧诗及之后的诗歌发展有一个明晰的定论,必须要对中国诗歌的文化大背景有一个简略的交代。从中国的诗歌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诗歌史就是一部国人理念的解放史。如果把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作是中国国民理念的第一次觉醒和生命体验的启蒙的话,那么一进入文化大革命,这种刚刚出现的对人的理念的解放就遭到了空前绝后的扼杀。文革十年,无论是中国的知识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长期处于文化黑洞的框桎中,传统观念和强权政治形成了一种铁的统治,人对人变得麻木不仁甚至不知道人之为何了。也就是说,人的物化已经使人成为物,人的异化也使人成为异族和异类了。某一天,当人们幡然醒悟突然得到解放并看清自己以前的蒙昧,那种惊异和激奋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乎,重获新生的人们都想着要把他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体验传达给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诗歌,因为只有诗歌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激情的宣泄来完成他们的表述。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国民心灵带来的阵痛以及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极不稳定的风雨政局,苏醒的中国文人在高压政治的强力压迫下,带着惴惴的心态像鼹鼠一样谨小慎微地审视和猜测着中国的未来。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昌行一时的前朦胧诗。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等。
前朦胧诗的文本特征和艺术特色:文本特征沿袭汉语分行自由体式。与传统意义上的汉语分行体诗不同的是前朦胧诗在分行断句上打破常规,比如不用标点符号断句,开始不讲究汉语规范语法。艺术特色重在突出诗意的朦胧。前面说过,这一时期的诗人们还处在审视和猜测阶段,他们害怕一不小心再次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文化黑洞和政治漩流。他们只能含糊其词地借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咕哝着他们的呓语。但从前朦胧诗的发展过程来看,前期大多是在说“我不”,总体意思是我不愿、不想、不要像以前那样过愚民和狱犯生活,不愿、不想、不要成为没有思想的动物。我是人,我不是动物。而后阶段,他们主要是在喊出“我要”,要过像人一样的生活,要有自己的思考,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抒自己想抒的情,我要成为本质意义上的我,我就是我自己。前朦胧诗为人的理念的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件事的发生必然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前朦胧诗时期正处在文革结束国门刚刚打开的特定历史时期。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研究人本身的各类学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给中国的前朦胧艺术家们带来了渐行渐绿的春意。这对国民的理念觉醒也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2、反叛诗歌的群体出场和深渊影响
反叛诗歌发生发展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伴随着前朦胧诗的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流派和各种风格的试验诗歌,这本身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诗人们激动且冲动地把“我不”和“我要”说出来以后,就会冷静下来仔细对诗歌艺术本身进行思考和探索。正因为如此,从84年开始,中国诗坛似乎一夜之间就涌现出了众多的先锋诗人和稀奇古怪的先锋流派。先锋反叛诗歌群体从九十年代开始日趋沉寂。原因之一是很多诗人受市场经济诱惑而投身于物质建设,另外,同前朦胧诗一样,反叛诗歌本身就是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当它完成任务之后必然又要走向新的变构。
反叛诗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内涵:反叛诗歌这一提法是针对传统诗歌的艺术观和价值观的,甚至也是针对前朦胧诗相对单一和单薄的艺术手法及审美内涵的。当这种反叛诗歌一出现,似乎因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无论是诗歌作品还是诗歌理论都远远地超越了诗人们当初的宗旨。反叛诗歌发展到最后,必然要对文化、社会、人类自身和诗歌自身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反思和质疑。我们从大展中异军突起的两个重要诗派的一些特征即可得到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86年的诗歌群体大展,四川的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名噪一时。非非主义的“前非非写作”时期(1986-1989),主张反文化、反价值、超文化、超语言,拆解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系,反抽象词语,甚至从反能指角度突围。(参见尹国均著《先锋实验》)。而莽汉主义则以亵渎一切的姿态出现在诗坛。研究者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先锋诗人时说:
对他们的“叛逆”基本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是诗的审美观念嬗变,以韩东、周伦佑、廖亦武、于坚为这一诗潮代表,其二认为是“文化态度”的叛逆,将第三代诗划分为“以现代意识反观古典文化的现代史诗”和“以显现人与文化的对抗与冲突为动意的反文化诗潮”,前者以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宋渠、宋炜为代表,后者以周伦佑、蓝马、杨黎、李亚伟、尚仲敏、廖亦武、于坚、韩东等为代表。①
总之,反叛诗歌到最后什么都要反,他们要反一切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他们在反传统的同时也要反先锋,反别人的同时更要反自己。现在看来,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肉体与灵魂得到解放之后的机械反弹式骚动,是对人的观念更新之后的无限张扬的青春情结。同时,更是一种对传统主流文化的一种极度对抗和彻底叛逆。他们坚信不移的是:不把固有的东西打破,就无法建立崭新的秩序。
3、“红色写作”和“继续非非”
我前面说过,无论是前朦胧诗和继后出现的先锋诗歌,都是中国特定文化和价值转型时期的过渡性产物。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价值和艺术嬗变之后,该向何处去成了诗人们苦苦探问和追寻的一件大事。曾经鼎盛一世的非非发起人和非非理论主笔周伦佑在1992年9月《非非》复刊号上“红色写作”诗学理论,在2001年《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上又提出“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这一重要理念。同时以他新完成的变构作品《遁辞》实践着他的诗学理论。
《红色写作》要义: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一文中对之前的“白色写作”和他界定的“红色写作”作了如下对照:
白色写作:缺乏血性的苍白、创造力丧失的平庸、故作优雅的表面文章……没有中心的溃散。飘忽无根的词语相互拥挤着,作清淡谈状、作隐士状、作嬉皮状、作痞子状……一味地琐碎,一味地平淡,一味地闲适。有意避开大师及其作品,对力度与深刻的惧怕或不敢问津。以白萝卜冒充象牙,借以逃避真实和虚构的险境。在轻音乐的弱奏中,一代人委蛇的分行排列,用有限的词语互相模仿、自我模仿、集体模仿、反复模仿,一个劲的贫乏与重复,使琐屑与平庸成为一个时期新诗写作的普遍特征。(周伦佑:《反价值时代》卷三《打开红色写作之门》)。周伦佑最后总结到,白色诗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闲适”,属于弱力人格对现实世界自觉脱离和逃避的“小白脸”式艺术。
红色写作: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模仿移植,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不是抽象智慧。近乎残酷的真实,深入肉体世界的一切险境。金属的尖锐。在摆脱了闲适与模仿之后,中国诗人用生命写出的真正中国感受的现代诗。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同上)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中一再强调“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提出写作本身就是行动和投入。认为诗人一生的主要意象与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有关。重视诗歌语言的品质和力度,提倡写作与做人的统一。红色写作是一种立场和精神。
周伦佑就是这样,总是带着他自己的立场和精神进入非非写作和非非理论的。
继续非非的内涵:在2001年《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中,周伦佑在接受《亚太时报》文化专栏主持人肖芸女士采访时提出了“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的理念。当肖芸女士问及《非非》第二次复刊的使命和意义时,周伦佑总结了三点:①主动拉开与体制文学的距离,重建体制外诗歌运动;②拒绝通俗文化及商业心态,为先锋写作注入新的活力;③倡导“体制外写作”理念,推动深入骨头与制度的“后非非写作”。在谈到什么是“非非主义精神”时,周伦佑也提出了三点:第一是它的革命性,它不是对传统的依附与归顺,而是彻底的反叛与解构。第二是它的变构意识。非非不是流星主义,从一开始它就提出了自我变构的不断革命思想,并以此为自己的精神推进器。变构线路为“语言变构”、“反文化”――“价值变构”、“超语义实验”――“红色写作”、“21世纪写作”。第三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凡是认同非非精神和非非诗歌理论并以自己的作品实践非非精神和非非理论的诗人均可成为非非主义诗人。
二、《遁辞》文本:对非非精神和非非诗歌理论的实践功效
简略回顾了前朦胧诗运动及之后的诗歌变构历程以及基本理清了“前非非写作”理念和“后非非写作”理论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阅读和分析周伦佑刊载于《非非》2001年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上的新作《遁辞》了。
1、《遁辞》诗题释义
《遁辞》本义:字典上对“遁”的注释是逃走的意思,而辞则是辞赋即一种文学体裁。遁可组成的词如隐遁、遁迹、逃遁、遁词等,遁词的意思是“因为理屈词穷故意避开正题的话”,周伦佑的《遁辞》一诗,从立意上讲,就是故意避开正题,通过对汉语言修辞方式的解构以揭示国人被体制意识形态异化和物化的“修辞化”处境。
《遁辞》喻义:通过人与物的各种辞格关系来比喻人的本质以及人间公理和真美的隐匿和沉沦。
《遁辞》借义:借三种辞格方式(人的比喻游戏、物的比拟游戏、人与物的反修辞练习)来写人的隐匿和人这一汉字的还原。
《遁辞》真义:通过对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遁词的赘述,强烈呼唤人类纯洁肉体和崇高品质的重建,呼唤人间公理和真美的重建,呼唤逃遁的一切重建,呼唤至高至上的诗歌重建,呼唤摧枯拉朽之后理想国的重建!
2、《遁辞》文本特征
修辞:周伦佑在《遁辞》一诗中,从汉语构词造句上直接采取汉语修辞中的几种方式来完成本文的写作。其一是比喻手法,即打比方,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另一事物。例句:“人像竹子,虚心使人进步,然后节节败退”。其二是比拟手法,即把物拟作人或把人拟作物。例句:“没有一种心灵不空虚,所以人是气态的”。其三是反修辞手法,即对常规修辞手法的反叛,通过分解、拆散、打乱、重组来达到传统意义的隐遁和消失,例句:“人发现鸡是一个打破了的蛋”。
重复与偏离:在《遁辞》中,作者反复使用了传统的重复修辞手法。这些重复手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像”、“似”、“仿佛”等喻词来完成。例句:“人像飞鸟,在有效的射程之内随时准备应声而落”。“飞鸟似人,在权力的范围之内随时可能踩响地雷”。“黑夜般深沉的人――所以人仿佛黑夜”。值得注意的是,《遁辞》中这种重复修辞手法的运用结果却使整句话的含义产生了意义上的奇妙偏离。这种偏离主要是依靠喻词前后的被喻体词和喻体词的内涵和外延而产生。《遁辞》使话语在意义上产生偏离是为了实现对传统价值词的意义消解。
整体类比和整体叠加:在《遁辞》中对汉语修辞的具体运用上,周伦佑采取了很传统的修辞方式:整体类比和整体叠加。整体类比:词与词类比,例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句与句类比,例句:“青松拟好人。青松总是长在英雄就义的地方;纸老虎拟坏人,一打就倒,不打也倒,自己倒”;段与段类比,例略。全诗三大部分(辞格1、辞格2、辞格3)在整体结构上都属于类比方式,每个部分之间写作方式(含修辞)类同。整体叠加:词与词的叠加,例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句与句的叠加,例句:“青松拟好人。青松总是长在英雄就义的地方;纸老虎拟坏人,一打就倒,不打也倒,自己倒”;段与段叠加,例略。全诗三大部分表现的意义叠加:1、把人比喻成其他人和物;2、把物比拟成人和其它物;3、把人和物都分解和还原成其他人和其它物或者非人和非物。
因果:传统因果:因为“人――像人类”,所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因为“‘坏蛋好比过街的老鼠”’,所以“人又像老鼠”。反传统因果:因为有“文字垃圾”,所以“语言已经拟杂物”了。因为“太阳像第一滴精液”,所以“使所有的石头怀孕”。从《遁辞》整体(三大部分:辞格1、辞格2、辞格3)上看,也符合整体因果原则:因为人像人或者人像物,因为物像人或者物像其它的物,因为人和物的组合和分解像另外的人和物,所以人和物不像什么或者不怎么像什么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像什么结果人和物已经是他人和他物、非人和非物了。
分解:形式上的分解是指对传统修辞、造句和反传统修辞和造句的分解,也就是分解、再分解、反分解,但绝不分解还原和还原分解。比如在《遁辞》的“分解练习”中对“人像关在笼子里的鸟”所进行的分解:
人象在笼子里关的鸟/人关象在鸟的笼子里
关在笼子里的鸟象人/笼子里的鸟象在关人
打破传统的修辞手法进行另类组合,对固定的词语进行异端地拆解、分裂和重组。这是周伦佑所谓反传统、反修辞、反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文本案例。它的实践意义只有一个:在特定的阶段先不谈重建,继续从修辞推进解构!
意义进度递增和价值进度递减:《遁辞》中存在着大量的意义进度递增的手法。意义进度递增:就是把一句话说完说尽。比如:“人仿佛小说。男人仿佛武侠小说,女人仿佛言情小说/或者换一个角度:男人仿佛通俗小说,女人仿佛流行杂志/内容空洞乏味,看点全在华丽的封面”。意义递增的第一层含义是一句话的意思完整度,另外就是从这句话迅速地说开去,说出作者自己必然要说出的。价值进度递减:指一句意义进度递增的话在审美价值进度上却呈现递减的现象。这是《遁辞》文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先看例句:“人像竹子,虚心使人进步,然后节节败退”。“敌人有如丧家之犬,所以人又像无家可归的狗”。“好人像青松。英雄总是倒在青松下”。“人仿佛没有归岸的船,在海上升帆、落帆,随时准备着沉没”。“你口碑好,你已经拟碑文了;你身体棒,你已经拟木头了;很异类的感觉使你长出根来,寻根把人寻成了植物。浑身铜臭的人已经是铜,水性杨花的人已经是水,都已经非人成物了。”“毛泽东翻手一片电光,罩住几十万条戴眼镜的蛇,至今不敢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在意义进度递增的同时其价值进度却在递减。这种特征的指向就是对常规词语的价值消解。价值进度递减到零的全过程,也就是“遁”的过程。“遁”即消解。
常规词句的大量插入:《遁辞》中大量使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词语,完全摈弃了学院派或知识分子诗歌的所谓必须是“诗”的诗句。比如流行民谣、过去样板戏或旧电影中的人名、传统成语、老百姓爱用的生活短句、泥土和花盆里一眼就能看见的花草科名、杂志上的流行称谓、体制内的学术和政治术语、经济时代的幽默和批评缩句等。这些常规词语大多带有特定的含义,《遁辞》力图把这些常规词语的特定含义进行彻底地消解。比如:“把政策放开,政策已经拟绳索了;把经济搞活,经济已经拟病马了……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已经拟磐石了。希望总是破灭,希望已经拟肥皂泡了。”把常规经典词语的特定价值全部“遁”化,以达到最终消解的目的。
自由撰稿类魔鬼词语阐释:《遁辞》辞格三中的“解读练习”将一般报刊媒体上曾经流行过的时尚魔鬼词语另类解读运用得出神入化。这是《遁辞》的又一特征。对这些词语解读的最终意义,周伦佑总是非同一般:要么如前面我所说的价值进度递减,要么对人性深处的顽疾和人类终极追寻进行直接和最本质的阐释。比如:“人云亦云:别人说云,你也说云;别人变成云,你也跟着变成云。比喻一个人丧失自我的变化过程。”在传统的意义解释上进一步直接和深化。又比如:“争鸣:争:抢着。像鸟儿叫春一样争先恐后地打嗝、放屁,放出些香花、毒草。”对体制内一些学术和研讨中出现的怪异现象进行概括和注解。再比如:“革命:革:去毛。也指去掉毛的兽皮。像剥皮去毛一样改造人民和世界。”政治残酷的一面赫然露脸。
3、《遁辞》与周伦佑非非诗学的实践关系
我们在前面的诗题释义中解释过《遁辞》的要义。现在我们将《遁辞》文本结合周伦佑的非非诗学来进行分析。周伦佑在非非创始之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诗歌美学概念:反价值。反价值具有非功利、非现实,非继承的特点。反价值主要是针对传统价值观的。反价值先从反文化开始,通过对伪价值的清除,打破传统的两值对立,对价值词的清除来达到反美、反和谐、反对称、反完整、反情态、反真实和新价值的建立。反诗歌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照周伦佑的反价值观点来看,反诗歌就是反具有传统价值量的诗歌。打破是为了重建!周伦佑在《遁辞》中反什么呢?他又要重建什么呢?
第一,从诗歌文本上看,传统的诗歌总是在文本中通过字词的组合来重现某个早已认定的价值观,即通过对汉语字词的处理达到提升主题的目的。而在周伦佑的《遁辞》中,他一直努力对早已认定的汉语字词价值观做最坚韧地消解,以达到对汉语传统价值的清除。
文案1:精神污染,人已经拟河流了;阶级斗争是拟阶梯的;路线斗争是拟道路的;党的光辉是拟太阳的。百花齐放是拟春天的。百家争鸣是拟鸟叫的。红卫兵是拟鲜血的。走资派是拟动物的。家庭成份是拟化学的。政治觉悟是拟佛经的……
价值还原:文案中诗句通过比拟将原有固定价值量的传统价值词语(精神污染、阶级斗争、党的光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红卫兵、走资派、家庭成份、政治觉悟)的价值观还原(回到比拟之前的词语原意),即将污染归到河流,阶级归到阶梯,路线归到道路,光辉归到太阳,百花齐放归到春天,百家争鸣归到鸟叫,红归到鲜血,走归到动物,觉悟归到佛经。取消固有的价值量,对传统汉语价值意义进行清除。让汉语还原到最初的本意上来。
第二,从语言的进度上来看,传统的诗歌语言进度总是向前、向前、再向前。所谓向前,即是语言沿着既定方向走到目的地。但周伦佑在《遁辞》中,言说总是在前进的过程中突然转向,让人在惊讶和莫名其妙的同时更深地体会到主语的自我悖谬。
文案2:
a.人像烈火,自己温暖自己,→(转向)自己烧痛自己。
b.哲学家像玻璃瓶里的苍蝇,前途光明,→(转向)没有出路。
c.人格可以自我塑造,→(转向)人当然是石膏或者陶土。
价值反向:价值反向比价值还原具有了更多反价值和更多的背叛。因为诗中话语转向后的价值观与传统固定的价值观相反,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违背传统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文化的叛徒,就是异端邪说。从上面文案中的转向结果来看,既滑稽又生动和深刻。
第三,既然打破的目的是为了新的价值表达和重建,那么周伦佑在《遁辞》中要表达和重建的究竟是什么呢?《遁辞》全篇分三个部分:辞格1、辞格2、辞格3。在辞格1的比喻游戏中写的是“人像人,人像其他人。人像物,人像所有物。”在辞格2的比拟游戏中,写的是改变人的诸多办法:“人拟物和物拟人。体制内的人拟物和体制外的人拟物。”辞格3的“以人与物为素材的反修辞练习”中进一步通过喻词证实人已经成为非人,“成为另一种物态和属性”。
文案3:
a.人像飞鸟,在有效的射程之内随时准备应声而落。
b.在斗争中锻炼――你首先是铁;在劳动中改造――你必须是废品。物质是第一性的。只有经过拟物的过程,你才能成为一颗忠诚的革命螺丝钉。
c.人,象形,两只脚的动物,一阴一阳的结合体,中国人的符号存在形式。无头,故不可使其知之;无手,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拆开,可还原为毫无意义的笔划:一撇、一捺。
价值反叛:中国人的存在形式整个就是一种物化的过程,人这一汉字的构造方式整个就是物性和奴性十足的书写表示。周伦佑在《遁辞》中将人的这些特征原原本本、客客气气地呈现出来,就像一件实物摆在那儿,一看都知道他是什么。《遁辞》就是这样一种实物。周伦佑的价值反叛只是针对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在《遁辞》中他一边采取对传统诗歌的构词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逃避,一边喋喋不休、哭笑不得地向人们述说这个严重异化、物化到非人非物的“修辞化”人类和“修辞化”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他要建立的,当然就是他心中的那个非修辞化,非物化,非异化的理想国了。
三、白色写作和红色写作的世纪大碰撞和后非非写作
1、《遁辞》与后非非写作
在《非非》2001年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上,周伦佑在接受《亚太时报》记者采访时对“后非非写作”有如下的论述:
后非非写作是非非主义的强势延伸,是后极权条件下一部分中国诗人、作家选择的写作立场。这里的“后”,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之后”那个意义上的“后”(POST――),而是“后期”的“后”,相当于中国古代史划分上的“前汉”、“后汉”的那个“后”。后非非写作时期的非非主义就是后期非非主义,或非非主义的新时期,后极权条件下的非非主义,等等。也不完全排除后现代主义的那个“后”字所包含的某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变构”的语义外延,后非非写作时期的非非主义在纠正非非主义过去曾有的谵妄、迷狂、偏激、自悖的同时,继续坚持和高扬以变构语言和文化为宗旨的非非主义精神,理论上承传艺术变构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反价值理论、红色写作理论、拒绝的姿态和“21世纪写作”理念中绵延不断,贯彻始终的坚持体制外先锋写作的不断革命思想。在创作中,强调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倡导并全力推动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②
由此可以看出,后非非写作是非非主义立场和艺术精神的全面推进。我们来看看《遁辞》对后非非创作的实践功效:
①、 在创作形式上反传统诗歌文本格式。整体结构以辞格1、2、3比喻、比拟和反修辞游戏、练习方式着手,这是传统诗歌绝不会整体采用的形式。单句结构也是通过比喻、比拟和反修辞方式来完成对传统构词方式和价值的消解。这是对前期非非诗歌的发展和变构。与非非风格相融。
②、 内容表达从整体到局部都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进行意义和价值的还原、消解、转向和反叛。
③、 取材上完全采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内容,人名、政治术语、流行民谣、时尚名词、宣传口号等应有尽有,用固有的价值词语来做比喻、比拟和反修辞练习,完成价值词语的非价值转换。
④、 通过价值还原和价值转换使整篇《遁辞》具有现实的高度真实性、社会政治和人类精神风貌的客观见证性和具有终极审美以及历史进程意义上的文献性。
2、白色写作和红色写作的大碰撞和大融合
在前面我们谈到了周伦佑提出的“白色写作”与“红色写作”概念:白色写作具有逃避当下现实、玩语言、玩诗歌的“闲适”倾向,自朦胧诗起至今,无论是中国体制内诗歌还是体制外的民间诗歌,都逃不脱白色写作的大染缸。“红色写作”则相反,是具有主动介入当下生存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拒绝和解与被体制内文学招安的深度写作,《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不仅充实、完成了红色写作的全面建构,而且,已经再次提供了精彩的红色写作实践:《遁辞》和《诗歌白皮书》。
《遁辞》中的白色暗伤:大部分由三种辞格游戏方式完成,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存在“玩”的表象,譬如《遁辞》的题引,此白色之一;单句语言通过比喻、比拟、借喻、隐喻等传统修辞手法完成,譬如辞格1和辞格2中的单句,此白色之二;有口语和嬉皮特征,例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就像小双像大双,周伦佑像周伦佐。”此白色之三;在艺术手法上时有借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例句:“太阳像第一滴精液使所有的石头受孕。”此白色之四。
《遁辞》中的红色血液:
虽然大部分由三种辞格游戏方式完成,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存在“玩”的表象;单句语言虽然通过比喻、比拟、借喻、隐喻等传统修辞手法完成;口语和嬉皮式的语言以及艺术手法上借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但整个《遁辞》只是纯粹借用白色写作中的艺术手法来明确地揭示当下国人生存现实中的被动、尴尬、困倦、无奈、滑稽、没落、萎缩、物化、低劣、恶俗、机械等生存境况,它所表达的价值递减却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也就是说,在语言运用上有白色的成分,但《遁辞》整体通过作者有机而精心地组合,矛盾而和谐,精彩而又经典,那些白色的因子在不断的大碰撞和大融汇中发生了加速而奇妙的运动和变化,最终向人们展露和揭示的主题和内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血液,是深入骨头与体制的尖锐表达。
反价值就在白色和红色的碰撞和融汇中冲天而起!
3、从拼贴游戏谈后非非写作与前非非写作的相继性和跨越性
从《遁辞》中可以看出后非非写作的一些基本特征:语言拼贴式狂欢,内核深入骨头与制度,建立非非命定的反价值!
由于历时和现时的原因,非非阵营中几大开国元老都已形存神亡,这本身是很自然的俗世现象,89年以后的后非非时期,可以说只有周伦佑和少数非非同仁在继续“坚持不懈”!从这一点来说,周伦佑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孤独者。从他提出“红色写作”起,在诗歌文本的创建上,可以说周伦佑本人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艺术上要变构,要红色写作,又要保持住非非惯有的质地,谈何容易。在红色以前,周伦佑的文本实践中就有如陈旭光所说的“亚文本叙述”或“体内混杂”:即在诗歌本文中对非诗文体(相当于诗本体的亚文体)进行滑稽性模仿:故作风雅的古典诗文、荒诞不经的现代新闻报道、毛主席语录、小猫钓鱼的童话、论证“道”、“名”关系的论文体……实际上,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无体裁写作”,一种杰姆逊所说的“机遇式的无边写作”。众多的“亚文体”作为“非诗文体”而挤进诗歌本文空间,杂乱堆积于一个平面上,自有其独特的反讽意义。这种写作方式曾经是被朦胧诗以后的写作者们达成默契和引起的大面积共识的。但对周伦佑来说,也许这都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第三代诗论》(1988)中这样解释过“反修辞”的含义:
反修辞首先是对传统修辞方法的摒弃:停止比喻!停止拟人、拟物!不再“像什么”、“什么般的什么”,而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更严重的是停止“通感”!停止“反逻辑比喻”!摒弃现代修辞,不再“芬芳地走”,不再倾听“活的石柱”。香味就是香味,不必“听到”和“喊叫”;石头就是石头,不必“活着”或“死去”。要实现的最低和最高的目标就是:直接性――语言的直接性!③
可以说,前非非写作就是在反价值状态下的反修辞写作。无论是蓝马、杨黎还是何小竹,他们的写作都是在反价值反修辞的前提下对外来诗歌文化的一种借用和初级变构。周伦佑的目的是要写出本土的直接的诗歌本文!《遁辞》只是最近的尝试。对周伦佑来说,《遁辞》肯定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在《遁辞》中,他还是没有完全逃脱以前写作的巢臼!其实,这根本就无法逃脱!
同前期《自由方块》一样,周伦佑在《遁辞》中也使用“狂欢式拼贴”方式,对这种“狂欢式拼贴”,王一川博士在《周伦佑:拼贴游戏》一文中有过这样的精彩论述:“周伦佑则是纵情地投入个人的语言拼贴游戏,直至在《自由方块》(1986年)中走入极端。这是一首语言或文体与众不同的奇特长诗。全诗由分行诗、散文诗、散文、引语、插话和图案等多种文体片断无逻辑地拼贴而成,交替运用了比喻、排比、回环、重复、无标点浓缩句等多种修辞手段,话题涉及当代与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与性、战争与体育、哲学与宗教等,在表意上充满着停顿、断裂和含混,明显地带有杂语喧哗与狂欢特点。然而,与立体语言和调侃式语言等在杂语喧哗中具有明显的现实再现意味不同,这里的杂语喧哗缺少那种具体再现性,而更多地返回能指语言自身,寻求语言内部的拼贴的狂欢。”④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就是一位拼贴大师,在他的《比萨诗章》中,就包括了传统诗歌美学认为不适合入诗的各种材料:经济学理论、各种历史文献、法律文本等。《比萨诗章》几乎囊括了任何文本材料。庞德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诗中建立一种新的形式,它不但足以表现当下任何事物,而且更能激发读者的意识和思想。在周伦佑的《遁辞》中,这种“狂欢式拼贴”仍然大量存在,与《自由方块》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狂欢重在对“现实的红色介入”,再也不像《自由方块》那样隐蔽。与庞德一样,他想要建立属于非非的特定的文本形式,不仅想要猛烈地激发读者的意识和思想,更要激发读者的激情与想象力,震动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从此种角度来看,后非非写作要努力做到的,只是更新、更快地变构和超越以前的一切形式和价值观!所有的目的都在变构和超越中逐渐逼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伦佑在解释“反修辞”时所说的最低和最高的目标“直接性”在语言方式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种价值和思想的直接介入和深化。新的思想和价值可以瓦解过去的一切,同时更能建立一种全新的艺术有机体甚至世界运行机制!
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才是最真实和直接的母体!其它的一切都是工具、载体和原料!思想是本质,是唯一的上帝,其余全是为他服务的奴隶!
四、《遁辞》的现实内蕴、语言价值观以及文本形式的多重可能
无论从历时的还是现时的角度来看,周伦佑所倡导的某些价值观与前面提到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的《比萨诗章》中所表现的价值观都非常相近,杰夫・特威切尔-沃斯在《灵魂的美妙夜晚来自帐篷中,泰山下》一文中这样指出:
《诗章》的前面部分相对来说较多地关注那些消极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关注永远被银行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和使银行得以行使极坏权力的政治贪婪或无能。庞德以此确立他全盘的创作构思。与此紧密相连的,当然是庞德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形式所寄予的政治希望遭到破灭……庞德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过去能依靠的所有各色支持和自信之后,必须依赖回忆,不仅重新审视那些决定他写诗生涯的假定,而且在更基本的水平上恢复那些重新肯定他生活价值观的经验。到头来是,在某些思想活跃的时刻,诗人寻找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苟且活命的恶劣条件之外寻找给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这些正是文学艺术为反对纯功利主义价值观而企图表达、扩大和捍卫的价值观。⑤
周伦佑也是如此。在他的诗集《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中,无论是比较重要的《带猫头鹰的男人》、《头像》、《十三级台阶》,还是《石头构图的境况》等短小精练之作,都表达了他一贯的主题。台湾诗人黄梁在《刀锋上的诗与历史》一文中对周伦佑的诗歌主题总结了三点:一、借整体抽象思维探察时代脉理,思考文化病症。二、以个体心灵价值之确立抗衡残酷的极权暴力。三、用意志撑持精神空间,伸张想象力突破现实禁锢。在《遁辞》中,周伦佑以他习惯的文本方式通过“狂欢式拼贴”游戏在消解体制价值的同时建立他的反价值――即新价值。具体地说,他通过三种修辞格的游戏与练习反向揭示出了人的物化处境和道德的沉沦、官场的腐败、政治的虚伪、学术的伪劣以及真善美的被玷污……总之,用他诗中结束时拆解“人”字的话来说,“人是两只脚的动物,是一阴一阳的结合体,中国人的符号存在形式。无头,故不可使其知之;无手,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拆开,可还原为毫无意义的笔划:一撇、一捺。”他通过如此精妙的“证伪”和“证无”,目的是要表达和建立他所向往的真实、美善和自由。
在文本形式上,《遁辞》通过自由而狂欢式的拼贴,来达成具有反价值的价值结构,看上去任何东西都是信手拈来,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是那么简单明白,但这些字词和话一经组合在一起,就具有无穷大的新价值。这就是我要提出的一个重要词汇――诗语结构!汉字是有限的,但汉字的结构组合却是无限的。一首诗就是作者所选定的汉字通过诗人的思想和灵魂而建构的一种全息结构,哪怕从一个极小极破碎的部分,也能看出人类和世界的缩影。若如此,则诗歌就具有了无限的价值可能和反价值可能!结构能产生一切!所以诗歌也能产生一切!包括有机的思想和多维的世界!
从文体情境和文本事实来看,诗歌文本本身更是一种信息结构。周伦佑的文体情境充满了刺激和反差。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坦利・费什在解释“文体情境”一词时说:
文体情境是一个语言型式突然被一个没有料到的成分打破。由这一干扰所产生的反差就是文体刺激。这种断裂不应被理解成是一种分离原则。反差的文体价值正在于它在两个冲突的成分之间建立的关系,没有它们在时序中的这种联系,就不会发生任何效果。换句话说,文体反差,像语言中其他有用的对比一样,创造了一种结构。⑥
无论是周伦佑的文本结构还是语言结构,都在极度膨胀中完成这种结构本身的能指功效。当然,随着这种结构本身的不断裂变和自我繁殖,这种结构完全可以创造出诗的无限可能,并由文本结构和诗语结构的敞亮带给新世纪的汉语诗歌一片新暖的曙光!
结语、非非反价值的红色宣言
打破一切常规形式,让一切不可能的可能自由呈现!
打破一切固定结构,在写作中创造多维的结构!
打破一切语法修辞,让每一首诗去创造自己的修辞和语法!
打破一切陈腐思想,让自由精神天马行空、随风高扬!
打破一切传统价值,让新价值的朝阳辉映四方!
注释:
①、尹国均:《先锋实验》第14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②、见《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第17页,新时代出版社2002年。
③、周伦佑:《第三代诗论》,《艺术广角》1989年第一期。
④、见王一川著《中国形象诗学》第158-16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⑤、见《庞德诗选.比萨诗章》276页,黄云特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
⑥、见《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
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就是战斗,语言就是价值,语言就是存在,语言就是时间和空间!
中国诗人必须立即从传统汉语意义上的反语言中突破出来,进行一个有血性中国人倾其一生而致力的伟大事业:重建新世纪诗歌和汉语言的价值体系!
――摘自2002年《诗歌札记》
在《非非》2001年第九卷非非流派专号上,有两个不仅对非非主义也对当下整个中国诗歌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常文本――周伦佑的《遁辞》和陈亚平的《诗歌白皮书》。我之所以说它们是两个极具重要的非常文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对诗歌语言价值体系的重建有着突破百年的领衔功能。在这里我们不必对中国的百年诗歌做一个工程浩大而繁杂的清理和清算,只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朦胧诗以及之后的先锋流派诗作一简要的回顾就可以开始进入本文研讨的主题。
80年代对中国诗歌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启蒙革命。随前朦胧诗破土而来的先锋实验写作出现了众多叛逆当时特定的体制文化和传统理性规范的诗歌群体,理论和作品呈鱼龙混杂之势翻搅于整个中国诗坛。此阶段的诗歌运动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1、诗歌整体凸出表现主义抽象化风格,艺术特征是拆除语言能指和所指的传统固定关系。这也是当时很时髦的一种反语言、反文化、反语法、反传统观。2、超现实主义的提升或者说淡化和还原,其艺术特征是抛弃已有的价值体系而走向客体和空无,这是另一种与崇高、传统道德和审美的进一步对抗和逆反。
一、反叛诗歌从出场到今天的变构的主要阶段性途径:
1、前朦胧诗为反叛诗歌的出场设定了必然的历史舞台
前朦胧诗的发生背景和动因:要对中国的前朦胧诗及之后的诗歌发展有一个明晰的定论,必须要对中国诗歌的文化大背景有一个简略的交代。从中国的诗歌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诗歌史就是一部国人理念的解放史。如果把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作是中国国民理念的第一次觉醒和生命体验的启蒙的话,那么一进入文化大革命,这种刚刚出现的对人的理念的解放就遭到了空前绝后的扼杀。文革十年,无论是中国的知识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长期处于文化黑洞的框桎中,传统观念和强权政治形成了一种铁的统治,人对人变得麻木不仁甚至不知道人之为何了。也就是说,人的物化已经使人成为物,人的异化也使人成为异族和异类了。某一天,当人们幡然醒悟突然得到解放并看清自己以前的蒙昧,那种惊异和激奋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乎,重获新生的人们都想着要把他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体验传达给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诗歌,因为只有诗歌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激情的宣泄来完成他们的表述。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国民心灵带来的阵痛以及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极不稳定的风雨政局,苏醒的中国文人在高压政治的强力压迫下,带着惴惴的心态像鼹鼠一样谨小慎微地审视和猜测着中国的未来。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昌行一时的前朦胧诗。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等。
前朦胧诗的文本特征和艺术特色:文本特征沿袭汉语分行自由体式。与传统意义上的汉语分行体诗不同的是前朦胧诗在分行断句上打破常规,比如不用标点符号断句,开始不讲究汉语规范语法。艺术特色重在突出诗意的朦胧。前面说过,这一时期的诗人们还处在审视和猜测阶段,他们害怕一不小心再次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文化黑洞和政治漩流。他们只能含糊其词地借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咕哝着他们的呓语。但从前朦胧诗的发展过程来看,前期大多是在说“我不”,总体意思是我不愿、不想、不要像以前那样过愚民和狱犯生活,不愿、不想、不要成为没有思想的动物。我是人,我不是动物。而后阶段,他们主要是在喊出“我要”,要过像人一样的生活,要有自己的思考,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抒自己想抒的情,我要成为本质意义上的我,我就是我自己。前朦胧诗为人的理念的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件事的发生必然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前朦胧诗时期正处在文革结束国门刚刚打开的特定历史时期。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研究人本身的各类学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给中国的前朦胧艺术家们带来了渐行渐绿的春意。这对国民的理念觉醒也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2、反叛诗歌的群体出场和深渊影响
反叛诗歌发生发展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伴随着前朦胧诗的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流派和各种风格的试验诗歌,这本身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诗人们激动且冲动地把“我不”和“我要”说出来以后,就会冷静下来仔细对诗歌艺术本身进行思考和探索。正因为如此,从84年开始,中国诗坛似乎一夜之间就涌现出了众多的先锋诗人和稀奇古怪的先锋流派。先锋反叛诗歌群体从九十年代开始日趋沉寂。原因之一是很多诗人受市场经济诱惑而投身于物质建设,另外,同前朦胧诗一样,反叛诗歌本身就是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当它完成任务之后必然又要走向新的变构。
反叛诗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内涵:反叛诗歌这一提法是针对传统诗歌的艺术观和价值观的,甚至也是针对前朦胧诗相对单一和单薄的艺术手法及审美内涵的。当这种反叛诗歌一出现,似乎因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无论是诗歌作品还是诗歌理论都远远地超越了诗人们当初的宗旨。反叛诗歌发展到最后,必然要对文化、社会、人类自身和诗歌自身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反思和质疑。我们从大展中异军突起的两个重要诗派的一些特征即可得到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86年的诗歌群体大展,四川的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名噪一时。非非主义的“前非非写作”时期(1986-1989),主张反文化、反价值、超文化、超语言,拆解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系,反抽象词语,甚至从反能指角度突围。(参见尹国均著《先锋实验》)。而莽汉主义则以亵渎一切的姿态出现在诗坛。研究者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先锋诗人时说:
对他们的“叛逆”基本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是诗的审美观念嬗变,以韩东、周伦佑、廖亦武、于坚为这一诗潮代表,其二认为是“文化态度”的叛逆,将第三代诗划分为“以现代意识反观古典文化的现代史诗”和“以显现人与文化的对抗与冲突为动意的反文化诗潮”,前者以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宋渠、宋炜为代表,后者以周伦佑、蓝马、杨黎、李亚伟、尚仲敏、廖亦武、于坚、韩东等为代表。①
总之,反叛诗歌到最后什么都要反,他们要反一切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他们在反传统的同时也要反先锋,反别人的同时更要反自己。现在看来,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肉体与灵魂得到解放之后的机械反弹式骚动,是对人的观念更新之后的无限张扬的青春情结。同时,更是一种对传统主流文化的一种极度对抗和彻底叛逆。他们坚信不移的是:不把固有的东西打破,就无法建立崭新的秩序。
3、“红色写作”和“继续非非”
我前面说过,无论是前朦胧诗和继后出现的先锋诗歌,都是中国特定文化和价值转型时期的过渡性产物。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价值和艺术嬗变之后,该向何处去成了诗人们苦苦探问和追寻的一件大事。曾经鼎盛一世的非非发起人和非非理论主笔周伦佑在1992年9月《非非》复刊号上“红色写作”诗学理论,在2001年《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上又提出“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这一重要理念。同时以他新完成的变构作品《遁辞》实践着他的诗学理论。
《红色写作》要义: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一文中对之前的“白色写作”和他界定的“红色写作”作了如下对照:
白色写作:缺乏血性的苍白、创造力丧失的平庸、故作优雅的表面文章……没有中心的溃散。飘忽无根的词语相互拥挤着,作清淡谈状、作隐士状、作嬉皮状、作痞子状……一味地琐碎,一味地平淡,一味地闲适。有意避开大师及其作品,对力度与深刻的惧怕或不敢问津。以白萝卜冒充象牙,借以逃避真实和虚构的险境。在轻音乐的弱奏中,一代人委蛇的分行排列,用有限的词语互相模仿、自我模仿、集体模仿、反复模仿,一个劲的贫乏与重复,使琐屑与平庸成为一个时期新诗写作的普遍特征。(周伦佑:《反价值时代》卷三《打开红色写作之门》)。周伦佑最后总结到,白色诗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闲适”,属于弱力人格对现实世界自觉脱离和逃避的“小白脸”式艺术。
红色写作: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模仿移植,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不是抽象智慧。近乎残酷的真实,深入肉体世界的一切险境。金属的尖锐。在摆脱了闲适与模仿之后,中国诗人用生命写出的真正中国感受的现代诗。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同上)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中一再强调“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提出写作本身就是行动和投入。认为诗人一生的主要意象与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有关。重视诗歌语言的品质和力度,提倡写作与做人的统一。红色写作是一种立场和精神。
周伦佑就是这样,总是带着他自己的立场和精神进入非非写作和非非理论的。
继续非非的内涵:在2001年《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中,周伦佑在接受《亚太时报》文化专栏主持人肖芸女士采访时提出了“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的理念。当肖芸女士问及《非非》第二次复刊的使命和意义时,周伦佑总结了三点:①主动拉开与体制文学的距离,重建体制外诗歌运动;②拒绝通俗文化及商业心态,为先锋写作注入新的活力;③倡导“体制外写作”理念,推动深入骨头与制度的“后非非写作”。在谈到什么是“非非主义精神”时,周伦佑也提出了三点:第一是它的革命性,它不是对传统的依附与归顺,而是彻底的反叛与解构。第二是它的变构意识。非非不是流星主义,从一开始它就提出了自我变构的不断革命思想,并以此为自己的精神推进器。变构线路为“语言变构”、“反文化”――“价值变构”、“超语义实验”――“红色写作”、“21世纪写作”。第三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凡是认同非非精神和非非诗歌理论并以自己的作品实践非非精神和非非理论的诗人均可成为非非主义诗人。
二、《遁辞》文本:对非非精神和非非诗歌理论的实践功效
简略回顾了前朦胧诗运动及之后的诗歌变构历程以及基本理清了“前非非写作”理念和“后非非写作”理论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阅读和分析周伦佑刊载于《非非》2001年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上的新作《遁辞》了。
1、《遁辞》诗题释义
《遁辞》本义:字典上对“遁”的注释是逃走的意思,而辞则是辞赋即一种文学体裁。遁可组成的词如隐遁、遁迹、逃遁、遁词等,遁词的意思是“因为理屈词穷故意避开正题的话”,周伦佑的《遁辞》一诗,从立意上讲,就是故意避开正题,通过对汉语言修辞方式的解构以揭示国人被体制意识形态异化和物化的“修辞化”处境。
《遁辞》喻义:通过人与物的各种辞格关系来比喻人的本质以及人间公理和真美的隐匿和沉沦。
《遁辞》借义:借三种辞格方式(人的比喻游戏、物的比拟游戏、人与物的反修辞练习)来写人的隐匿和人这一汉字的还原。
《遁辞》真义:通过对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遁词的赘述,强烈呼唤人类纯洁肉体和崇高品质的重建,呼唤人间公理和真美的重建,呼唤逃遁的一切重建,呼唤至高至上的诗歌重建,呼唤摧枯拉朽之后理想国的重建!
2、《遁辞》文本特征
修辞:周伦佑在《遁辞》一诗中,从汉语构词造句上直接采取汉语修辞中的几种方式来完成本文的写作。其一是比喻手法,即打比方,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另一事物。例句:“人像竹子,虚心使人进步,然后节节败退”。其二是比拟手法,即把物拟作人或把人拟作物。例句:“没有一种心灵不空虚,所以人是气态的”。其三是反修辞手法,即对常规修辞手法的反叛,通过分解、拆散、打乱、重组来达到传统意义的隐遁和消失,例句:“人发现鸡是一个打破了的蛋”。
重复与偏离:在《遁辞》中,作者反复使用了传统的重复修辞手法。这些重复手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像”、“似”、“仿佛”等喻词来完成。例句:“人像飞鸟,在有效的射程之内随时准备应声而落”。“飞鸟似人,在权力的范围之内随时可能踩响地雷”。“黑夜般深沉的人――所以人仿佛黑夜”。值得注意的是,《遁辞》中这种重复修辞手法的运用结果却使整句话的含义产生了意义上的奇妙偏离。这种偏离主要是依靠喻词前后的被喻体词和喻体词的内涵和外延而产生。《遁辞》使话语在意义上产生偏离是为了实现对传统价值词的意义消解。
整体类比和整体叠加:在《遁辞》中对汉语修辞的具体运用上,周伦佑采取了很传统的修辞方式:整体类比和整体叠加。整体类比:词与词类比,例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句与句类比,例句:“青松拟好人。青松总是长在英雄就义的地方;纸老虎拟坏人,一打就倒,不打也倒,自己倒”;段与段类比,例略。全诗三大部分(辞格1、辞格2、辞格3)在整体结构上都属于类比方式,每个部分之间写作方式(含修辞)类同。整体叠加:词与词的叠加,例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句与句的叠加,例句:“青松拟好人。青松总是长在英雄就义的地方;纸老虎拟坏人,一打就倒,不打也倒,自己倒”;段与段叠加,例略。全诗三大部分表现的意义叠加:1、把人比喻成其他人和物;2、把物比拟成人和其它物;3、把人和物都分解和还原成其他人和其它物或者非人和非物。
因果:传统因果:因为“人――像人类”,所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因为“‘坏蛋好比过街的老鼠”’,所以“人又像老鼠”。反传统因果:因为有“文字垃圾”,所以“语言已经拟杂物”了。因为“太阳像第一滴精液”,所以“使所有的石头怀孕”。从《遁辞》整体(三大部分:辞格1、辞格2、辞格3)上看,也符合整体因果原则:因为人像人或者人像物,因为物像人或者物像其它的物,因为人和物的组合和分解像另外的人和物,所以人和物不像什么或者不怎么像什么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像什么结果人和物已经是他人和他物、非人和非物了。
分解:形式上的分解是指对传统修辞、造句和反传统修辞和造句的分解,也就是分解、再分解、反分解,但绝不分解还原和还原分解。比如在《遁辞》的“分解练习”中对“人像关在笼子里的鸟”所进行的分解:
人象在笼子里关的鸟/人关象在鸟的笼子里
关在笼子里的鸟象人/笼子里的鸟象在关人
打破传统的修辞手法进行另类组合,对固定的词语进行异端地拆解、分裂和重组。这是周伦佑所谓反传统、反修辞、反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文本案例。它的实践意义只有一个:在特定的阶段先不谈重建,继续从修辞推进解构!
意义进度递增和价值进度递减:《遁辞》中存在着大量的意义进度递增的手法。意义进度递增:就是把一句话说完说尽。比如:“人仿佛小说。男人仿佛武侠小说,女人仿佛言情小说/或者换一个角度:男人仿佛通俗小说,女人仿佛流行杂志/内容空洞乏味,看点全在华丽的封面”。意义递增的第一层含义是一句话的意思完整度,另外就是从这句话迅速地说开去,说出作者自己必然要说出的。价值进度递减:指一句意义进度递增的话在审美价值进度上却呈现递减的现象。这是《遁辞》文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先看例句:“人像竹子,虚心使人进步,然后节节败退”。“敌人有如丧家之犬,所以人又像无家可归的狗”。“好人像青松。英雄总是倒在青松下”。“人仿佛没有归岸的船,在海上升帆、落帆,随时准备着沉没”。“你口碑好,你已经拟碑文了;你身体棒,你已经拟木头了;很异类的感觉使你长出根来,寻根把人寻成了植物。浑身铜臭的人已经是铜,水性杨花的人已经是水,都已经非人成物了。”“毛泽东翻手一片电光,罩住几十万条戴眼镜的蛇,至今不敢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在意义进度递增的同时其价值进度却在递减。这种特征的指向就是对常规词语的价值消解。价值进度递减到零的全过程,也就是“遁”的过程。“遁”即消解。
常规词句的大量插入:《遁辞》中大量使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词语,完全摈弃了学院派或知识分子诗歌的所谓必须是“诗”的诗句。比如流行民谣、过去样板戏或旧电影中的人名、传统成语、老百姓爱用的生活短句、泥土和花盆里一眼就能看见的花草科名、杂志上的流行称谓、体制内的学术和政治术语、经济时代的幽默和批评缩句等。这些常规词语大多带有特定的含义,《遁辞》力图把这些常规词语的特定含义进行彻底地消解。比如:“把政策放开,政策已经拟绳索了;把经济搞活,经济已经拟病马了……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已经拟磐石了。希望总是破灭,希望已经拟肥皂泡了。”把常规经典词语的特定价值全部“遁”化,以达到最终消解的目的。
自由撰稿类魔鬼词语阐释:《遁辞》辞格三中的“解读练习”将一般报刊媒体上曾经流行过的时尚魔鬼词语另类解读运用得出神入化。这是《遁辞》的又一特征。对这些词语解读的最终意义,周伦佑总是非同一般:要么如前面我所说的价值进度递减,要么对人性深处的顽疾和人类终极追寻进行直接和最本质的阐释。比如:“人云亦云:别人说云,你也说云;别人变成云,你也跟着变成云。比喻一个人丧失自我的变化过程。”在传统的意义解释上进一步直接和深化。又比如:“争鸣:争:抢着。像鸟儿叫春一样争先恐后地打嗝、放屁,放出些香花、毒草。”对体制内一些学术和研讨中出现的怪异现象进行概括和注解。再比如:“革命:革:去毛。也指去掉毛的兽皮。像剥皮去毛一样改造人民和世界。”政治残酷的一面赫然露脸。
3、《遁辞》与周伦佑非非诗学的实践关系
我们在前面的诗题释义中解释过《遁辞》的要义。现在我们将《遁辞》文本结合周伦佑的非非诗学来进行分析。周伦佑在非非创始之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诗歌美学概念:反价值。反价值具有非功利、非现实,非继承的特点。反价值主要是针对传统价值观的。反价值先从反文化开始,通过对伪价值的清除,打破传统的两值对立,对价值词的清除来达到反美、反和谐、反对称、反完整、反情态、反真实和新价值的建立。反诗歌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照周伦佑的反价值观点来看,反诗歌就是反具有传统价值量的诗歌。打破是为了重建!周伦佑在《遁辞》中反什么呢?他又要重建什么呢?
第一,从诗歌文本上看,传统的诗歌总是在文本中通过字词的组合来重现某个早已认定的价值观,即通过对汉语字词的处理达到提升主题的目的。而在周伦佑的《遁辞》中,他一直努力对早已认定的汉语字词价值观做最坚韧地消解,以达到对汉语传统价值的清除。
文案1:精神污染,人已经拟河流了;阶级斗争是拟阶梯的;路线斗争是拟道路的;党的光辉是拟太阳的。百花齐放是拟春天的。百家争鸣是拟鸟叫的。红卫兵是拟鲜血的。走资派是拟动物的。家庭成份是拟化学的。政治觉悟是拟佛经的……
价值还原:文案中诗句通过比拟将原有固定价值量的传统价值词语(精神污染、阶级斗争、党的光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红卫兵、走资派、家庭成份、政治觉悟)的价值观还原(回到比拟之前的词语原意),即将污染归到河流,阶级归到阶梯,路线归到道路,光辉归到太阳,百花齐放归到春天,百家争鸣归到鸟叫,红归到鲜血,走归到动物,觉悟归到佛经。取消固有的价值量,对传统汉语价值意义进行清除。让汉语还原到最初的本意上来。
第二,从语言的进度上来看,传统的诗歌语言进度总是向前、向前、再向前。所谓向前,即是语言沿着既定方向走到目的地。但周伦佑在《遁辞》中,言说总是在前进的过程中突然转向,让人在惊讶和莫名其妙的同时更深地体会到主语的自我悖谬。
文案2:
a.人像烈火,自己温暖自己,→(转向)自己烧痛自己。
b.哲学家像玻璃瓶里的苍蝇,前途光明,→(转向)没有出路。
c.人格可以自我塑造,→(转向)人当然是石膏或者陶土。
价值反向:价值反向比价值还原具有了更多反价值和更多的背叛。因为诗中话语转向后的价值观与传统固定的价值观相反,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违背传统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文化的叛徒,就是异端邪说。从上面文案中的转向结果来看,既滑稽又生动和深刻。
第三,既然打破的目的是为了新的价值表达和重建,那么周伦佑在《遁辞》中要表达和重建的究竟是什么呢?《遁辞》全篇分三个部分:辞格1、辞格2、辞格3。在辞格1的比喻游戏中写的是“人像人,人像其他人。人像物,人像所有物。”在辞格2的比拟游戏中,写的是改变人的诸多办法:“人拟物和物拟人。体制内的人拟物和体制外的人拟物。”辞格3的“以人与物为素材的反修辞练习”中进一步通过喻词证实人已经成为非人,“成为另一种物态和属性”。
文案3:
a.人像飞鸟,在有效的射程之内随时准备应声而落。
b.在斗争中锻炼――你首先是铁;在劳动中改造――你必须是废品。物质是第一性的。只有经过拟物的过程,你才能成为一颗忠诚的革命螺丝钉。
c.人,象形,两只脚的动物,一阴一阳的结合体,中国人的符号存在形式。无头,故不可使其知之;无手,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拆开,可还原为毫无意义的笔划:一撇、一捺。
价值反叛:中国人的存在形式整个就是一种物化的过程,人这一汉字的构造方式整个就是物性和奴性十足的书写表示。周伦佑在《遁辞》中将人的这些特征原原本本、客客气气地呈现出来,就像一件实物摆在那儿,一看都知道他是什么。《遁辞》就是这样一种实物。周伦佑的价值反叛只是针对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在《遁辞》中他一边采取对传统诗歌的构词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逃避,一边喋喋不休、哭笑不得地向人们述说这个严重异化、物化到非人非物的“修辞化”人类和“修辞化”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他要建立的,当然就是他心中的那个非修辞化,非物化,非异化的理想国了。
三、白色写作和红色写作的世纪大碰撞和后非非写作
1、《遁辞》与后非非写作
在《非非》2001年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上,周伦佑在接受《亚太时报》记者采访时对“后非非写作”有如下的论述:
后非非写作是非非主义的强势延伸,是后极权条件下一部分中国诗人、作家选择的写作立场。这里的“后”,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之后”那个意义上的“后”(POST――),而是“后期”的“后”,相当于中国古代史划分上的“前汉”、“后汉”的那个“后”。后非非写作时期的非非主义就是后期非非主义,或非非主义的新时期,后极权条件下的非非主义,等等。也不完全排除后现代主义的那个“后”字所包含的某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变构”的语义外延,后非非写作时期的非非主义在纠正非非主义过去曾有的谵妄、迷狂、偏激、自悖的同时,继续坚持和高扬以变构语言和文化为宗旨的非非主义精神,理论上承传艺术变构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反价值理论、红色写作理论、拒绝的姿态和“21世纪写作”理念中绵延不断,贯彻始终的坚持体制外先锋写作的不断革命思想。在创作中,强调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倡导并全力推动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②
由此可以看出,后非非写作是非非主义立场和艺术精神的全面推进。我们来看看《遁辞》对后非非创作的实践功效:
①、 在创作形式上反传统诗歌文本格式。整体结构以辞格1、2、3比喻、比拟和反修辞游戏、练习方式着手,这是传统诗歌绝不会整体采用的形式。单句结构也是通过比喻、比拟和反修辞方式来完成对传统构词方式和价值的消解。这是对前期非非诗歌的发展和变构。与非非风格相融。
②、 内容表达从整体到局部都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进行意义和价值的还原、消解、转向和反叛。
③、 取材上完全采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内容,人名、政治术语、流行民谣、时尚名词、宣传口号等应有尽有,用固有的价值词语来做比喻、比拟和反修辞练习,完成价值词语的非价值转换。
④、 通过价值还原和价值转换使整篇《遁辞》具有现实的高度真实性、社会政治和人类精神风貌的客观见证性和具有终极审美以及历史进程意义上的文献性。
2、白色写作和红色写作的大碰撞和大融合
在前面我们谈到了周伦佑提出的“白色写作”与“红色写作”概念:白色写作具有逃避当下现实、玩语言、玩诗歌的“闲适”倾向,自朦胧诗起至今,无论是中国体制内诗歌还是体制外的民间诗歌,都逃不脱白色写作的大染缸。“红色写作”则相反,是具有主动介入当下生存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拒绝和解与被体制内文学招安的深度写作,《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不仅充实、完成了红色写作的全面建构,而且,已经再次提供了精彩的红色写作实践:《遁辞》和《诗歌白皮书》。
《遁辞》中的白色暗伤:大部分由三种辞格游戏方式完成,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存在“玩”的表象,譬如《遁辞》的题引,此白色之一;单句语言通过比喻、比拟、借喻、隐喻等传统修辞手法完成,譬如辞格1和辞格2中的单句,此白色之二;有口语和嬉皮特征,例句:“人像中国人。人像美国人。人像非洲人/就像小双像大双,周伦佑像周伦佐。”此白色之三;在艺术手法上时有借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例句:“太阳像第一滴精液使所有的石头受孕。”此白色之四。
《遁辞》中的红色血液:
虽然大部分由三种辞格游戏方式完成,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存在“玩”的表象;单句语言虽然通过比喻、比拟、借喻、隐喻等传统修辞手法完成;口语和嬉皮式的语言以及艺术手法上借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但整个《遁辞》只是纯粹借用白色写作中的艺术手法来明确地揭示当下国人生存现实中的被动、尴尬、困倦、无奈、滑稽、没落、萎缩、物化、低劣、恶俗、机械等生存境况,它所表达的价值递减却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也就是说,在语言运用上有白色的成分,但《遁辞》整体通过作者有机而精心地组合,矛盾而和谐,精彩而又经典,那些白色的因子在不断的大碰撞和大融汇中发生了加速而奇妙的运动和变化,最终向人们展露和揭示的主题和内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血液,是深入骨头与体制的尖锐表达。
反价值就在白色和红色的碰撞和融汇中冲天而起!
3、从拼贴游戏谈后非非写作与前非非写作的相继性和跨越性
从《遁辞》中可以看出后非非写作的一些基本特征:语言拼贴式狂欢,内核深入骨头与制度,建立非非命定的反价值!
由于历时和现时的原因,非非阵营中几大开国元老都已形存神亡,这本身是很自然的俗世现象,89年以后的后非非时期,可以说只有周伦佑和少数非非同仁在继续“坚持不懈”!从这一点来说,周伦佑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孤独者。从他提出“红色写作”起,在诗歌文本的创建上,可以说周伦佑本人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艺术上要变构,要红色写作,又要保持住非非惯有的质地,谈何容易。在红色以前,周伦佑的文本实践中就有如陈旭光所说的“亚文本叙述”或“体内混杂”:即在诗歌本文中对非诗文体(相当于诗本体的亚文体)进行滑稽性模仿:故作风雅的古典诗文、荒诞不经的现代新闻报道、毛主席语录、小猫钓鱼的童话、论证“道”、“名”关系的论文体……实际上,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无体裁写作”,一种杰姆逊所说的“机遇式的无边写作”。众多的“亚文体”作为“非诗文体”而挤进诗歌本文空间,杂乱堆积于一个平面上,自有其独特的反讽意义。这种写作方式曾经是被朦胧诗以后的写作者们达成默契和引起的大面积共识的。但对周伦佑来说,也许这都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第三代诗论》(1988)中这样解释过“反修辞”的含义:
反修辞首先是对传统修辞方法的摒弃:停止比喻!停止拟人、拟物!不再“像什么”、“什么般的什么”,而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更严重的是停止“通感”!停止“反逻辑比喻”!摒弃现代修辞,不再“芬芳地走”,不再倾听“活的石柱”。香味就是香味,不必“听到”和“喊叫”;石头就是石头,不必“活着”或“死去”。要实现的最低和最高的目标就是:直接性――语言的直接性!③
可以说,前非非写作就是在反价值状态下的反修辞写作。无论是蓝马、杨黎还是何小竹,他们的写作都是在反价值反修辞的前提下对外来诗歌文化的一种借用和初级变构。周伦佑的目的是要写出本土的直接的诗歌本文!《遁辞》只是最近的尝试。对周伦佑来说,《遁辞》肯定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在《遁辞》中,他还是没有完全逃脱以前写作的巢臼!其实,这根本就无法逃脱!
同前期《自由方块》一样,周伦佑在《遁辞》中也使用“狂欢式拼贴”方式,对这种“狂欢式拼贴”,王一川博士在《周伦佑:拼贴游戏》一文中有过这样的精彩论述:“周伦佑则是纵情地投入个人的语言拼贴游戏,直至在《自由方块》(1986年)中走入极端。这是一首语言或文体与众不同的奇特长诗。全诗由分行诗、散文诗、散文、引语、插话和图案等多种文体片断无逻辑地拼贴而成,交替运用了比喻、排比、回环、重复、无标点浓缩句等多种修辞手段,话题涉及当代与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与性、战争与体育、哲学与宗教等,在表意上充满着停顿、断裂和含混,明显地带有杂语喧哗与狂欢特点。然而,与立体语言和调侃式语言等在杂语喧哗中具有明显的现实再现意味不同,这里的杂语喧哗缺少那种具体再现性,而更多地返回能指语言自身,寻求语言内部的拼贴的狂欢。”④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就是一位拼贴大师,在他的《比萨诗章》中,就包括了传统诗歌美学认为不适合入诗的各种材料:经济学理论、各种历史文献、法律文本等。《比萨诗章》几乎囊括了任何文本材料。庞德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诗中建立一种新的形式,它不但足以表现当下任何事物,而且更能激发读者的意识和思想。在周伦佑的《遁辞》中,这种“狂欢式拼贴”仍然大量存在,与《自由方块》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狂欢重在对“现实的红色介入”,再也不像《自由方块》那样隐蔽。与庞德一样,他想要建立属于非非的特定的文本形式,不仅想要猛烈地激发读者的意识和思想,更要激发读者的激情与想象力,震动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从此种角度来看,后非非写作要努力做到的,只是更新、更快地变构和超越以前的一切形式和价值观!所有的目的都在变构和超越中逐渐逼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伦佑在解释“反修辞”时所说的最低和最高的目标“直接性”在语言方式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种价值和思想的直接介入和深化。新的思想和价值可以瓦解过去的一切,同时更能建立一种全新的艺术有机体甚至世界运行机制!
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才是最真实和直接的母体!其它的一切都是工具、载体和原料!思想是本质,是唯一的上帝,其余全是为他服务的奴隶!
四、《遁辞》的现实内蕴、语言价值观以及文本形式的多重可能
无论从历时的还是现时的角度来看,周伦佑所倡导的某些价值观与前面提到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的《比萨诗章》中所表现的价值观都非常相近,杰夫・特威切尔-沃斯在《灵魂的美妙夜晚来自帐篷中,泰山下》一文中这样指出:
《诗章》的前面部分相对来说较多地关注那些消极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关注永远被银行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和使银行得以行使极坏权力的政治贪婪或无能。庞德以此确立他全盘的创作构思。与此紧密相连的,当然是庞德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形式所寄予的政治希望遭到破灭……庞德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过去能依靠的所有各色支持和自信之后,必须依赖回忆,不仅重新审视那些决定他写诗生涯的假定,而且在更基本的水平上恢复那些重新肯定他生活价值观的经验。到头来是,在某些思想活跃的时刻,诗人寻找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苟且活命的恶劣条件之外寻找给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这些正是文学艺术为反对纯功利主义价值观而企图表达、扩大和捍卫的价值观。⑤
周伦佑也是如此。在他的诗集《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中,无论是比较重要的《带猫头鹰的男人》、《头像》、《十三级台阶》,还是《石头构图的境况》等短小精练之作,都表达了他一贯的主题。台湾诗人黄梁在《刀锋上的诗与历史》一文中对周伦佑的诗歌主题总结了三点:一、借整体抽象思维探察时代脉理,思考文化病症。二、以个体心灵价值之确立抗衡残酷的极权暴力。三、用意志撑持精神空间,伸张想象力突破现实禁锢。在《遁辞》中,周伦佑以他习惯的文本方式通过“狂欢式拼贴”游戏在消解体制价值的同时建立他的反价值――即新价值。具体地说,他通过三种修辞格的游戏与练习反向揭示出了人的物化处境和道德的沉沦、官场的腐败、政治的虚伪、学术的伪劣以及真善美的被玷污……总之,用他诗中结束时拆解“人”字的话来说,“人是两只脚的动物,是一阴一阳的结合体,中国人的符号存在形式。无头,故不可使其知之;无手,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拆开,可还原为毫无意义的笔划:一撇、一捺。”他通过如此精妙的“证伪”和“证无”,目的是要表达和建立他所向往的真实、美善和自由。
在文本形式上,《遁辞》通过自由而狂欢式的拼贴,来达成具有反价值的价值结构,看上去任何东西都是信手拈来,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是那么简单明白,但这些字词和话一经组合在一起,就具有无穷大的新价值。这就是我要提出的一个重要词汇――诗语结构!汉字是有限的,但汉字的结构组合却是无限的。一首诗就是作者所选定的汉字通过诗人的思想和灵魂而建构的一种全息结构,哪怕从一个极小极破碎的部分,也能看出人类和世界的缩影。若如此,则诗歌就具有了无限的价值可能和反价值可能!结构能产生一切!所以诗歌也能产生一切!包括有机的思想和多维的世界!
从文体情境和文本事实来看,诗歌文本本身更是一种信息结构。周伦佑的文体情境充满了刺激和反差。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坦利・费什在解释“文体情境”一词时说:
文体情境是一个语言型式突然被一个没有料到的成分打破。由这一干扰所产生的反差就是文体刺激。这种断裂不应被理解成是一种分离原则。反差的文体价值正在于它在两个冲突的成分之间建立的关系,没有它们在时序中的这种联系,就不会发生任何效果。换句话说,文体反差,像语言中其他有用的对比一样,创造了一种结构。⑥
无论是周伦佑的文本结构还是语言结构,都在极度膨胀中完成这种结构本身的能指功效。当然,随着这种结构本身的不断裂变和自我繁殖,这种结构完全可以创造出诗的无限可能,并由文本结构和诗语结构的敞亮带给新世纪的汉语诗歌一片新暖的曙光!
结语、非非反价值的红色宣言
打破一切常规形式,让一切不可能的可能自由呈现!
打破一切固定结构,在写作中创造多维的结构!
打破一切语法修辞,让每一首诗去创造自己的修辞和语法!
打破一切陈腐思想,让自由精神天马行空、随风高扬!
打破一切传统价值,让新价值的朝阳辉映四方!
注释:
①、尹国均:《先锋实验》第14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②、见《非非》第九卷“非非主义流派专号”第17页,新时代出版社2002年。
③、周伦佑:《第三代诗论》,《艺术广角》1989年第一期。
④、见王一川著《中国形象诗学》第158-16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⑤、见《庞德诗选.比萨诗章》276页,黄云特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
⑥、见《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