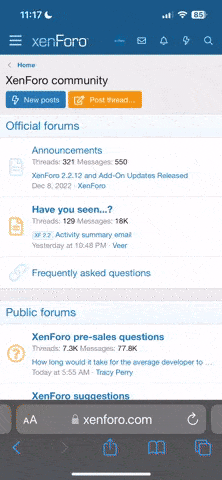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王菲画传》四十五元。
《凡高画传》五十元。
一只苹果多少钱。
如果是你在,你也会像我这样犹豫不定吧。想起你眉头皱起来的表情,我忽然笑了。
笑声好象某种物件凭空掉落在没有人的房间里,被砸得粉碎。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残存笑容的脸,房间空荡荡。是什么被砸碎了呢。午后的阳光晴好地照近来,刚洗过的头发散发着潮湿的香味,脏的马克杯泡在水槽里,床上乱得一塌糊涂。这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周末,没有任何意外事件发生,只是我。
只是我又忽然地想起了你。
春天不动声色地行进,我给自己擦了透明的唇膏和指甲油,穿着枣红色的大毛衣在人走光的宿舍里度过安静的周末夜晚。哼着调子踩了几步恰恰,空空的房间其实两个人跳舞刚合适。但现在大了一些。泡了一杯据说有减肥功效的味道怪怪的中草药,就着甜腻的奥利奥花生加巧克力夹心饼干喝下去,剩了几块怎样也吃不完。新买的杂志里有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男模,我想给人说说可是发现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曾经的那个他。盒子里的烟抽完了,我无所事事地趴在窗口看着外面突然灿烂的星空。亲爱的,如果你在,该有多好。
其实我已经不愿意去想你了。
我开始厌倦这种不厌其烦不停地想念一个人的感觉。
我知道我在自以为越来越冷漠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脆弱。
这漫无边际的想念让我对自己失去耐心。亲爱的,那你就说我虚伪吧,只要你不难过。
最近上网的时候常常都碰到他。但是我总是隐着身,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你相信吗?我真已经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我甚至都不太记得清楚他的生日了。想起那年夏天我把他指给你看的时候你用很意外的语气说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某某。你说没想到让我念念不忘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男子。我记得他戴着黑框眼镜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有一搭无一搭和和我说话,他送给我的那张什么也没有写的卡片。还有挺浪漫的夜晚他却不解风情地说月亮像只大烧饼。
记忆是一道闸,只要一打开,过去的那些人和事又都哗啦啦地冲回来,势不可挡。
可是亲爱的,那时的我们还多么的美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孤独和让我们疼得死去活来的伤害。我们像两片初生的叶子完整地连在一起。我们嘲笑过在秋天穿着牛仔短裤的中年男老师,嘲笑过在喝酒喝醉以后哭得淅沥哗啦的小女孩。我们嘲笑那些盲目无知的恋情,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也将去体会并如是地老去。
我们不知道那些年华,走得那样的迅疾。
我们只是一无所知地就各自天涯了。
然后,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有一部分在现实里,有一部分在网上。我们开始走进对方的生活一起做一些事情。偶尔也说说缠绵悱恻的话。我慢慢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尽管里面仍然终年弥漫着雾一般的忧伤。生活逐渐脱离原有的想象。比如。比如我会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和几个陌生人相约去看一座古老的教堂。比如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学校门口突然不想回去于是折身去网吧打发掉一个通宵。比如在夏天到来之前我开始学会给自己买一瓶并不昂贵的防晒油。又比如坐在双层的公车上从起点到终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去什么地方。
一年以后我仍然在这个城市里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归宿感。我还是慌慌张张地过马路,懒懒散散地说话。我还是在上课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想其他,还是在聚会的时候纵情地快乐肆意地醉生梦死。我还是这样。还是一个人,自娱自乐地写着不着边的那些风花雪月。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没有。只是在某些细小的瞬间,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你来。
哈,你该鄙视我此刻的失魂落魄。或者。
或者你也会垂下头来告诉我你也一样的难过。
在你告诉我你和那个男人的事的那个清晨,我真的很想跳起来给你一个耳光把你彻底打醒。可是我只是打着哈哈对你说要注意安全第一。我知道其实你也和我一样清醒。就如同我和你一样的无能为力。挂断电话以后我心痛得把自己整个埋到被子里,不想让妈妈听到我抽泣的声音。我一遍一遍地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直到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件无望的事情。可能这样也好。怕只怕等到你回来的那天,我们忽然发现彼此都不再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个人了。
只有在记忆里永生。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从镇上回学校的那条僻静小路上,黄昏的天空渐次暗淡下来。竟然有星星在闪烁,我抬头看着天,又看看四下的田野和升起炊烟的农家,想到自己是在异乡彼地,一时间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看到一个男人倒在荒凉的公路上,不停地抽搐着流出鲜色的血液。周围宁静安好。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男人消失了。这不过是幻觉。一股剧烈的悲怆在瞬间扼住我的咽喉,我呛得想流泪,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个暴戾天真的女孩上哪儿去了。那个在难过的时候蹲下来大声哭泣的女孩。
我再找不到她。
我只是独自一人被遗弃在这个陌生城市陌生的荒郊野外,没有一只鸟飞过。
我长时间地被那阵莫名的悲痛揪着,疲惫得提不起步子。
我想给谁打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一个人在这里大概快死了。
但脑子一片空白,我什么也没法说。
在天黑之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一个人看书,写字,吃饼干,跳舞。
在2004年某一期的《花溪》上,隰夕在她的专栏文章里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她说等你回来,我们就能够玩1978二人弹珠游戏。后来我告诉过她那是我最喜欢的句子。等你回来……好象是一个可以永远绵延下去的句式,哪怕仅仅是假设,暗藏着爱意四合的微小幸福,在我碰触到你手指的真实片刻将会被一一证实。等你回来,我会让你陪我一起吃掉巨长脂肪的奥利奥夹心饼;等你回来,我会拉着你跳一曲完整而并不优雅的恰恰;等你回来,我会告诉你那些太久没有对人说起过的任性话语;等你回来,要你在渐上浓妆的夜色里和我一起坐在双层巴士的上面肆无忌惮地一边抽烟一边看夜景。
等你回来……这样的排比句你相信我可以眼睛都不眨地一直一直写下去。因为都只是假设。
我却发现自己在一边写的同时一边捂着不住流泪的左眼。看上去很滑稽。
在写这些字的间隙里我接了一个送蛋糕的电话,穿着拖鞋去楼下拿了一只漂亮精致的草莓蛋糕,阳光刺得我的眼睛疼。桌子上已经摆着好几瓶酒和一大堆零食,晚上宿舍里有女孩过生日。想来又是会醉吧。其实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喝过酒了。和你最后一次喝酒又是什么时候呢。毕业酒?去年Snow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喝酒,一边喝一边想你。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哭。终究不是那些醉了哭了睡了忘了的小丫头了。时间过得这样的快,在分别以后的时间里我们絮絮叨叨地通过几次电话写了几封情谊绵绵的信呢。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些日子以来,我走了多远。又是如何的,忘了返回的路。
那些大片大片枯死过去的铁灰色玉米地。
那些从山涧笔直落下的寂静怀想和随流水匆匆前往的诸多感念。
那些短暂寂寞的旅行。那些天真的笑容和洁净的眼神。
我有没有告诉你。
然后。
然后是我们站在各自暮色苍茫的城市里小心翼翼地彼此惦记。我们猜测着对方生活里的细枝末节,碎碎地互相倾诉或者是长时间地不主动联络。在这里我又认识了许多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看过落日。时光好象水一样滑过我的指缝,这些日子留给我的却只是一滩潮湿的水印。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无息中被忽略了。那天我坐在面馆里看一本过期了的娱乐杂志。上面写着BEYOND的消息。亲爱的,只有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夏天,我们在炽热的气温里看他们的演唱会,傻乎乎地泪流满面。Snow把借来的《重庆森林》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都没有说话。那是怎样的夏天。
可是第三个夏季都快来了,你还不回来我身边。
对你说了很决绝的话,消失和死亡。我想你大概快哭了。你说我这样的想你你就真舍得对我说这些字眼。我闭上眼睛,你哭泣的样子在黑暗中慢慢清晰,疼痛和疲倦此消彼长地纠缠不休,我累了。
然后呢。似乎就没有然后了。
枕头下面放着你寄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我没有写完的小说。
它们安静整齐地躺在一起,好好的。
《凡高画传》五十元。
一只苹果多少钱。
如果是你在,你也会像我这样犹豫不定吧。想起你眉头皱起来的表情,我忽然笑了。
笑声好象某种物件凭空掉落在没有人的房间里,被砸得粉碎。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残存笑容的脸,房间空荡荡。是什么被砸碎了呢。午后的阳光晴好地照近来,刚洗过的头发散发着潮湿的香味,脏的马克杯泡在水槽里,床上乱得一塌糊涂。这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周末,没有任何意外事件发生,只是我。
只是我又忽然地想起了你。
春天不动声色地行进,我给自己擦了透明的唇膏和指甲油,穿着枣红色的大毛衣在人走光的宿舍里度过安静的周末夜晚。哼着调子踩了几步恰恰,空空的房间其实两个人跳舞刚合适。但现在大了一些。泡了一杯据说有减肥功效的味道怪怪的中草药,就着甜腻的奥利奥花生加巧克力夹心饼干喝下去,剩了几块怎样也吃不完。新买的杂志里有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男模,我想给人说说可是发现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曾经的那个他。盒子里的烟抽完了,我无所事事地趴在窗口看着外面突然灿烂的星空。亲爱的,如果你在,该有多好。
其实我已经不愿意去想你了。
我开始厌倦这种不厌其烦不停地想念一个人的感觉。
我知道我在自以为越来越冷漠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脆弱。
这漫无边际的想念让我对自己失去耐心。亲爱的,那你就说我虚伪吧,只要你不难过。
最近上网的时候常常都碰到他。但是我总是隐着身,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你相信吗?我真已经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我甚至都不太记得清楚他的生日了。想起那年夏天我把他指给你看的时候你用很意外的语气说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某某。你说没想到让我念念不忘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男子。我记得他戴着黑框眼镜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有一搭无一搭和和我说话,他送给我的那张什么也没有写的卡片。还有挺浪漫的夜晚他却不解风情地说月亮像只大烧饼。
记忆是一道闸,只要一打开,过去的那些人和事又都哗啦啦地冲回来,势不可挡。
可是亲爱的,那时的我们还多么的美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孤独和让我们疼得死去活来的伤害。我们像两片初生的叶子完整地连在一起。我们嘲笑过在秋天穿着牛仔短裤的中年男老师,嘲笑过在喝酒喝醉以后哭得淅沥哗啦的小女孩。我们嘲笑那些盲目无知的恋情,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也将去体会并如是地老去。
我们不知道那些年华,走得那样的迅疾。
我们只是一无所知地就各自天涯了。
然后,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有一部分在现实里,有一部分在网上。我们开始走进对方的生活一起做一些事情。偶尔也说说缠绵悱恻的话。我慢慢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尽管里面仍然终年弥漫着雾一般的忧伤。生活逐渐脱离原有的想象。比如。比如我会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和几个陌生人相约去看一座古老的教堂。比如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学校门口突然不想回去于是折身去网吧打发掉一个通宵。比如在夏天到来之前我开始学会给自己买一瓶并不昂贵的防晒油。又比如坐在双层的公车上从起点到终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去什么地方。
一年以后我仍然在这个城市里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归宿感。我还是慌慌张张地过马路,懒懒散散地说话。我还是在上课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想其他,还是在聚会的时候纵情地快乐肆意地醉生梦死。我还是这样。还是一个人,自娱自乐地写着不着边的那些风花雪月。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没有。只是在某些细小的瞬间,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你来。
哈,你该鄙视我此刻的失魂落魄。或者。
或者你也会垂下头来告诉我你也一样的难过。
在你告诉我你和那个男人的事的那个清晨,我真的很想跳起来给你一个耳光把你彻底打醒。可是我只是打着哈哈对你说要注意安全第一。我知道其实你也和我一样清醒。就如同我和你一样的无能为力。挂断电话以后我心痛得把自己整个埋到被子里,不想让妈妈听到我抽泣的声音。我一遍一遍地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直到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件无望的事情。可能这样也好。怕只怕等到你回来的那天,我们忽然发现彼此都不再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个人了。
只有在记忆里永生。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从镇上回学校的那条僻静小路上,黄昏的天空渐次暗淡下来。竟然有星星在闪烁,我抬头看着天,又看看四下的田野和升起炊烟的农家,想到自己是在异乡彼地,一时间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看到一个男人倒在荒凉的公路上,不停地抽搐着流出鲜色的血液。周围宁静安好。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男人消失了。这不过是幻觉。一股剧烈的悲怆在瞬间扼住我的咽喉,我呛得想流泪,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个暴戾天真的女孩上哪儿去了。那个在难过的时候蹲下来大声哭泣的女孩。
我再找不到她。
我只是独自一人被遗弃在这个陌生城市陌生的荒郊野外,没有一只鸟飞过。
我长时间地被那阵莫名的悲痛揪着,疲惫得提不起步子。
我想给谁打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一个人在这里大概快死了。
但脑子一片空白,我什么也没法说。
在天黑之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一个人看书,写字,吃饼干,跳舞。
在2004年某一期的《花溪》上,隰夕在她的专栏文章里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她说等你回来,我们就能够玩1978二人弹珠游戏。后来我告诉过她那是我最喜欢的句子。等你回来……好象是一个可以永远绵延下去的句式,哪怕仅仅是假设,暗藏着爱意四合的微小幸福,在我碰触到你手指的真实片刻将会被一一证实。等你回来,我会让你陪我一起吃掉巨长脂肪的奥利奥夹心饼;等你回来,我会拉着你跳一曲完整而并不优雅的恰恰;等你回来,我会告诉你那些太久没有对人说起过的任性话语;等你回来,要你在渐上浓妆的夜色里和我一起坐在双层巴士的上面肆无忌惮地一边抽烟一边看夜景。
等你回来……这样的排比句你相信我可以眼睛都不眨地一直一直写下去。因为都只是假设。
我却发现自己在一边写的同时一边捂着不住流泪的左眼。看上去很滑稽。
在写这些字的间隙里我接了一个送蛋糕的电话,穿着拖鞋去楼下拿了一只漂亮精致的草莓蛋糕,阳光刺得我的眼睛疼。桌子上已经摆着好几瓶酒和一大堆零食,晚上宿舍里有女孩过生日。想来又是会醉吧。其实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喝过酒了。和你最后一次喝酒又是什么时候呢。毕业酒?去年Snow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喝酒,一边喝一边想你。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哭。终究不是那些醉了哭了睡了忘了的小丫头了。时间过得这样的快,在分别以后的时间里我们絮絮叨叨地通过几次电话写了几封情谊绵绵的信呢。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些日子以来,我走了多远。又是如何的,忘了返回的路。
那些大片大片枯死过去的铁灰色玉米地。
那些从山涧笔直落下的寂静怀想和随流水匆匆前往的诸多感念。
那些短暂寂寞的旅行。那些天真的笑容和洁净的眼神。
我有没有告诉你。
然后。
然后是我们站在各自暮色苍茫的城市里小心翼翼地彼此惦记。我们猜测着对方生活里的细枝末节,碎碎地互相倾诉或者是长时间地不主动联络。在这里我又认识了许多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看过落日。时光好象水一样滑过我的指缝,这些日子留给我的却只是一滩潮湿的水印。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无息中被忽略了。那天我坐在面馆里看一本过期了的娱乐杂志。上面写着BEYOND的消息。亲爱的,只有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夏天,我们在炽热的气温里看他们的演唱会,傻乎乎地泪流满面。Snow把借来的《重庆森林》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都没有说话。那是怎样的夏天。
可是第三个夏季都快来了,你还不回来我身边。
对你说了很决绝的话,消失和死亡。我想你大概快哭了。你说我这样的想你你就真舍得对我说这些字眼。我闭上眼睛,你哭泣的样子在黑暗中慢慢清晰,疼痛和疲倦此消彼长地纠缠不休,我累了。
然后呢。似乎就没有然后了。
枕头下面放着你寄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我没有写完的小说。
它们安静整齐地躺在一起,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