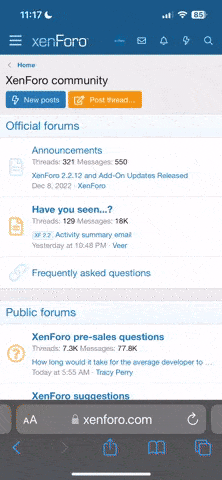飘逝的花头巾
原著名 陈建功
“她是谁?”
“她叫沈萍。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顿了顿,他忽然苦笑起来,“其实,算什么‘认识’呢,不过是――我记住了她……那是三年前,早春的一天,哦,是二月二十六号,没错儿,因为我坚持到今天这本日记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们的‘红星215号’客轮在薄雾中启锚。你到重庆坐过江轮吗?那你一定尝过这个滋味儿了:薄雾非但不散,而且越来越浓,连升起的太阳也被淹没在里面,朦朦胧胧地散着灰白色的光。能见度这样低,船是不能启航的。客轮只好停在江心,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机器停了,我走出机舱透气儿,看见四等舱外的甲板上站着一个姑娘。她不象别的旅客那样,把手掌遮在眼眉上看天呼,询问呀,咒骂呀,她不。她背靠着船舷的栏杆,娴静地看书。我真嫉妒她。她全神贯注,眼睛很亮,嘴角微微上翘,时时一颤,一颤,不知道书里有什么拨动着她的心。她很朴素,头发是并拢着梳在脑后的两根短辫,没有什么饰物。一身蓝色裤褂,只是从上衣领口里闪出了内衣的绣花领子,才可以看得出一个姑娘本能的追求。她身材修长、健美,眉清目秀,和那身朴素的装束配在一起,再加上她那读书的神态,不知为什么很吸引我……
“我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了。在BJ,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也认识不少女孩于。她们也追过我。可是我却一次恋爱也没谈过……”
“这次却一见钟情了?”
“不,还没有。我只是觉得她挺神秘,有股子让人嫉妒的傲气――不是我过去接触过的女孩子那种做作的傲气,而是……怎么说呢,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是她那捧着书本,如处无人之境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有一种凌然超人的精神优势。虽然平时我也能大谈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让那些浅薄的姑娘们投来傻子一样的目光,俨然我也成了拿破仑似的。可眼前这位姑娘却使我自惭形秽。但我又不服气。我认定她是装蒜、充大,附庸风雅……
“临近中午,雾散了。客轮全速行驶在坦阔的江面。太阳很晃眼,江面也粼粼闪光。她不再看书了,拿出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把两角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江风很猛,头巾抖开了,啪啪地甩打着,那上面印着的两只火红的凤凰在飞舞。她揪住飘闪的一角,俯在栏杆上,凝视着烟雾未尽的远方。
“我交了班,到船员餐厅去吃早饭。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发现那系着头巾的扣子已经松了。我靠在她背后的舱门上,架着胳膊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说:‘喂,别浪漫了,要刮到江里给龙王爷戴了!’她闻声回过头,赶忙把系头巾的扣子紧了紧,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嘿,她的眼眶里似乎还有泪花。我为这发现感到几分得意。‘这干嘛?联络暗号?和谁?’我是随口说的,没有什么深意,她的脸却红了,说:‘我妈妈。’我惊讶了:‘你妈妈?在哪儿?’她伸手向前方的江岸一指,说:‘在那儿!’江岸那儿,翠竹掩映,炊烟袅袅。她的妈妈就在江边那所小学校里教书。那里也是她们的家。再过十几分钟,船就经过那里。她把花头巾系在这里,是要让妈妈看见,这旁边站的就是她。‘荷,生离死别一样悲壮!’我笑她。她却晃着脑袋说:‘不是生离死别,可是……当然悲壮!’好家伙,真狂!
“她是搭船到武汉,打算换乘火车到BJ上S大学中文系的。她是很了不起。不过是初中毕业的学历,却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她很得意。当然,换上谁能不得意?!‘你没参加高考吗?’她问我。‘我?’我用棉丝擦着油污的双手,苦笑着摇头,又把那团棉丝扔到江里去了。‘男子汉大丈夫,干嘛那么熊?!’她盯着我,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我翻了翻眼皮,有点撒赖似地说:‘我认熊。’她咯咯笑起来:‘该死!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跳江里去算啦!我就不认熊!不认熊,也不认命!我妈是右派――她说她不是!可爸爸把我们甩了,一个人“革命”去了!我妈从小就教我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哼,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现在怎么样!’她张开五指,一下一下地推着在脸颊前翻卷的花头巾,象是在欣赏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我不知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也许,和一个姑娘偶尔相遇,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使你终生难以忘怀。她就是这样忽然充满了我的心间。你别误会。她给我留下的,不光是一种单纯的温馨、美好的回忆,不,不只是这些。那次对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见她。我只能时时从机房里探出头来,远远看着她在落日的余晖里,在猿猱的悲啸声中读书的身影: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栏杆上架起双脚,仰着头枕在靠背上,举着书,一动也不动。江水在下面奔涌。青山如削,拂面而过……关于她的奋斗,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也许,在襁褓中她就开始和妈妈一起经历人生的沧桑了?可是现在,她多得意啊,多自豪啊!而我,不错,也受过四、五年罪,现在还忘不了咒骂。可是除了咒骂,哦,还有除了对中西菜点的谙熟,我还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
“我从这一天开始向自己宣战了。拚命,苦读。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朝天发誓……当然,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她,我会象以前一样,把多少次奋斗计划变成灰烬。可是这一次我成功了。因为她那身姿、神态、话语,那飘动的花头巾,一直在我眼前闪,在我耳边响。我当时的誓言你听起来一定会笑――我下决心也要考上S大学中文系,我要去见她……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当然也因为过去就喜欢,但也许更因为她学的是文学。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后来,渐渐的,才华、毅力、激情,这些我早已陌生的东西,似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读、写作、劳动;自然、社会、人……一切开始充满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可是,我的眼前仍然离不开她的身影,这个向陷在生活泥潭里的我投来第一根绳子的姑娘――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我的心底确确实实萌发了一种渴望。也许这就叫爱情?反正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自豪地站到她面前,在她惊异的目光中告诉她:‘都是因为见到了你!’”
“嘟嘟――”一辆接一辆载重卡车轰隆隆驶过马路,打破了街心花园里的宁静。车上,钢条铁管咣当乱响,沉重的引擎声在夜空飘荡。倒霉!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以后,秦江的声音也不再出现了。
我瞟了他一眼。他的脸膛遮在黑黝黝的树影里,嘴唇紧闭,只有眸子里闪着冷峻的光。
我似乎已经摸到他心中的伤痛了,叹了一口气,不无同情地对他说:“我明白了。你是爱上她了。是不是这次你终于考上S大学中文系以后,见到她时,她已经……”
他没答腔。
“嗨,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点,慢慢你就会好的。”我劝他。
他摇摇头:“你理解错了。”
“怎么?”
“真象你猜的,倒也没什么了。当然,我会痛苦,但我能想得开。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到底怎么了呢?”
“在‘红星’轮上见过的那位姑娘,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癌症?!”我惊叫起来。
他一怔。然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摇头。
“我一到S大学,就急着找她。我不知道姓名,也不好意思打听。我常常留意眼前走过的每一个女同学。我敢说,只要她一出现,我会立即认出她来。因为这两年里,她在我的梦中,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秦江和我走出街心花园,沿一盏一盏高压水银灯照耀下的人行道,走回宾馆。我们两个的身影,一会儿长长长,一会儿短短短,一会儿又长长长。他的声调依然是沉稳的,仿佛每一句都是从心灵深处缓缓流出的。
“那你到底见到她没有呢?”
“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到校二十多天以后了。系里召开庆祝国庆三十一周年的联欢会,全系同学聚在一起。先是表演节目,然后随便围成一个一个圆圈,击鼓传花。咚咚的鼓声很是扣人心弦,每个人拿到那朵纸花以后,都象触了电一样扔给下一个人。礼堂里一片欢声笑语。
“说实话,我哪有什么玩的兴致。我知道她就在这里,在这几百人中间。可是,她什么时候能站到我的面前啊。
“我的希望没有落空。终天有一次,旁边一个圈子里又响起一片欢呼。鼓声停了,人群里推推搡出一个姑娘。这就是她!我一眼认出来了,是她!她的装束有些改变,穿着灰色夹银丝的西式上衣,端庄、大方。发式也已经不是短辫,蓬松地束成一把,甩在肩后。比轮船上见的她更显得有些魅力了。难怪我难以从人群里一下子认出她来!她还是那么自信,落落大方,没有再跟旁边‘耍赖’的女同学们费口舌,绷了绷微微上翘的嘴唇,走到圈子中央抽了签。按照签子上写的,她要在两分钟以内猜出一个刁钻古怪的谜语。她没有猜出来,只好又按照签子上写的惩罚办法,到一个彩色的竹篓里去摸一个‘未来的爱人’。
“同学们又欢呼起来。不知这是谁设计的恶作剧,而又偏偏让她赶上了。不管从那竹篓里摸出的字条上写的是‘中山狼’还是‘武大郎’,被罚的人都要向大家宣布这是自己‘未来的爱人’。尽管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她还是咬起下唇,眼睛里闪着紧张的光,把手伸向竹篓里了。唉,想来真可笑,与其说她紧张,不如说我比她更紧张――虽然她不知道。我心中好象觉得,她伸手抓出的字条,冥冥中和我有什么关联----这一切,是在我刚刚认出她来的时候发生的呀!
“她摸出字条了。她打开看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咚咚乱跳起来。那字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使得她的脸飞红了,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她双手一拍,情不自禁地喊:‘哎呀!真赚!’同学们都笑起来。有的高喊:‘快念念!怎么这么激动?’‘一定非常非常如意!’她这才明白过来,红着脸,跺着脚喊:‘我不是那意思!我才不是那意思呢!’……大家笑得更开心了。那字条终于被别的同学抢过来读了。那上面写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在同学们更猛烈的笑喊声中,那个读条的男同学还一本正经地走过去,伸手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把右手甩到了身后,这又引起全场一片戏谑的笑……
“尽管她抽到了最好的一张字条,尽管这个玩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快乐,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是滋味儿。联欢会散了,我没有象多少次梦想过的那样,突然走到她的面前。甚至当她拖着椅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也没动声色。她的脸颊上,仍然泛着刚才兴奋的红晕。她也没认出我来。
“为这,我暗自谴责了自己多少次。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褊狭。褊狭到因为一场游戏而耿耿于怀。是因为爱情的自私,还是因为别的?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到她的宿舍去了。‘还认得我吗?’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好象正为什么伤心,眼角还有泪痕。她吃惊地打量着我,抱歉地摇头。我说:‘荷,找到了风度翩翩,前途无量的爱人,就把什么都忘了!’她显然没心思和我开玩笑,垂下眼睑,说:‘别闹。你到底是谁?’我说:‘一个险些跳到长江里去的认“熊”的水手。’‘是你?’她盯着我,接着,是我已经见过的那样子: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双手一拍,笑着喊:‘哎呀,我想起来了!’她把我让进屋,心情却很快又回到了刚才的抑郁之中,强打出微笑,可又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我盯着她的眼睛,拿出船上初见时的口气,逗她说:‘干嘛?又是生离死别?和谁?这回不悲壮了?你的花头巾呢?’她没有回答我,懒洋洋地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那上面就蒙着那块印着凤凰的花头巾。她心不在焉,凝视窗外。外面,秋雨丝一样飘拂。我真希望她问我怎么也报考了这里,希望她问问我这两年来经历的一切。可是,她的心思好象根本不在这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我开口了:‘你……这两年过得还好吗?’她拿手指往床上划着:‘有什么好不好的。象我们这样的人,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再混一年,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个教书匠,心满意足……’话,是冷冷的,最后还苦笑了一声,补充道:‘比我妈妈那个教书匠强一点。她教小学,我教中学……’我吃了一惊,忽然觉得她很陌生。问她到底有什么不顺心,她抿了抿嘴唇,没有立刻回答我。可是,她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泪水……
“嗨,其实,不过是因为她们班里的几位同学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全班同学那么多,叫上谁或者不叫谁,都是有可能的呀。可是,谁能体会得到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进入堂皇学府以后的敏感和悲哀?她说她们几个人看不起她,就是!――她既没听过玛祖卡和波尔卡,也不知道德拉克罗瓦;她没有一个亲朋是什么名流、学者,于是也就从来没有勇气去敲任何一位教授的家门。她说她们一定嫌她‘土’,因为她只能象傻子一样,在旁边听她们那些高雅、时髦的奇谈, 便插上两句话,也多半充当了她们的笑料……她那么认真。激愤,不平,不断从鼻腔里吐出斩钉截铁的‘哼’声,是蔑视?是不服气?还是‘走着瞧’的挑战?都有。这神态,和当年在船上向我诉说身世遭遇时一模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非但不再激起当年的情感,反而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怅惘和忧虑。好象我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里,这时才突然发现,原来也有败叶和秋光一起生长。她讲的,即使都是真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在我们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许许多多从荆天棘地里挺拔出来的云杉,自然也生长着不少从幸运的土地上萌发起的根苗。这里,有自命为‘拼命委员会’的学习小组,有媳灯以后仍然躲在盥洗间里背单词的青年,也有时髦之士、风流人物等,有诸熟‘终南捷径’,在出版部门、学术团体进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奇怪的倒是她,何至于对一次小小的秋游耿耿于怀,何至于因为一些浅薄的嘲笑而不安?噢,怪不得她桌上摆满了《肖邦》、《贝多芬传》之类,刚才还以为她在攻艺术史,原来她是为了知道玛祖卡和波尔卡。原来她的心里,埋藏着一颗虚荣的种子……
应该说,我对她的过去了解得还是那样少。我不知道,她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是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吗?
“是啊,我的失望就在这里。她梦寐以求的,只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发现,她猛背莫奈、梵高、马蒂斯和毕加索;她学会了不知是从喉咙还是鼻腔里不时地滚出一句‘唔嗯?’截断别人的谈话。是首肯、认可?还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鬼知道!反正这是现今最时髦的语气词――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位从人家外国留学生那里批发来的。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总算打听到了她妈妈过去的一位学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她要去拜访他,请他推荐稿子,引见名流。终于有一天的中午,她又在路上遇到了我,得意洋洋地说,她把那些小看她的人给‘镇’了――那些人拿着某学者的推荐信,去拜访文学研究所的高唐教授,万没想到遇上她正在客厅里和高先生谈笑风生,把那些人看傻了!这两天还接二连三地问:‘你怎么和高先生这么熟?’……她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次,她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她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也许,她那几位同学不敢再小看她了?她可以加入他们那一伙儿了?看着她那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冷冷地打断她,说:‘真值得祝贺。’我走了。
“那天,我在石榴湖边的长椅上呆了一下午。早春的风沙打着旋儿,在身前身后飞舞。我的眼前却总是出现她――上大学以后见到的她和‘红星215轮’上那个霞光水色中读书的身影。也许,我没有什么力量干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只能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熬煎着失望的痛苦。我想,难道她奋斗了半天,是要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难道我奋斗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那里,是断送一个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华的泥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的啊!哦,挣扎,想起了那次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挣扎,眼前蓦然闪亮在暮色中的路灯,又蓦地使我心头发热――你为什么不快去找她?你怎么能不去找她……
“她正准备出门,说是有事。什么事?把头发一圈一圈裹上头顶,身上飘散出淡淡的檀香。中午我那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好象并没使她心存芥蒂,她的表情比以往更温柔,闪着眸子看我――但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她将赴的约会。她向我投来抱歉的笑,说她最近太忙。她说她猜到了我找她干什么。本来嘛,初入校门,她理该为‘老朋友’引见一些名人。可惜太忙了。放心,她不会忘记的,不会的,更何况大家都同是来自巴山蜀地的‘小人物’……我脸红了,一种受侮辱的感觉使我的脑血管突突跳。窗外,对面宿舍楼闪烁的灯光好象突然飞炸成无数碎片,扑头盖脸而来。我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过了好久,才能用稍稍冷静的声音告诉她,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她问我,那有什么别的事吗?我说:‘没有。’我告辞了。
“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号,那天晚上我们S大学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男排在世界杯预选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校园里一片欢腾。同学们欢呼着,敲盆打碗,不击烂不尽心头之快。‘砰砰’的暖瓶炸裂声此伏彼起。几千人冲出宿舍楼,点起火炬,一把小号高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围着石榴湖游行,欢庆通宵……走在这支队伍里,我流下了眼泪。我忽然发现,那么多同学,他们过去是奋斗者,现在仍然是奋斗者,不少人过去的奋斗,也许不过是因为对不平遭遇的反抗,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了新的奋斗支点。多么好啊,这里,多少慷慨悲歌之士,为国为民的精英……而沈萍,她在干什么?她会为这一切激动吗?会吗?我想起‘植树节’那天,全系去京郊山区植树,她和我碰巧坐在一辆大轿车上。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开进山区,间或可以看见山坡上几间石块垒成的小房,几个放羊的孩子。她忽然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我膘了她一眼,说:‘你庆幸自己,是吗?’她微微点头,自言自语似地说:‘当然,如果没有今天,糊里糊涂,也许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可是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她说的,是真话。她不堪回首往事。她充满了摆脱命运的漩涡,进入一种新生活、新天地的庆幸。她绝不想想自己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还应该有什么关系。大概,生活中也还会有激起她不平,鼓舞她奋斗的东西,但绝不会是这些,绝不会。会是什么呢?可能只是一个白眼,可能只是一次冷遇……唉,奋斗者,不尽然那么伟大,不尽然,是吗?
“我连夜给她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我问她是不是感觉到了被人生的浊流裹挟去的危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浸漫着一股多.么可悲的浊流啊。我诉说我的担心,担心她在背‘名人辞典’,广交名流的浮华中毁了自己……当然,我很动感情。我向她吐露了那年‘红星’轮相遇以后,从心底渐渐萌发的情感,我承认这是爱。我说,正是因为那难以磨灭的爱,才促使我向她倾诉我的担心和希望。
“……这件事办得这样不理智。我后来才听说,这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某学者(恕我不讲姓名)的儿子――一切都应了‘击鼓传花’得的预言: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而我在她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更何况,我还讲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傻瓜也不会写这样的情书的。
“以后,我们偶尔相遇时,还互相点点头,打一个简单的招呼,但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她给我下的结论是――嫉妒,假正经,还故作多情……”
秦江把双手抬到胸前,交迭十指掰着、按着,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他没有说下去,脸色很难看。一盏一盏水银灯下,我们的身影还是短短短,长长长。
“就完了?”
“唔,应该说是完了。”顿了顿,他又说,“可又象是没完。要不,我干嘛还要管闲事,给自己招来痛苦?”
四
前面是通向宾馆转门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了门,宽敞的会客大厅空无一人。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来。
“上星期六晚上,在无轨电车上,好象是你喊我。我没理你,是吗?”
我点头,一笑。
“就是因为那件事。我很烦躁。”
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我是到首都剧场看戏去了。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朋友,哦,也是过去在‘老莫’和‘康乐’泡过的朋友。他爸爸是搞外事工作的。”
“他和沈萍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他在外地,来BJ出差的。可是在闲扯中,我很意外地听说他的妹妹――一个过去我也认识的女孩子――在谈恋爱,男方的爸爸就是某学者。我吃了一惊,追问了一句,原来那个男的,就是沈萍的男朋友。”
“真的?!”
“我当时也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知道那个男的和沈萍的事。他不屑一提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S大的一位四川妞儿,死缠着他。他告诉我妹妹:烦透她了!我寻思这小子也不安好心,耍耍人家呗……嗨,他当然追我妹妹。他想出国!他有几封教授的推荐信,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混上奖学金,他让我家老头子走走门子,给催催……’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进去。我的脊梁上透过一股寒气。我只想着沈萍。又是浊流!社会的浊流!人生的浊流!而沈萍在这中间算得了什么呀!随波浮沉的一根小草。可悲的是她不知道这些。是的,她不知道。这两天,她不是得意地讲她的男朋友要出国了吗。唉,她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准备挂起她的花头巾了。可是她想到没有,那挂着花头巾的航船正冲向礁石呀……
“回学校的电车上,我连买车票的话都懒得说,当然也没有兴趣回答你的招呼。我只是一遍一遍问自己:告诉她呜?告诉她吗?告诉她,她能相信吗?她不会又一次说你嫉妒、挑拨?再者,那位剧场偶遇的朋友,他说话的可信性有多少哇!缄口不言?这痛苦还不仅在良心上,而且在更隐秘的感情深处!我这时才发现,爱情,尤其是初恋的爱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我得到了那样的回报,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时时回味起那晨雾、远村、坦阔的江面,飘拂的头巾……更何况在现在!在现在!
“回到宿舍,已经熄灯了。默默地躺到床上。同屋的几位正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某某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宝钗’式的人物啦,‘好生生一个清白女子,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啦,谁谁如何‘交游干谒’有道,正进行出国留学的‘秘密外交’啦……我烦透了。浊流,四处漫延的浊流。一股什么火儿升起来,我怒吼一声:‘算了!睡吧!’把他们吓哑了。我呢,却一夜也没睡着。
“清晨起来,我决定把一切告诉她。猜疑、臭骂都可以,反正我尽自己的责任。
“吃早饭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就在那张桌子旁。我端着碗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很惊讶,疑惑地向我点点头。我默默吃了几口面包,说:‘沈萍,你……你过得还好吗?’――天!这叫什么话,连我自己都怀疑这话里有什么‘不良居心’了。‘过得挺好。’她瞟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猜忌,又有挑战。我说:“听说,他……你们那位,要出国留学了?’她说:‘没有。去通过“托夫”了,还要等护照。再过个把月吧。’她老练多了。得意、自豪,全隐藏在漫不经心里。‘托夫’、‘护照’……知道吗?最时髦的名词儿,说得越漫不经心,越时髦。我还能往下说什么呢?我知道,我要说的一切肯定会招来什么。我犹豫了,舌头打了卷儿。
“看来,我只能采取一个最愚蠢的行动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幸亏它没能实现。那可能是我身上消失了多年的干部子弟气质的偶然再现吧。当时,我打听到了她那位男朋友的地址。我决定去找他谈一谈,问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耍这个来自小乡镇的姑娘。真是那样,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他一番,直到他认错为止……多浪漫,骑士一般!当时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个念头。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去了。
“他没在家。他的妈妈说他很忙。护照早就领到了,后天就要飞美洲了。这个消息更使我相信,沈萍的悲剧为期不远了――他这么快就要走了,看来沈萍并不知道哇。
“我在门口勾留了片刻,只好离开了他的家。走出楼门,忽然看见沈萍和一个小伙子远远携手而来。我闪到一旁。她穿着一件时新的银灰色绸料衬衫,丝带束着腰,衬出窈窕的身姿。近胯处的腰带结子随着她的走动而跳跃,飘洒、大方,已经看不出一个外省姑娘的丝毫痕迹。她一定自认为是幸福的,幸福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她绝不会想到等在自己前面的是什么!而我,只能用目光尾随着,看她跟着他走进了那黑森森的楼门。
“天黑了,楼房噼噼啪啪亮起一方一方灯光。几滴雨点飘下来,打到身上。我没有离开,在楼前的马路上徘徊。
“三层,最东边那个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上映出两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他们。也许,现在就是他向她摊牌的时候。大概过不了一会儿,沈萍会流着泪冲下楼来,跌撞着走进微雨之中。天这么晚了,我留在这儿会有些用处。至少,我要远远跟在她的身后,和她一起坐上回学校的汽车,再远远跟在她的身后,目送她走进女生宿舍楼……可是,我又多么害怕看见她跑出来。哦,不,还是跑出来吧……
“十点钟了,窗帘上的身影还在动。一个身影――那是她,她在梳头。我凝神注视着。这姿态我是熟悉的。三年前,在‘红星215’轮上,曙色初开,船过神女峰。她站在船舷,仰脸望峰。江风吹起她的秀发,她的右手也拿着一把梳子,顺着风势,一下,两下……那亭亭玉立的身姿,使站在机房门口的我凝视很久。可是,现在……突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又咚咚急跳起来,因为我看见那个窗户里的灯一下熄了。‘啪啪啪啪’,我踏着马路上耀眼的水窝,几步冲到最东边一个门,嗵嗵地向楼上跑去……
“我还是理智的。我跑到二层时收住了脚步。我问自己:‘你去干什么?’我退下楼来了,走出楼门,闭上眼睛,仰脸让雨水滴打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班驳的路,慢慢地走了。走了几十步,我又回来,默对着那黑黝黝的窗口。我感到心酸。为沈萍,为她妈妈,也为我自己。但愿我在首都剧场听到的那一席话,全是胡扯、谎话、瞎说八道!但愿如此。可是,即便如此,沈萍就幸福了吗?一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她会感到永远幸福吗……我又想,说不定沈萍完了,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浅薄付出了牺牲。可也许,值得庆幸的是,这又使她回到我们中间,重新思索一下生活……如果真能那样,我将把今天晚上所见到的一切永远埋在心底,永远。可能的话,我还会对她说,我仍然爱着她……”
秦江不再讲了,仰头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好象在努力平息情感的波涛。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向眼前缭绕的烟雾使劲儿吹去。结果呢,更多的烟雾在我们的身边飘游。
“后来呢,沈萍怎么样了?”
“不知道。这是前天才发生的事。”
我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瞥了我一眼,用手把面前的烟雾撩开:“你叹什么气?我不是说啦,这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只能使我们警醒、思考、坚定。”
“是这样的。”我点头,“……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和你不见你的爸爸有什么关系?”
“哦,”他笑了,“我险些忘了。”沉吟了一下,他说:“也许,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情了。戴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我爸爸面前----得意吗?得意。可好象又觉得挺没意思。我想起了‘红星215’轮上那块花头巾。人生的道路还长,我为自己设计的这种得意场面感到羞愧。其次呢,我不知道你预感到没有,人们一旦知道秦江是谁,会给我特殊的恩宠,不少老朋友们又会拉我去作‘老莫’、‘康乐’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毅力经受这些了。说真的,这都要感谢沈萍。她使我想许多问题----关于奋斗者。关于人生。”
“那你就永远不去见你父亲了?”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失去这戏剧性的场面,我毕竟有些遗憾。
秦江又笑了:“你何必过于执。等心情好了,我随时都可能回家去看他。不过对你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个儿子回家看看父亲,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我们一起等电梯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作品?我觉得,这件事里倒有不少深意。”
“怎么写?都是同学,又还都在学校。写出来不是惹麻烦吗!”他摇头,忽然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感兴趣,你写。”
我说:“真的?”
“谁写不一样!我又没登记‘专利’。”他沉思片刻,又说:“再说,我要向沉萍讲的,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才能表达了。而这只有由你来说才合适……”
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原著名 陈建功
“她是谁?”
“她叫沈萍。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顿了顿,他忽然苦笑起来,“其实,算什么‘认识’呢,不过是――我记住了她……那是三年前,早春的一天,哦,是二月二十六号,没错儿,因为我坚持到今天这本日记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们的‘红星215号’客轮在薄雾中启锚。你到重庆坐过江轮吗?那你一定尝过这个滋味儿了:薄雾非但不散,而且越来越浓,连升起的太阳也被淹没在里面,朦朦胧胧地散着灰白色的光。能见度这样低,船是不能启航的。客轮只好停在江心,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机器停了,我走出机舱透气儿,看见四等舱外的甲板上站着一个姑娘。她不象别的旅客那样,把手掌遮在眼眉上看天呼,询问呀,咒骂呀,她不。她背靠着船舷的栏杆,娴静地看书。我真嫉妒她。她全神贯注,眼睛很亮,嘴角微微上翘,时时一颤,一颤,不知道书里有什么拨动着她的心。她很朴素,头发是并拢着梳在脑后的两根短辫,没有什么饰物。一身蓝色裤褂,只是从上衣领口里闪出了内衣的绣花领子,才可以看得出一个姑娘本能的追求。她身材修长、健美,眉清目秀,和那身朴素的装束配在一起,再加上她那读书的神态,不知为什么很吸引我……
“我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了。在BJ,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也认识不少女孩于。她们也追过我。可是我却一次恋爱也没谈过……”
“这次却一见钟情了?”
“不,还没有。我只是觉得她挺神秘,有股子让人嫉妒的傲气――不是我过去接触过的女孩子那种做作的傲气,而是……怎么说呢,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是她那捧着书本,如处无人之境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有一种凌然超人的精神优势。虽然平时我也能大谈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让那些浅薄的姑娘们投来傻子一样的目光,俨然我也成了拿破仑似的。可眼前这位姑娘却使我自惭形秽。但我又不服气。我认定她是装蒜、充大,附庸风雅……
“临近中午,雾散了。客轮全速行驶在坦阔的江面。太阳很晃眼,江面也粼粼闪光。她不再看书了,拿出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把两角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江风很猛,头巾抖开了,啪啪地甩打着,那上面印着的两只火红的凤凰在飞舞。她揪住飘闪的一角,俯在栏杆上,凝视着烟雾未尽的远方。
“我交了班,到船员餐厅去吃早饭。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发现那系着头巾的扣子已经松了。我靠在她背后的舱门上,架着胳膊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说:‘喂,别浪漫了,要刮到江里给龙王爷戴了!’她闻声回过头,赶忙把系头巾的扣子紧了紧,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嘿,她的眼眶里似乎还有泪花。我为这发现感到几分得意。‘这干嘛?联络暗号?和谁?’我是随口说的,没有什么深意,她的脸却红了,说:‘我妈妈。’我惊讶了:‘你妈妈?在哪儿?’她伸手向前方的江岸一指,说:‘在那儿!’江岸那儿,翠竹掩映,炊烟袅袅。她的妈妈就在江边那所小学校里教书。那里也是她们的家。再过十几分钟,船就经过那里。她把花头巾系在这里,是要让妈妈看见,这旁边站的就是她。‘荷,生离死别一样悲壮!’我笑她。她却晃着脑袋说:‘不是生离死别,可是……当然悲壮!’好家伙,真狂!
“她是搭船到武汉,打算换乘火车到BJ上S大学中文系的。她是很了不起。不过是初中毕业的学历,却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她很得意。当然,换上谁能不得意?!‘你没参加高考吗?’她问我。‘我?’我用棉丝擦着油污的双手,苦笑着摇头,又把那团棉丝扔到江里去了。‘男子汉大丈夫,干嘛那么熊?!’她盯着我,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我翻了翻眼皮,有点撒赖似地说:‘我认熊。’她咯咯笑起来:‘该死!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跳江里去算啦!我就不认熊!不认熊,也不认命!我妈是右派――她说她不是!可爸爸把我们甩了,一个人“革命”去了!我妈从小就教我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哼,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现在怎么样!’她张开五指,一下一下地推着在脸颊前翻卷的花头巾,象是在欣赏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我不知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也许,和一个姑娘偶尔相遇,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使你终生难以忘怀。她就是这样忽然充满了我的心间。你别误会。她给我留下的,不光是一种单纯的温馨、美好的回忆,不,不只是这些。那次对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见她。我只能时时从机房里探出头来,远远看着她在落日的余晖里,在猿猱的悲啸声中读书的身影: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栏杆上架起双脚,仰着头枕在靠背上,举着书,一动也不动。江水在下面奔涌。青山如削,拂面而过……关于她的奋斗,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也许,在襁褓中她就开始和妈妈一起经历人生的沧桑了?可是现在,她多得意啊,多自豪啊!而我,不错,也受过四、五年罪,现在还忘不了咒骂。可是除了咒骂,哦,还有除了对中西菜点的谙熟,我还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
“我从这一天开始向自己宣战了。拚命,苦读。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朝天发誓……当然,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她,我会象以前一样,把多少次奋斗计划变成灰烬。可是这一次我成功了。因为她那身姿、神态、话语,那飘动的花头巾,一直在我眼前闪,在我耳边响。我当时的誓言你听起来一定会笑――我下决心也要考上S大学中文系,我要去见她……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当然也因为过去就喜欢,但也许更因为她学的是文学。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后来,渐渐的,才华、毅力、激情,这些我早已陌生的东西,似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读、写作、劳动;自然、社会、人……一切开始充满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可是,我的眼前仍然离不开她的身影,这个向陷在生活泥潭里的我投来第一根绳子的姑娘――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我的心底确确实实萌发了一种渴望。也许这就叫爱情?反正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自豪地站到她面前,在她惊异的目光中告诉她:‘都是因为见到了你!’”
“嘟嘟――”一辆接一辆载重卡车轰隆隆驶过马路,打破了街心花园里的宁静。车上,钢条铁管咣当乱响,沉重的引擎声在夜空飘荡。倒霉!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以后,秦江的声音也不再出现了。
我瞟了他一眼。他的脸膛遮在黑黝黝的树影里,嘴唇紧闭,只有眸子里闪着冷峻的光。
我似乎已经摸到他心中的伤痛了,叹了一口气,不无同情地对他说:“我明白了。你是爱上她了。是不是这次你终于考上S大学中文系以后,见到她时,她已经……”
他没答腔。
“嗨,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点,慢慢你就会好的。”我劝他。
他摇摇头:“你理解错了。”
“怎么?”
“真象你猜的,倒也没什么了。当然,我会痛苦,但我能想得开。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到底怎么了呢?”
“在‘红星’轮上见过的那位姑娘,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癌症?!”我惊叫起来。
他一怔。然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摇头。
“我一到S大学,就急着找她。我不知道姓名,也不好意思打听。我常常留意眼前走过的每一个女同学。我敢说,只要她一出现,我会立即认出她来。因为这两年里,她在我的梦中,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秦江和我走出街心花园,沿一盏一盏高压水银灯照耀下的人行道,走回宾馆。我们两个的身影,一会儿长长长,一会儿短短短,一会儿又长长长。他的声调依然是沉稳的,仿佛每一句都是从心灵深处缓缓流出的。
“那你到底见到她没有呢?”
“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到校二十多天以后了。系里召开庆祝国庆三十一周年的联欢会,全系同学聚在一起。先是表演节目,然后随便围成一个一个圆圈,击鼓传花。咚咚的鼓声很是扣人心弦,每个人拿到那朵纸花以后,都象触了电一样扔给下一个人。礼堂里一片欢声笑语。
“说实话,我哪有什么玩的兴致。我知道她就在这里,在这几百人中间。可是,她什么时候能站到我的面前啊。
“我的希望没有落空。终天有一次,旁边一个圈子里又响起一片欢呼。鼓声停了,人群里推推搡出一个姑娘。这就是她!我一眼认出来了,是她!她的装束有些改变,穿着灰色夹银丝的西式上衣,端庄、大方。发式也已经不是短辫,蓬松地束成一把,甩在肩后。比轮船上见的她更显得有些魅力了。难怪我难以从人群里一下子认出她来!她还是那么自信,落落大方,没有再跟旁边‘耍赖’的女同学们费口舌,绷了绷微微上翘的嘴唇,走到圈子中央抽了签。按照签子上写的,她要在两分钟以内猜出一个刁钻古怪的谜语。她没有猜出来,只好又按照签子上写的惩罚办法,到一个彩色的竹篓里去摸一个‘未来的爱人’。
“同学们又欢呼起来。不知这是谁设计的恶作剧,而又偏偏让她赶上了。不管从那竹篓里摸出的字条上写的是‘中山狼’还是‘武大郎’,被罚的人都要向大家宣布这是自己‘未来的爱人’。尽管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她还是咬起下唇,眼睛里闪着紧张的光,把手伸向竹篓里了。唉,想来真可笑,与其说她紧张,不如说我比她更紧张――虽然她不知道。我心中好象觉得,她伸手抓出的字条,冥冥中和我有什么关联----这一切,是在我刚刚认出她来的时候发生的呀!
“她摸出字条了。她打开看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咚咚乱跳起来。那字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使得她的脸飞红了,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她双手一拍,情不自禁地喊:‘哎呀!真赚!’同学们都笑起来。有的高喊:‘快念念!怎么这么激动?’‘一定非常非常如意!’她这才明白过来,红着脸,跺着脚喊:‘我不是那意思!我才不是那意思呢!’……大家笑得更开心了。那字条终于被别的同学抢过来读了。那上面写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在同学们更猛烈的笑喊声中,那个读条的男同学还一本正经地走过去,伸手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把右手甩到了身后,这又引起全场一片戏谑的笑……
“尽管她抽到了最好的一张字条,尽管这个玩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快乐,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是滋味儿。联欢会散了,我没有象多少次梦想过的那样,突然走到她的面前。甚至当她拖着椅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也没动声色。她的脸颊上,仍然泛着刚才兴奋的红晕。她也没认出我来。
“为这,我暗自谴责了自己多少次。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褊狭。褊狭到因为一场游戏而耿耿于怀。是因为爱情的自私,还是因为别的?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到她的宿舍去了。‘还认得我吗?’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好象正为什么伤心,眼角还有泪痕。她吃惊地打量着我,抱歉地摇头。我说:‘荷,找到了风度翩翩,前途无量的爱人,就把什么都忘了!’她显然没心思和我开玩笑,垂下眼睑,说:‘别闹。你到底是谁?’我说:‘一个险些跳到长江里去的认“熊”的水手。’‘是你?’她盯着我,接着,是我已经见过的那样子: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双手一拍,笑着喊:‘哎呀,我想起来了!’她把我让进屋,心情却很快又回到了刚才的抑郁之中,强打出微笑,可又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我盯着她的眼睛,拿出船上初见时的口气,逗她说:‘干嘛?又是生离死别?和谁?这回不悲壮了?你的花头巾呢?’她没有回答我,懒洋洋地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那上面就蒙着那块印着凤凰的花头巾。她心不在焉,凝视窗外。外面,秋雨丝一样飘拂。我真希望她问我怎么也报考了这里,希望她问问我这两年来经历的一切。可是,她的心思好象根本不在这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我开口了:‘你……这两年过得还好吗?’她拿手指往床上划着:‘有什么好不好的。象我们这样的人,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再混一年,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个教书匠,心满意足……’话,是冷冷的,最后还苦笑了一声,补充道:‘比我妈妈那个教书匠强一点。她教小学,我教中学……’我吃了一惊,忽然觉得她很陌生。问她到底有什么不顺心,她抿了抿嘴唇,没有立刻回答我。可是,她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泪水……
“嗨,其实,不过是因为她们班里的几位同学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全班同学那么多,叫上谁或者不叫谁,都是有可能的呀。可是,谁能体会得到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进入堂皇学府以后的敏感和悲哀?她说她们几个人看不起她,就是!――她既没听过玛祖卡和波尔卡,也不知道德拉克罗瓦;她没有一个亲朋是什么名流、学者,于是也就从来没有勇气去敲任何一位教授的家门。她说她们一定嫌她‘土’,因为她只能象傻子一样,在旁边听她们那些高雅、时髦的奇谈, 便插上两句话,也多半充当了她们的笑料……她那么认真。激愤,不平,不断从鼻腔里吐出斩钉截铁的‘哼’声,是蔑视?是不服气?还是‘走着瞧’的挑战?都有。这神态,和当年在船上向我诉说身世遭遇时一模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非但不再激起当年的情感,反而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怅惘和忧虑。好象我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里,这时才突然发现,原来也有败叶和秋光一起生长。她讲的,即使都是真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在我们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许许多多从荆天棘地里挺拔出来的云杉,自然也生长着不少从幸运的土地上萌发起的根苗。这里,有自命为‘拼命委员会’的学习小组,有媳灯以后仍然躲在盥洗间里背单词的青年,也有时髦之士、风流人物等,有诸熟‘终南捷径’,在出版部门、学术团体进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奇怪的倒是她,何至于对一次小小的秋游耿耿于怀,何至于因为一些浅薄的嘲笑而不安?噢,怪不得她桌上摆满了《肖邦》、《贝多芬传》之类,刚才还以为她在攻艺术史,原来她是为了知道玛祖卡和波尔卡。原来她的心里,埋藏着一颗虚荣的种子……
应该说,我对她的过去了解得还是那样少。我不知道,她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是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吗?
“是啊,我的失望就在这里。她梦寐以求的,只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发现,她猛背莫奈、梵高、马蒂斯和毕加索;她学会了不知是从喉咙还是鼻腔里不时地滚出一句‘唔嗯?’截断别人的谈话。是首肯、认可?还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鬼知道!反正这是现今最时髦的语气词――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位从人家外国留学生那里批发来的。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总算打听到了她妈妈过去的一位学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她要去拜访他,请他推荐稿子,引见名流。终于有一天的中午,她又在路上遇到了我,得意洋洋地说,她把那些小看她的人给‘镇’了――那些人拿着某学者的推荐信,去拜访文学研究所的高唐教授,万没想到遇上她正在客厅里和高先生谈笑风生,把那些人看傻了!这两天还接二连三地问:‘你怎么和高先生这么熟?’……她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次,她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她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也许,她那几位同学不敢再小看她了?她可以加入他们那一伙儿了?看着她那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冷冷地打断她,说:‘真值得祝贺。’我走了。
“那天,我在石榴湖边的长椅上呆了一下午。早春的风沙打着旋儿,在身前身后飞舞。我的眼前却总是出现她――上大学以后见到的她和‘红星215轮’上那个霞光水色中读书的身影。也许,我没有什么力量干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只能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熬煎着失望的痛苦。我想,难道她奋斗了半天,是要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难道我奋斗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那里,是断送一个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华的泥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的啊!哦,挣扎,想起了那次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挣扎,眼前蓦然闪亮在暮色中的路灯,又蓦地使我心头发热――你为什么不快去找她?你怎么能不去找她……
“她正准备出门,说是有事。什么事?把头发一圈一圈裹上头顶,身上飘散出淡淡的檀香。中午我那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好象并没使她心存芥蒂,她的表情比以往更温柔,闪着眸子看我――但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她将赴的约会。她向我投来抱歉的笑,说她最近太忙。她说她猜到了我找她干什么。本来嘛,初入校门,她理该为‘老朋友’引见一些名人。可惜太忙了。放心,她不会忘记的,不会的,更何况大家都同是来自巴山蜀地的‘小人物’……我脸红了,一种受侮辱的感觉使我的脑血管突突跳。窗外,对面宿舍楼闪烁的灯光好象突然飞炸成无数碎片,扑头盖脸而来。我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过了好久,才能用稍稍冷静的声音告诉她,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她问我,那有什么别的事吗?我说:‘没有。’我告辞了。
“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号,那天晚上我们S大学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男排在世界杯预选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校园里一片欢腾。同学们欢呼着,敲盆打碗,不击烂不尽心头之快。‘砰砰’的暖瓶炸裂声此伏彼起。几千人冲出宿舍楼,点起火炬,一把小号高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围着石榴湖游行,欢庆通宵……走在这支队伍里,我流下了眼泪。我忽然发现,那么多同学,他们过去是奋斗者,现在仍然是奋斗者,不少人过去的奋斗,也许不过是因为对不平遭遇的反抗,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了新的奋斗支点。多么好啊,这里,多少慷慨悲歌之士,为国为民的精英……而沈萍,她在干什么?她会为这一切激动吗?会吗?我想起‘植树节’那天,全系去京郊山区植树,她和我碰巧坐在一辆大轿车上。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开进山区,间或可以看见山坡上几间石块垒成的小房,几个放羊的孩子。她忽然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我膘了她一眼,说:‘你庆幸自己,是吗?’她微微点头,自言自语似地说:‘当然,如果没有今天,糊里糊涂,也许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可是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她说的,是真话。她不堪回首往事。她充满了摆脱命运的漩涡,进入一种新生活、新天地的庆幸。她绝不想想自己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还应该有什么关系。大概,生活中也还会有激起她不平,鼓舞她奋斗的东西,但绝不会是这些,绝不会。会是什么呢?可能只是一个白眼,可能只是一次冷遇……唉,奋斗者,不尽然那么伟大,不尽然,是吗?
“我连夜给她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我问她是不是感觉到了被人生的浊流裹挟去的危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浸漫着一股多.么可悲的浊流啊。我诉说我的担心,担心她在背‘名人辞典’,广交名流的浮华中毁了自己……当然,我很动感情。我向她吐露了那年‘红星’轮相遇以后,从心底渐渐萌发的情感,我承认这是爱。我说,正是因为那难以磨灭的爱,才促使我向她倾诉我的担心和希望。
“……这件事办得这样不理智。我后来才听说,这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某学者(恕我不讲姓名)的儿子――一切都应了‘击鼓传花’得的预言: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而我在她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更何况,我还讲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傻瓜也不会写这样的情书的。
“以后,我们偶尔相遇时,还互相点点头,打一个简单的招呼,但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她给我下的结论是――嫉妒,假正经,还故作多情……”
秦江把双手抬到胸前,交迭十指掰着、按着,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他没有说下去,脸色很难看。一盏一盏水银灯下,我们的身影还是短短短,长长长。
“就完了?”
“唔,应该说是完了。”顿了顿,他又说,“可又象是没完。要不,我干嘛还要管闲事,给自己招来痛苦?”
四
前面是通向宾馆转门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了门,宽敞的会客大厅空无一人。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来。
“上星期六晚上,在无轨电车上,好象是你喊我。我没理你,是吗?”
我点头,一笑。
“就是因为那件事。我很烦躁。”
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我是到首都剧场看戏去了。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朋友,哦,也是过去在‘老莫’和‘康乐’泡过的朋友。他爸爸是搞外事工作的。”
“他和沈萍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他在外地,来BJ出差的。可是在闲扯中,我很意外地听说他的妹妹――一个过去我也认识的女孩子――在谈恋爱,男方的爸爸就是某学者。我吃了一惊,追问了一句,原来那个男的,就是沈萍的男朋友。”
“真的?!”
“我当时也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知道那个男的和沈萍的事。他不屑一提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S大的一位四川妞儿,死缠着他。他告诉我妹妹:烦透她了!我寻思这小子也不安好心,耍耍人家呗……嗨,他当然追我妹妹。他想出国!他有几封教授的推荐信,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混上奖学金,他让我家老头子走走门子,给催催……’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进去。我的脊梁上透过一股寒气。我只想着沈萍。又是浊流!社会的浊流!人生的浊流!而沈萍在这中间算得了什么呀!随波浮沉的一根小草。可悲的是她不知道这些。是的,她不知道。这两天,她不是得意地讲她的男朋友要出国了吗。唉,她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准备挂起她的花头巾了。可是她想到没有,那挂着花头巾的航船正冲向礁石呀……
“回学校的电车上,我连买车票的话都懒得说,当然也没有兴趣回答你的招呼。我只是一遍一遍问自己:告诉她呜?告诉她吗?告诉她,她能相信吗?她不会又一次说你嫉妒、挑拨?再者,那位剧场偶遇的朋友,他说话的可信性有多少哇!缄口不言?这痛苦还不仅在良心上,而且在更隐秘的感情深处!我这时才发现,爱情,尤其是初恋的爱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我得到了那样的回报,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时时回味起那晨雾、远村、坦阔的江面,飘拂的头巾……更何况在现在!在现在!
“回到宿舍,已经熄灯了。默默地躺到床上。同屋的几位正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某某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宝钗’式的人物啦,‘好生生一个清白女子,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啦,谁谁如何‘交游干谒’有道,正进行出国留学的‘秘密外交’啦……我烦透了。浊流,四处漫延的浊流。一股什么火儿升起来,我怒吼一声:‘算了!睡吧!’把他们吓哑了。我呢,却一夜也没睡着。
“清晨起来,我决定把一切告诉她。猜疑、臭骂都可以,反正我尽自己的责任。
“吃早饭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就在那张桌子旁。我端着碗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很惊讶,疑惑地向我点点头。我默默吃了几口面包,说:‘沈萍,你……你过得还好吗?’――天!这叫什么话,连我自己都怀疑这话里有什么‘不良居心’了。‘过得挺好。’她瞟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猜忌,又有挑战。我说:“听说,他……你们那位,要出国留学了?’她说:‘没有。去通过“托夫”了,还要等护照。再过个把月吧。’她老练多了。得意、自豪,全隐藏在漫不经心里。‘托夫’、‘护照’……知道吗?最时髦的名词儿,说得越漫不经心,越时髦。我还能往下说什么呢?我知道,我要说的一切肯定会招来什么。我犹豫了,舌头打了卷儿。
“看来,我只能采取一个最愚蠢的行动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幸亏它没能实现。那可能是我身上消失了多年的干部子弟气质的偶然再现吧。当时,我打听到了她那位男朋友的地址。我决定去找他谈一谈,问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耍这个来自小乡镇的姑娘。真是那样,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他一番,直到他认错为止……多浪漫,骑士一般!当时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个念头。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去了。
“他没在家。他的妈妈说他很忙。护照早就领到了,后天就要飞美洲了。这个消息更使我相信,沈萍的悲剧为期不远了――他这么快就要走了,看来沈萍并不知道哇。
“我在门口勾留了片刻,只好离开了他的家。走出楼门,忽然看见沈萍和一个小伙子远远携手而来。我闪到一旁。她穿着一件时新的银灰色绸料衬衫,丝带束着腰,衬出窈窕的身姿。近胯处的腰带结子随着她的走动而跳跃,飘洒、大方,已经看不出一个外省姑娘的丝毫痕迹。她一定自认为是幸福的,幸福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她绝不会想到等在自己前面的是什么!而我,只能用目光尾随着,看她跟着他走进了那黑森森的楼门。
“天黑了,楼房噼噼啪啪亮起一方一方灯光。几滴雨点飘下来,打到身上。我没有离开,在楼前的马路上徘徊。
“三层,最东边那个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上映出两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他们。也许,现在就是他向她摊牌的时候。大概过不了一会儿,沈萍会流着泪冲下楼来,跌撞着走进微雨之中。天这么晚了,我留在这儿会有些用处。至少,我要远远跟在她的身后,和她一起坐上回学校的汽车,再远远跟在她的身后,目送她走进女生宿舍楼……可是,我又多么害怕看见她跑出来。哦,不,还是跑出来吧……
“十点钟了,窗帘上的身影还在动。一个身影――那是她,她在梳头。我凝神注视着。这姿态我是熟悉的。三年前,在‘红星215’轮上,曙色初开,船过神女峰。她站在船舷,仰脸望峰。江风吹起她的秀发,她的右手也拿着一把梳子,顺着风势,一下,两下……那亭亭玉立的身姿,使站在机房门口的我凝视很久。可是,现在……突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又咚咚急跳起来,因为我看见那个窗户里的灯一下熄了。‘啪啪啪啪’,我踏着马路上耀眼的水窝,几步冲到最东边一个门,嗵嗵地向楼上跑去……
“我还是理智的。我跑到二层时收住了脚步。我问自己:‘你去干什么?’我退下楼来了,走出楼门,闭上眼睛,仰脸让雨水滴打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班驳的路,慢慢地走了。走了几十步,我又回来,默对着那黑黝黝的窗口。我感到心酸。为沈萍,为她妈妈,也为我自己。但愿我在首都剧场听到的那一席话,全是胡扯、谎话、瞎说八道!但愿如此。可是,即便如此,沈萍就幸福了吗?一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她会感到永远幸福吗……我又想,说不定沈萍完了,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浅薄付出了牺牲。可也许,值得庆幸的是,这又使她回到我们中间,重新思索一下生活……如果真能那样,我将把今天晚上所见到的一切永远埋在心底,永远。可能的话,我还会对她说,我仍然爱着她……”
秦江不再讲了,仰头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好象在努力平息情感的波涛。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向眼前缭绕的烟雾使劲儿吹去。结果呢,更多的烟雾在我们的身边飘游。
“后来呢,沈萍怎么样了?”
“不知道。这是前天才发生的事。”
我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瞥了我一眼,用手把面前的烟雾撩开:“你叹什么气?我不是说啦,这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只能使我们警醒、思考、坚定。”
“是这样的。”我点头,“……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和你不见你的爸爸有什么关系?”
“哦,”他笑了,“我险些忘了。”沉吟了一下,他说:“也许,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情了。戴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我爸爸面前----得意吗?得意。可好象又觉得挺没意思。我想起了‘红星215’轮上那块花头巾。人生的道路还长,我为自己设计的这种得意场面感到羞愧。其次呢,我不知道你预感到没有,人们一旦知道秦江是谁,会给我特殊的恩宠,不少老朋友们又会拉我去作‘老莫’、‘康乐’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毅力经受这些了。说真的,这都要感谢沈萍。她使我想许多问题----关于奋斗者。关于人生。”
“那你就永远不去见你父亲了?”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失去这戏剧性的场面,我毕竟有些遗憾。
秦江又笑了:“你何必过于执。等心情好了,我随时都可能回家去看他。不过对你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个儿子回家看看父亲,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我们一起等电梯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作品?我觉得,这件事里倒有不少深意。”
“怎么写?都是同学,又还都在学校。写出来不是惹麻烦吗!”他摇头,忽然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感兴趣,你写。”
我说:“真的?”
“谁写不一样!我又没登记‘专利’。”他沉思片刻,又说:“再说,我要向沉萍讲的,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才能表达了。而这只有由你来说才合适……”
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