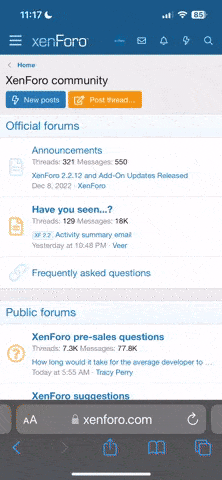树必自腐而后虫蛀之。
“空谈误国”最近很热,尤其涉及人心向背的“腐败”问题之际。ZG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而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主管中纪委,甚至重现问计专家的新闻桥段。凡此种种,使得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反腐”再掀热情:这次,来真的了?
那么,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CPI)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对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
透明国际的数据历史虽谈不上多久远,但不仅为学界接纳,近些年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虽然其统计方式虽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中立性却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更为公允的评价应该是纵向比较。中国90年代曾经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中排名78。
由此可见,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虽有起伏,但仍有不少进步,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正如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发诸多反响,“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伴随着“裸官”到“裸商”的过渡,近几年来腐败几乎成为最能够激起公众集体情绪的词汇之一,甚至当年提出腐败某种情况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学者张维迎,也对于近年腐败的加剧错愕不已,声称腐败已经蔓延到到语言领域。
当我们谈论腐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各家对腐败定义不知凡几,透明国际的广为人知的定义是“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Klitgaard甚至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责任+自由裁量权”。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腐败更准确的定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收取租金。在真实世界中,政府权力就是一笔巨大资源,其中大部分租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权力系统中的个人收集。
也正因此,腐败问题有“表与里”两个层面:表面的问题是,在为政府收租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将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收取的租过大,且未经完备授权,滋生了诸多寻租空间,也使得贪腐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但仍旧可以收取过大的租。
也正因此,民众对腐败的义愤,不仅在于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在于腐败引发的不公加剧,也间接拷问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换而言之,腐败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权力分配的歧视。
现代政府,往往有作为民众守夜人的职责,收取合理租金有其必要性。与之对应,政府收租之后应该为民众提供所匹配的公共产品,而腐败减少了民众理应获得的服务;更加严重的是,官员收租之后,往往允许其收买者超出规则许可范围地行动,间接置其余于不公平境地,如此是双重的不公正与剥夺。
也正因此,腐败并不是仅仅一群体制内官员自肥的封闭小圈子,其影响足以外溢到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以及潜规则盛行不过其中一端。城池破碎,还可修葺一新,但是人心颓败,恐怕难以重拾底线,腐败盛行之下,社会溃败的隐忧甚至超过社会动荡。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距离权力的距离,几乎定义了一个人成功的几率,腐败因此成为不公正获利的扈从。民众对腐败的憎恶,也掺杂着对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义愤;当收入分配不均已经是社会稳定最大隐忧,如果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制度性腐败,则是超级炸弹。
腐败的负外部性可见一斑,可见人人都恨腐败,既然如此,为何不去根除腐败,甚至出现民间所谓“越反越腐”的咄咄怪现象?
已故的美国学者奥尔森晚年曾经倾心于对权力及经济繁荣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其次则是没有掠夺行为。
对照来看,腐败无疑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侵蚀,且如果繁荣的真理如此显而易见,为何没有所有国家都跟随?奥尔森指出,提供法律与秩序的成本,一般情况应该远远低于国民收入以及税收,财产等不平等甚至往往有助于维持秩序;但是在经济政策不善以及制度不良的国家,则存在另一番情况。
在这类国家,政府的规定价格往往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之上也成立),那么区间就有大量的寻租空间,买卖双方都会因规避法律而有所收获,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也倾向于破坏法律,这也是不少学者抱怨的“全民腐败”症结――如果存在大量的价格扭曲行为,必然有各种形式的权力黑市存在,行贿与受贿也变得司空见惯。
奥尔森强调,第三世界的政府倾向于试图推行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甚至违反市场规律往往成为国家的行为规范;他认为这是腐败在苏联式国家不仅成为问题,甚至苏联解体之后也成为重要问题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对于权力的监督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腐败更被列为是世界性难题。政府权力是抽象的,必然依赖具体的个人来实施,也正因此,官员天然具备自由裁量权;问题在于,如何约束这样的自由裁量权?
一方面,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来约束,不少组织行为学的文献证明,其有效性薄弱不堪,而且科层制下官员的晋升可能倾向于会超过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不少经济学研究也证明,至少对于底层官员而言,至下而上的监督也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率――比如,这就是民主而腐败的印度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境。
也正因此,反腐败而言,单向度的监督远远不够,必须“自上而下”系统中添加来自下层的与来自横向的约束,才有可能补足对权力的约束。下层约束的最好方式是官员以其政绩被问责,例如竞选;横向约束而言,其方式则包括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等带来的力量。
回头对照,中国式腐败为何难解?症结在于,政府过分强大,不仅掌握了过分巨大的社会资源,收取了过多的租,而且民间社会长期被挤压,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使得下层约束与横向约束的可能性与渠道遭遇隔绝。
“空谈误国”最近很热,尤其涉及人心向背的“腐败”问题之际。ZG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而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主管中纪委,甚至重现问计专家的新闻桥段。凡此种种,使得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反腐”再掀热情:这次,来真的了?
那么,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CPI)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对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
透明国际的数据历史虽谈不上多久远,但不仅为学界接纳,近些年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虽然其统计方式虽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中立性却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更为公允的评价应该是纵向比较。中国90年代曾经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中排名78。
由此可见,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虽有起伏,但仍有不少进步,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正如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发诸多反响,“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伴随着“裸官”到“裸商”的过渡,近几年来腐败几乎成为最能够激起公众集体情绪的词汇之一,甚至当年提出腐败某种情况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学者张维迎,也对于近年腐败的加剧错愕不已,声称腐败已经蔓延到到语言领域。
当我们谈论腐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各家对腐败定义不知凡几,透明国际的广为人知的定义是“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Klitgaard甚至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责任+自由裁量权”。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腐败更准确的定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收取租金。在真实世界中,政府权力就是一笔巨大资源,其中大部分租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权力系统中的个人收集。
也正因此,腐败问题有“表与里”两个层面:表面的问题是,在为政府收租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将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收取的租过大,且未经完备授权,滋生了诸多寻租空间,也使得贪腐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但仍旧可以收取过大的租。
也正因此,民众对腐败的义愤,不仅在于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在于腐败引发的不公加剧,也间接拷问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换而言之,腐败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权力分配的歧视。
现代政府,往往有作为民众守夜人的职责,收取合理租金有其必要性。与之对应,政府收租之后应该为民众提供所匹配的公共产品,而腐败减少了民众理应获得的服务;更加严重的是,官员收租之后,往往允许其收买者超出规则许可范围地行动,间接置其余于不公平境地,如此是双重的不公正与剥夺。
也正因此,腐败并不是仅仅一群体制内官员自肥的封闭小圈子,其影响足以外溢到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以及潜规则盛行不过其中一端。城池破碎,还可修葺一新,但是人心颓败,恐怕难以重拾底线,腐败盛行之下,社会溃败的隐忧甚至超过社会动荡。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距离权力的距离,几乎定义了一个人成功的几率,腐败因此成为不公正获利的扈从。民众对腐败的憎恶,也掺杂着对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义愤;当收入分配不均已经是社会稳定最大隐忧,如果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制度性腐败,则是超级炸弹。
腐败的负外部性可见一斑,可见人人都恨腐败,既然如此,为何不去根除腐败,甚至出现民间所谓“越反越腐”的咄咄怪现象?
已故的美国学者奥尔森晚年曾经倾心于对权力及经济繁荣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其次则是没有掠夺行为。
对照来看,腐败无疑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侵蚀,且如果繁荣的真理如此显而易见,为何没有所有国家都跟随?奥尔森指出,提供法律与秩序的成本,一般情况应该远远低于国民收入以及税收,财产等不平等甚至往往有助于维持秩序;但是在经济政策不善以及制度不良的国家,则存在另一番情况。
在这类国家,政府的规定价格往往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之上也成立),那么区间就有大量的寻租空间,买卖双方都会因规避法律而有所收获,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也倾向于破坏法律,这也是不少学者抱怨的“全民腐败”症结――如果存在大量的价格扭曲行为,必然有各种形式的权力黑市存在,行贿与受贿也变得司空见惯。
奥尔森强调,第三世界的政府倾向于试图推行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甚至违反市场规律往往成为国家的行为规范;他认为这是腐败在苏联式国家不仅成为问题,甚至苏联解体之后也成为重要问题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对于权力的监督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腐败更被列为是世界性难题。政府权力是抽象的,必然依赖具体的个人来实施,也正因此,官员天然具备自由裁量权;问题在于,如何约束这样的自由裁量权?
一方面,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来约束,不少组织行为学的文献证明,其有效性薄弱不堪,而且科层制下官员的晋升可能倾向于会超过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不少经济学研究也证明,至少对于底层官员而言,至下而上的监督也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率――比如,这就是民主而腐败的印度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境。
也正因此,反腐败而言,单向度的监督远远不够,必须“自上而下”系统中添加来自下层的与来自横向的约束,才有可能补足对权力的约束。下层约束的最好方式是官员以其政绩被问责,例如竞选;横向约束而言,其方式则包括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等带来的力量。
回头对照,中国式腐败为何难解?症结在于,政府过分强大,不仅掌握了过分巨大的社会资源,收取了过多的租,而且民间社会长期被挤压,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使得下层约束与横向约束的可能性与渠道遭遇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