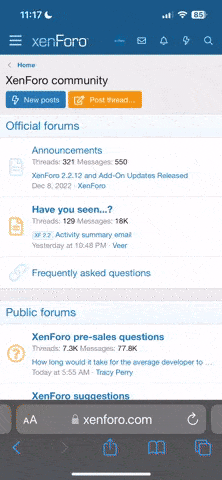1962年,约莫23岁的男青年王仕辉从家乡信宜镇隆来到电白那霍覃坑小学长头岭分校当教师,过着每月工资23元、每天7两米的安乐生活。
“文革”暴发不久,学校停课。王仕辉按捺不住寂寞,到羊角上门做女婿,刁X胜(已自杀)闻知,放言:“王仕辉这地主仔,等其回学校,一枪收拾其。”我警告他:“X胜,你要冷静,千万不要乱来!”同时,我特别提醒王仕辉:“王老师,你要少走动,避避“风头”。他不听劝告,嘴多又好动,“核派有支枪,从水东打到林头了吗?”“我要出去打听一下核派消息……”
1968年的一天,王仕辉从羊角回来,途经那霍兽医站路段,被核派分子一枪击毙,尸体被拖走,留下沾有血迹的一挂袋和一件衣服静静躺在路中央,被兽医站职工黄号辉(健在)好心收留,之后,转到我手,我将它们挂在办公室墙上,全身起寒战。
过了几个月,王仕辉的妹妹跑过来吵闹,责怪大队干部,当时我在县开会,便叫其他大队干部撬开我的房门将那两样东西交给她,捧着弟弟的遗物,她闹着、哭着,肝肠寸断.....
带不走的是阴影,清晰如昨。
“文革”暴发不久,学校停课。王仕辉按捺不住寂寞,到羊角上门做女婿,刁X胜(已自杀)闻知,放言:“王仕辉这地主仔,等其回学校,一枪收拾其。”我警告他:“X胜,你要冷静,千万不要乱来!”同时,我特别提醒王仕辉:“王老师,你要少走动,避避“风头”。他不听劝告,嘴多又好动,“核派有支枪,从水东打到林头了吗?”“我要出去打听一下核派消息……”
1968年的一天,王仕辉从羊角回来,途经那霍兽医站路段,被核派分子一枪击毙,尸体被拖走,留下沾有血迹的一挂袋和一件衣服静静躺在路中央,被兽医站职工黄号辉(健在)好心收留,之后,转到我手,我将它们挂在办公室墙上,全身起寒战。
过了几个月,王仕辉的妹妹跑过来吵闹,责怪大队干部,当时我在县开会,便叫其他大队干部撬开我的房门将那两样东西交给她,捧着弟弟的遗物,她闹着、哭着,肝肠寸断.....
带不走的是阴影,清晰如昨。